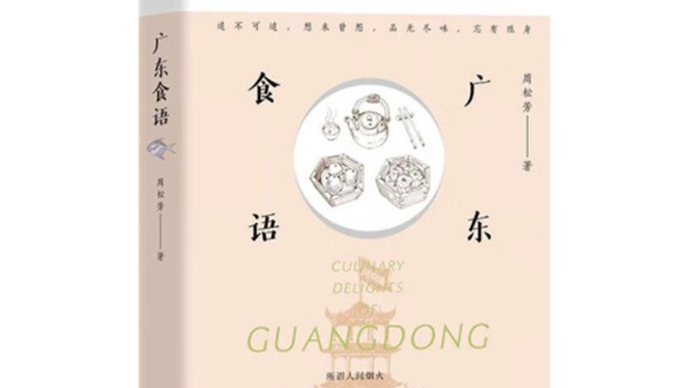周松芳博士的《广东食语》,显然是在致敬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屈大均自序:“夫无穷不在无穷,而在昭昭;广厚不在广厚,而在一撮土;广大不在广大,而在一卷石;不测不在不测,而在一勺。”这是一种文化自信。个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定当跋过千山,涉过万水,更不只读书破万卷书,方能下笔如有神。
如今的《广东食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找到的史料足以广大精微,开阔“食在广州”的视野。所谓“食在广州”,并没有悠久的光辉史,不过得名于晚清民初。周松芳根据大量的新发现文献,指出“食在广州”的得名,与晚清民国作为文化传播中心的上海文化人和媒体的喜欢与鼓吹大有关系,并渐渐得到学者、读者及饮食业界认可。研究饮食文化史,从第一手的文献出发,尤其注重背后的“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则万川汇流成史海,取之无尽,用之无穷。
从前粤菜的第一标配是鲍参翅肚,于今粤菜的第一标配是生猛海鲜。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粤菜的沧桑。周松芳考证,韩愈“初南食”就吃到了不少生猛海鲜,记于《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
广式点心在“食在广州”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某些初尝粤菜、不惯粤鲜的食客心目中,甚至比粤菜特别是海鲜来得更重要。晚清民初徐珂说:“吾好粤之歌曲,吾嗜粤之点心,而粤人之能轻财,能合群,能冒险,能致富,亦未尝不心悦诚服,而叹其特性也。粤多人材,吾国之革命实赖之。”美食之中,赋予了许多文化内涵。
俗话说南米北面。然而,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说“岭南面自古所重”。并说苏轼特别喜欢吃岭南面,忍不住亲自动手:“常于博罗溪水,日转两轮,举四杵,以作白面。”还以诗记事:“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岭南面好吃,苏轼还要以制酒曲,以酿美酒,作诗:“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浆。”踵继苏轼的足迹来惠州的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景仰东坡,留下石刻《朝云墓志》。还有一项与面有关的发明,大约是得了苏轼的神示,那就是伊面。伊面旧称“伊府面”,制法特异,与北方任何面食不同,因为面条是经油炸过的,有时可以直接食用。伊面的好处是,可以煮成汤面,也可以炒来吃,还可以焖,又可以配各种各样作料,成为大小酒楼受众最广的主食兼菜肴。黄苗子将广东伊面与四川泸州的菠菜面,视为面食双绝。
美食的背后是人情。周松芳考证傅彦长上粤菜馆的历史,既是一部上海粤菜馆的微型发展史,也是一部上海文艺界的小型活动史。傅彦长的存世日记,在1933年全年累计上新雅酒楼227次。4月10日的日记中说到与鲁迅的相遇:“午后到沪,在新雅午餐。遇鲁迅、黎烈文、李青崖、陈子展、张振宇。”这是《鲁迅日记》里没有的。鲁迅曾在广州生活过几个月,许广平除了经常陪他上馆子,还两度送他最具乡土特色的食材土鲮鱼,足以证明鲁迅对粤菜的接受和喜欢。至于顾颉刚广州宴游记,从顾颉刚日记中可见,席上有傅斯年、赵元任、罗常培、伍叔傥、杨振声、李济等人,这些人后来大名鼎鼎,而当年俱属少壮,云集岭南,于斯而言,何其幸也,堪为“食在广州”文化贴金。更有趣的是郁达夫的日记里记录了许多不具名的小酒馆饮食。饮食市场中,高中低档酒楼,总是呈金字塔形分布,顶级酒楼就金字塔顶那么几家,高档酒楼处于金字塔上部,为数也不多,大多数还是入不了文人特别是大作家的笔端。好在郁达夫有些“无聊”,写下了,换作鲁迅或顾颉刚,相信去了压根儿也没记上。郁达夫所记的,正是难得的第一手文献。
从谭延闿日记中,周松芳发现谭氏对中国西餐的真正赞美,自广州始,自太平馆始,甚至可以说是自太平馆的鸽子始。一般来说,诗礼富贵人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即使其中饕餮之徒,也多止于浅尝。但谭氏食太平馆之鸽,少则两只,多则三四只,必是至爱。太平馆烧鸽的奥秘,却在谭氏所不喜的中西结合之上。而中西结合却一直是“食在广州”的时尚,在号称“食在广州”开山、自诩广东第一的江孔殷那儿更是如此。晚清民初广州西餐如此风行,粤菜北渐,而以西餐先行,正是岭南文化向外拓展的变迁史。
谭延闿与江孔殷两大美食家在广州的相逢,则是岭南饮食文化史的重要篇章。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江孔殷家宴的江湖地位及其对粤菜乃至湘菜的影响。谭延闿认为饮食之事,昔不如今,也即厚今薄古的观点,更值得今人珍视:“事事皆今不如古,惟饮食不然,吾言不诬也。”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