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芬/文
位于帕皮提市中心海滨大道边的蒂阿瑞旅馆(Hotel Tiare Tahiti),堪称英国小说家威廉· 萨默赛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素材库,也是我南太平洋之行的最重要目的地之一。多年来,我一直以毛姆的平生足迹为线索,试图追忆他丰富多姿而有充满神秘感的人生。此行的最后,从波拉波拉回到帕皮提,终于住进毛姆100年前的下榻之地。
“Tiare(蒂阿瑞)旅馆位置优越,离海滩只有几步”,这是毛姆在书中对旅馆位置的描述。我的塔希提之旅特意订了这家旅馆,心心念念着毛姆下榻100年之后这个旅馆的模样。在这个弥漫着海水和阳光味道的夏日上午,梦呓般,我终于站在了蒂阿瑞旅馆门前。
心,隐隐地跳,但不惊惶,因为我日奔两万里,越洲跨洋,就是来寻找他的。在100年后、这个南纬17度的一个正午,阴阳暌违之间,我终于接住了毛姆散落于地球这一隅的气息。
不错,旅馆隔一条宽阔的海滨大道就是海湾。一眼望去,路上汽车川流不息,海湾里船帆林立,一艘豪华客轮——“高更号”正静静停泊。门前的海滨大道站满了椰姿蕉影,而我并不被眼前的攘攘凡尘搅扰,我恍惚间感到,有一个人,他正悄悄走过来,以他那惯于嘲讽的眼神瞟我一眼,依然与身边那个英俊男孩仰头打量着门牌,土著人为他们提着行李,他们的身影定格在旅馆门口回头的刹那……我则把这一幕镶进一帧发黄的画框,题为:毛姆抵达塔希提。
我在门外站了好久,寻觅着胖胖的老板娘蒂阿瑞。100年啊,可有那个可爱的影子?
01 打开“毛姆的素材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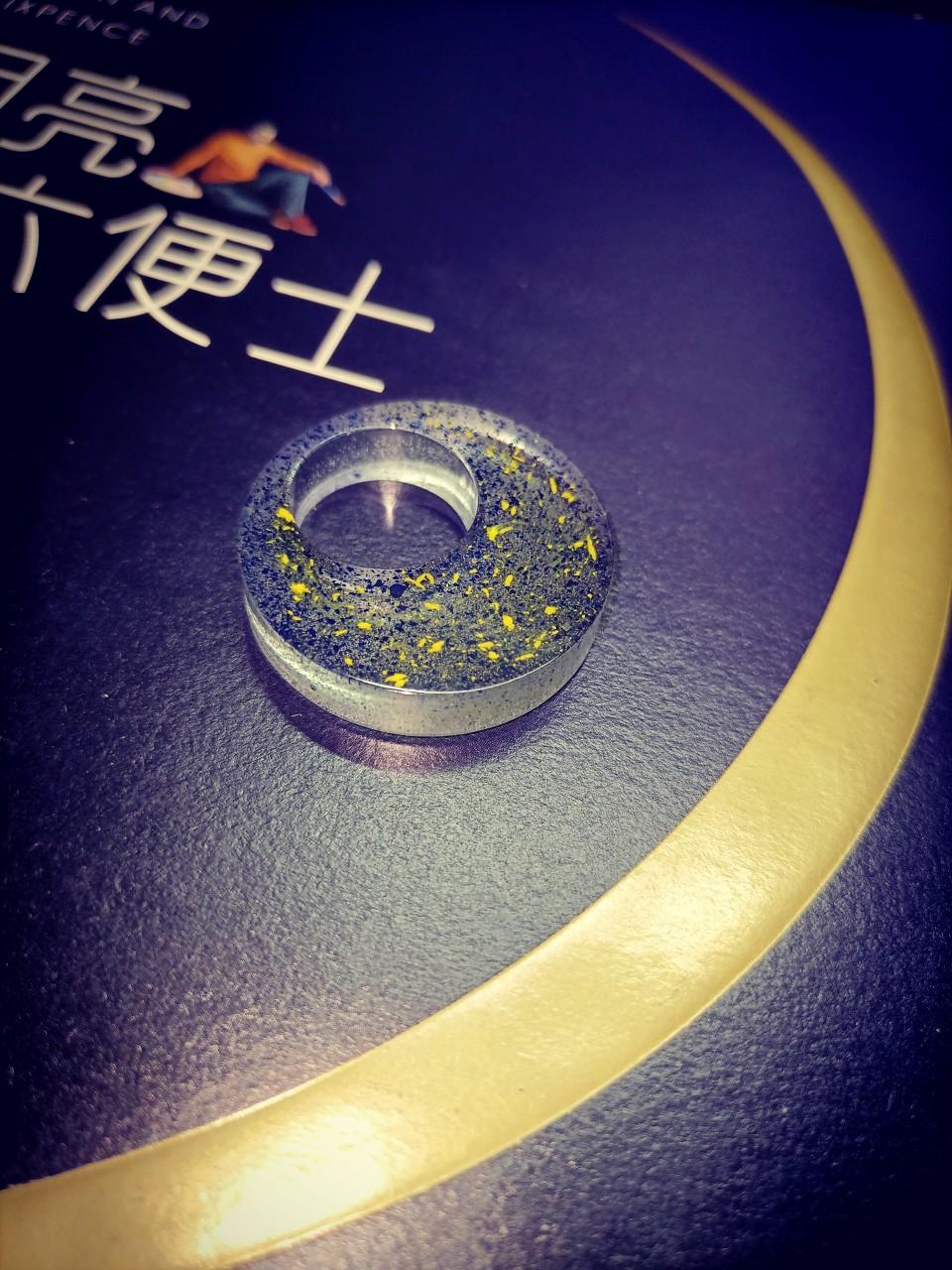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从写作意义上说,毛姆是带着使命来到大溪地的,而非纯粹观光。不擅长交际的他,在旅馆里悄悄进行着对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研究,而他随身带去的那个小男友杰拉德·哈克斯顿就到处闲逛为他收集素材。那时毛姆一方面欣赏塔希提极美的天然景致,另一方面集中收集高更的资料以备写小说之用,但很难遇到能够谈到高更(《月亮与六便士》主人公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人,正是蒂阿瑞为他提供了这一切,并介绍一些与高更有关的人让他认识。
比如,与蒂阿瑞紧密相关的一个“题外话”:蒂阿瑞为毛姆介绍了一个女酋长。可别小瞧这位女酋长,她无意间让毛姆发了一笔“横财”。她告诉毛姆附近有一处收藏高更画作的民房,毛姆与哈克斯顿惊喜地匆匆前去,以200法郎买下民房里一扇画有高更画作的木门。离开塔希提时毛姆把它装箱运回法国,后来安装在他在地中海沿岸的莫雷斯克别墅的书房里,一直到1962年,他拍卖这幅门板,竟卖了37400美元。这个情节,被他“移植”到《月亮与六便士》里的犹太商人寇汉……从这个角度讲,蒂阿瑞充当了毛姆作品《月亮与六便士》的素材库,功不可没。
毛姆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鲜花旅馆”,“客厅并不大,摆着一架简易式的钢琴,沿着四边墙壁整齐地摆着一套菲律宾红木家具,上面铺着烙着花的丝绒罩子,圆桌上放着几本照相薄,墙上挂着蒂阿瑞同她第一个丈夫约翰生船长的放大照片。虽然蒂阿瑞已经又老又胖,可是有几次我们还是把布鲁塞尔地毯卷起来,请来在旅馆里干活的女孩子同蒂阿瑞的两个朋友,跳起舞来,只不过伴奏的是由一台像害了气喘病似的唱机放出的音乐而已。露台上,空气里弥漫着蒂阿瑞花的浓郁香气,头顶上,南十字座星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上闪烁发光”。
这段文字,没能说明旅馆是平房还是楼房。但在毛姆的《总结》和《作家笔记》以及其他多篇文章中,对于他在帕皮提下榻的旅馆都有详细描述。例如在《作家笔记》里,他写到:旅馆是座平房,四面是露台,避出了一块用作餐厅。有一间不大的会客室,地上铺着打蜡镶木地板,摆着钢琴和曲木家具,都盖着天鹅绒。卧室又小又暗。厨房是独立的一栋小房子,洛维娜夫人就整天坐在这儿监督中国厨师。

(从房间阳台俯瞰街道和海湾 摄影/刘世芬)
但100年后的“鲜花旅馆”已“长”到五层。楼体的外墙面呈乳白色,前室可以欣赏到海湾、游艇和海港里来来往往的游船。我们的房间就给到了五层一侧,虽未正对海湾,但也能看到位于酒店东侧的大片海景以及城市风光。

(这个楼梯通往夹层餐厅 摄影/刘世芬 )
餐厅已经不在“一层”,而是位于一楼与二楼之间的夹层,餐布和椅套都是充满大溪地风情的印花布做成,温馨而具有视觉冲击。但客厅与毛姆笔下的无异,几乎还是那个客厅了,也就是进门处的顾客临时休息室。客厅的墙纸是一种米黄色草席,其间点缀着用各种花布做成的图案,以及各种形状的草编饰品,两只藤椅上也是花布椅垫,给人一种独特的装饰感。
02 收到“塔希提的信物”
蒂阿瑞(英文Tiare)本是一种香气芬芳的白花,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国花。在塔希提,一上岛就会被这种花包围。确切说,还没上岛,当我从东京飞往帕皮提的法阿机场,在登机口,大溪地航空的两位超靓的“空少”站在舷梯两侧,其中一人手托一个大圆盘,依次为乘客分发一朵洁白的花,一缕缕清香袭来,引来乘客们一声声惊叹。岛没到,花香来。我也惊讶地叫出声来,因为这朵花终于从毛姆书中飘落到我眼前,不仅可触可摸,并且还以如此美好的形式被赠予……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塔希提岛的男女,都爱戴花,花冠花环必备。这个国家118个岛屿上的每家度假村都会用它来迎宾,一边说着“友—奥—拉—纳”(大溪地语:你好),一边把又香又白的花环挂在你的脖子上。
许多大溪地的旅游资料中,高更的传记里,总之,凡是关系到塔希提的文字,几乎都有一句话:“只要你闻过这种花香,不论走得多么远,最终还要被吸引回到岛上,这是塔希提给你的信物。”
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这句话当然不能缺席。思特里克兰德遇到的塔希提正是这样,“我正在擦洗甲板,突然间有一个人对我说:看,那不是吗?我抬头一看,看到了这个岛的轮廓,我马上知道这是我终生寻找的地方。有时候,当我在这里散步时,我见到的东西好像都很熟悉。我敢发誓,过去我曾经在这里待过”,“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把人吸引住。有的人趁他们的船上货的时候,到岸上,准备待几个小时,可是从此就再也不离开这个地方了。别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待不下去”。
03 寻找“蒂阿瑞”

(蒂阿瑞旅馆前厅 摄影/刘世芬)
多部毛姆传记详细描述过毛姆于1917年2月初抵达塔希提的过程,他就住在帕皮提的“鸡蛋花旅馆”,英文版本为Hotel Tiare Tahiti,旅馆老板娘的真实名字——鲁瓦伊娜·查普曼。毛姆把“Tiare Tahiti”挪到书中,成为“鲜花旅馆”,鲁瓦伊娜·查普曼则成为“蒂阿瑞”。
蒂阿瑞来到读者面前,已经接近《月亮与六便士》的尾声。或许这个人物次要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毛姆把她写得很有“料儿”。
我在这神奇的空间中寻着蒂阿瑞的影子,但整个旅店只有前台值班的一位女士。她显然比蒂阿瑞年轻,无一例外地在右耳插着一朵洁白的蒂阿瑞花,一件圆领大花上衣,宽边眼镜,她身上有一种公事公办的正经表情,绝无毛姆笔下的蒂阿瑞那开朗活泼的热辣性格。不过我很欣慰仍从她黑胖的外表依稀看到了蒂阿瑞的身影。
毛姆把“鲜花旅馆”的老板娘取名蒂阿瑞,很是机趣空灵,令人感到兴味悠长。蒂阿瑞是一个有着一半塔希提血统的女人,个性十足,魅力依然,在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名声赫赫。蒋勋说,花的争奇斗艳,隐含着生命。这句话放在这里,既说给蒂阿瑞花,也说给蒂阿瑞这个女人。这样一个配角,别指望她多么端庄高尚,也别试图从她身上挖掘什么人性的光辉,她就是一个女人的俗世代表,蒂阿瑞“只喜欢三样东西:笑话,酒,漂亮男人”。
但这又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人,“她对所有年轻人都给予慈母般的关照,当在莫安那号船上做乘务长的小伙子喝得烂醉时,我看见她拖着庞大的身躯,走过去把酒杯从他手里拿走,不让他再喝,又派自己的儿子把他安全送回船上”。蒂阿瑞的长相乏善可陈,只那肥胖就让人望而却步了。但这又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女人,弥勒佛一样的女人,天生菩萨心肠,看不得别人受苦,乐善好施放在她身上恰如其分,用眼下中国的国家用语就是“身上充满了正能量”。
在毛姆笔下,“鲜花旅馆”就像慈善机构,帮助所有旅客和非旅客,即,只要让蒂阿瑞看到饥寒交迫的人,她没有坐视不理的。思特里克兰德就是蒂阿瑞让茶房从外面找回来的,思特里克兰德本来与鲜花旅馆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蒂阿瑞偶尔瞥见他瘦骨嶙峋,经常一个人走来走去,她看不下去了,就把他叫去吃饭,给他找工作,但思特里克兰德却“不配合”,总是消失,荒林是他的归宿,他时而出现,时而走失,于是与蒂阿瑞才成为朋友,并且蒂阿瑞做了他的月老。
有些描述很有画面感,蒂阿瑞曾目睹思特里克兰德的遗物,“有十来张画,但是都没有镶框,谁也不要。有几张要卖十法郎,但是大部分只卖五、六法郎一张。想想吧,如果我把它们买下来,现在可是大富翁了”。这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遗憾,更让塔希提众多与思特里克兰德相识的人痛心疾首。
女人的胖,本是非常令人忌讳的,但毛姆在这里却给以欣赏的口吻,“有缘同她结识真是一件荣幸的事”。我在100年后的蒂阿瑞宾馆住了一天一夜,总是下意识地寻找“蒂阿瑞”的哪怕一丝的气息,那个胖胖的身影在我心目中一直很“立体”,皆因毛姆三两笔就把这个人写活了。胖而不腻,两眼炯炯有神,一头秀发。善良,慈悲,崇尚爱情,性情开朗,乐观向上,善良,温厚,宽容,真实,不虚伪,极富同情心,这就是蒂阿瑞的全部了。
毛姆笔下的蒂阿瑞是可爱的,宿命的,跟随时光流逝的,是道法自然的。如果到此你还想象不出蒂阿瑞的模样,那就看看《泰坦尼克号》里那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暴发富婆莫莉·布朗吧。其扮演者是凯西·贝兹,被描绘成“肤如凝胶,丰满、微微撅起的嘴唇,再加上一双蓝中带绿的眼睛,实在是个迷人的尤物”。我曾多次想,倘若要重拍《月亮与六便士》,蒂阿瑞的扮演者非凯西·贝兹莫属。
蒂阿瑞、莫莉·布朗、凯西·贝兹,三人身上具有共同的外形特征和内在的精神气质:肥胖,乐观,通达,个性鲜明,最后她们都让自己的个性成为魅力,成功把肥胖的负性效应减至最低。比如,凯西·贝兹一度被越来越肥的趋势所困扰,粗壮的腰身受到一些评论家的嘲笑,这可是作为一名演员的大忌。但她不气馁,根据角色需要,通过自身的个性魅力,塑造了许多受人喜欢的角色。在《泰坦尼克号》中,虽然戏份不多(正如《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蒂阿瑞),但是这位“不沉的夫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蒂阿瑞从不戴面具,这是一个活得真实的人物。虽是小人物,却在毛姆眼里极为“有趣”。纵观毛姆的所有作品,他打量一个人的出发点只有一点——是否有趣。如果他遇到一个极成功、极有名的人,但却很“乔治”,那么,他会和蒂阿瑞一样,先是奚落嘲弄一番,然后再一脚把对方踹开。毛姆在《克拉多克夫人》里称“邪恶的贝基·夏普比愚钝的阿米莉亚(都是《名利场》人物)要好上一万倍”,而《克拉多克夫人》中的格格弗小姐是“最好性情、最慷慨的人之一,是自制和无私的奇葩;但是,能从她那儿得到乐趣的人,只可能是个十足的疯子”,“她是个亲切仁慈的人,在教区做了无数善事,但她真的太乏味了,只适合出现在天堂”……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姆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出于这个“有趣”的设置,也是他对人的取舍标准。《月亮与六便士》中也是如此,思特里克兰德属于大设置,蒂阿瑞、勃朗什、阿伯拉罕等都是小细节,却令人难忘,犹如西班牙斗牛士身上那件猩红的披风,亦如餐盘上那枚精致鲜美的红樱桃。他用阿美、施特略夫、乔治等那些“正经”却无趣的人物衬托着以思特里克兰德为代表的一众奇葩人物,总之,一切都要围绕他自己的表达需要。
当然,无论如何都应该感谢毛姆,他让蒂阿瑞们就像一尾尾新鲜的活鱼,刚放进水中,就扑棱棱地游了起来,一直游到读者心中。
(作者刘世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看不够的<红楼梦>,品不完的众人生》、《醉杭州 最江南》、《毛姆:一只贴满标签的旅行箱》、《将军台——“时代楷模”张连印》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