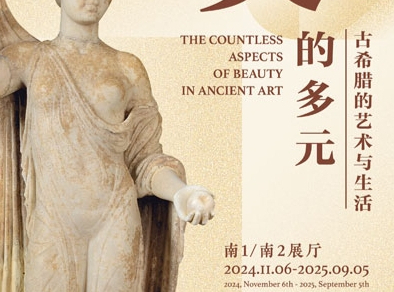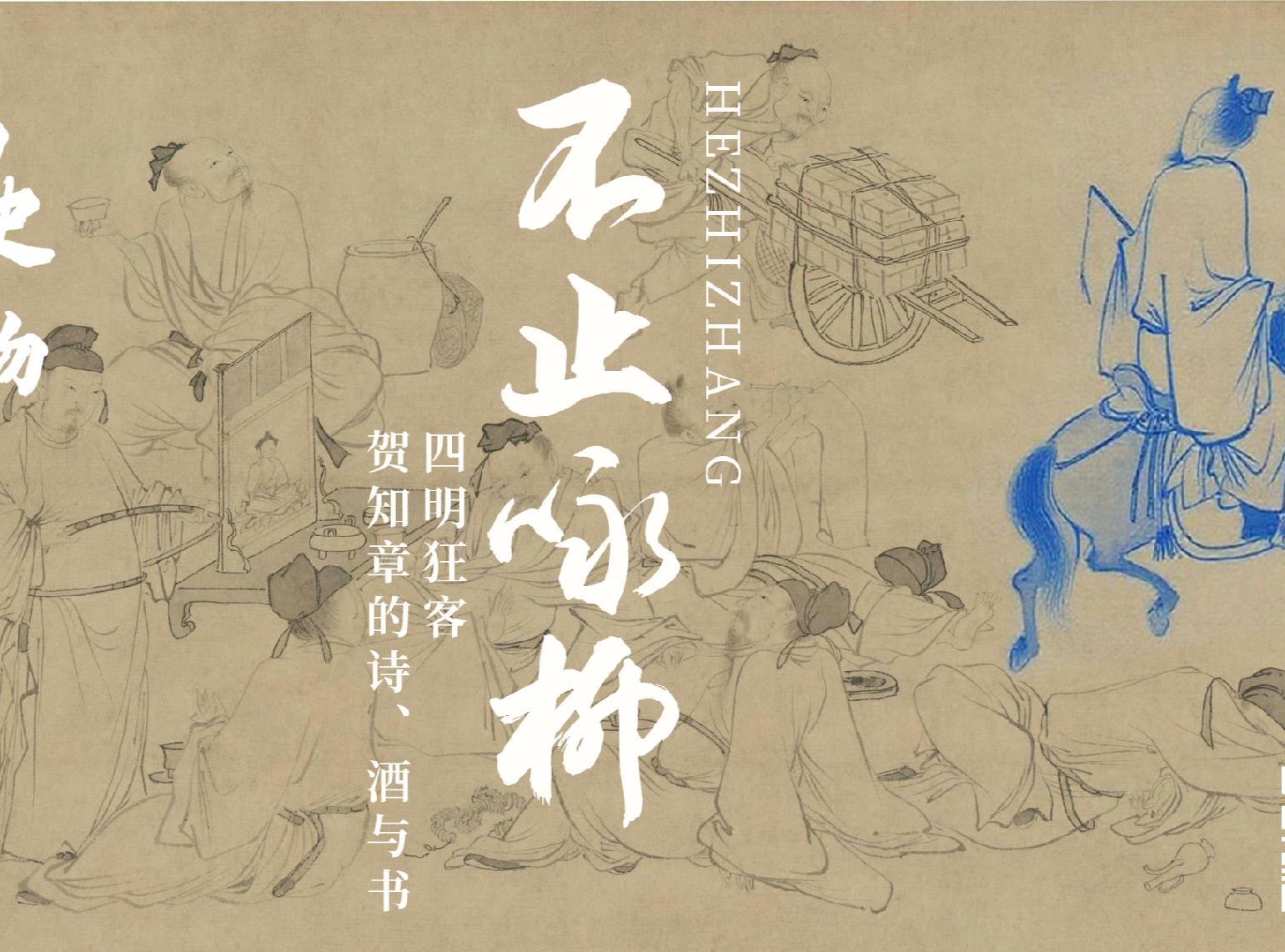尹敏志/文 从长江到岷江,一路溯流而上,20岁不到的齐邦媛孤身一人来到已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读书,时为1943年。进校后她被名师朱光潜亲自约见,转入外文系跟着他读英诗,从华兹华斯、雪莱到济慈。同时,她还跟义兄张大飞产生了暧昧的情愫。每星期都会有一封浅蓝色的航空信从基地寄到她寝室里,有一次,里面夹了一张英姿勃发的恋人和战斗机的合影——“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看到照片的齐邦媛不禁想起这句诗,后来竟一语成谶。
日军的炮火随时可能打破这泛着玫瑰色的青春。有一天她在读诗时,王星拱校长忽然在文庙前召集全体师生,宣布日军一旦入川,大家都要迁到更偏远的“雪马屏峨”区去。一个多甲子后,齐邦媛依然清晰地记得,王校长那天因身穿一袭旧长袍而更显清癯。在初春凛冽的风中,他悲戚地说,我们已经艰苦地撑了八年,绝对不可放弃,“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然而,最后让齐邦媛无法再静下心读济慈《夜莺颂》的,却不是凶恶的日本人,而是激昂的政治歌曲。由于不想跟侯学姐和室友赵晓兰一起去参加左派的“读书会”,那个刚入学时还对她很友好的学姐竟立即反目:这位“进步青年”回来后故意在走廊里大声唱《喀秋莎》和《东方红》,一见到齐邦媛过来就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连赵晓兰也不理她了。难以忍受这样的孤立,齐邦媛只好搬寝室。搬东西的时候,侯学姐还用大嗓门不指名地斥责她是高官子女,“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
那晚安好新铺位后,齐邦媛躺在小床上,头枕三江流水声,望着窗外满天星斗,泪水湿透双颊。半个多世纪后,她在美国和两位华裔作家共同进餐,又勾起了陈年往事。宴毕,年近花甲她走在灯火通明的纽约街头,想起乐山那夜的委屈和不解,仍然感觉痛彻心扉。
“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她在《巨流河》里写道,尤其是那些留在大陆的同学,“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
政治盖过一切的趋势,自从抗战胜利后便已很明显:校园所有课外活动包括话剧、壁报、文学书刊,以及学术讲座都被“左”和“右”鲜明地分开,战时那种团结一心、同甘共苦的凝聚力在胜利的欢呼声和鞭炮声中刹那瓦解。国共两党都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准备争夺东北,紧张的政治气氛笼罩全国。
知识分子在其中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刚到联大的时候,不问政治,天天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治学,有同侪戏赠他别号“何妨一下楼主人”。但此时他却急剧左转,激烈地著文、演讲批评当局。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的悼念会上做了著名的演讲后,他被特务暗杀,身后留下五个孩子。
闻一多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投身政治的,但齐邦媛认为“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给他深爱的国和家换来幸福。”不可否认,他控诉黑暗的道德勇气彪炳千秋,但在那一个急需知识分子站出来以平和理性的态度呼吁两党对话的时刻,他却以一边倒的政治态度把全国性的学潮推到了难以收场的地步。他激昂的呼喊让全国青年荒废学业,参加各种仇恨运动,放弃自由思想,甘当政治工具(虽然这也许并不是他的本意)。其中最后一点“对于中国的命运更有长远的影响。因为他所影响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
当知识分子 —— 尤其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完全投身到政治运动时,那种一呼百应的气势,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独裁权力。虽然这权力并没有实体,但其幻觉已足够让他们丧失自我。在这个“剧场效应”中,不仅观众(青年学生)会受到台上演员(知识分子)的影响,演员自己也会被台下观众鼓动,做出自己原本不打算做的事情。
政治如同筌网,自古以来,被权力诱惑进去的知识分子鲜有能全身而退的。闻一多死后留下一枚未完成的石印章,印面是“其愚不可及”。他到底是借此表明“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决心呢?还是懊悔自己变得太快、太猛,到那个时刻已完全身不由己?
在这种相互激励的政治狂热气氛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无论是左还是右,那时候似乎都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对手消灭,就能解决国家的一切问题。就像把肿瘤切除后,病人就能立即恢复健康,而不从整个机体角度分析肿瘤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思维不止在内战期间流行,后来的反右、文革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其重演,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齐邦媛就问道:“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真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能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曾认为,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向人民灌输对敌的仇恨、将政治抬得至高无上,确实是必要的。因为人们的情感会因此得到锻炼,变得冷酷,“为的是准备在极端的情况下有时候要采用哪些不顾生死的出击”。但如果在这种情况过去后还这样做,那么“心灵就受到了一种无偿的玷污”, “道德情操就会大打折扣”,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人性和“美好的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
在1945年后的中国,出现的就是后面这种情况。齐邦媛回忆道:“自此以后,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别的万岁,每次换换即是。”中间派此时已完全没有生存空间了。如果有学生在当时敢主张我们不应该加入政治运动,还是该好好读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话,便会被左右两派一起攻击。在她1947年毕业时,甚至已有男学生在宿舍里拳脚相向了。
毕业不久,齐邦媛离开喧豗纷扰的大陆,来到台湾大学当助教。回忆录的叙述,也从那章开始,如同流出峡谷进入平原的江水,变得平缓起来。她结婚生子、赴美进修、教书育人。做的最冒险的一件事,就是参与了新国文教科书的编写,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把那些政治宣传品都剔除出去。她说:“我记得在乐山狭窄的街上,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
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台湾,就是这样由知识分子带头推动去政治化,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艰难而逐步地建立起了民主宪政制度。海峡对岸则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下,铁腕地进行全盘苏化,并展开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至1993年作者回到暌违多年的大陆时,她的武大老师吴宓、袁昌英,还有一部分中学和大学同学几十年前就已死于非命。
幸运的人往往是不自觉的,而总要从别人那里确证这一点。在上海邮政医院里,齐邦媛见到了已在弥留阶段的武大同学鲁巧珍。已处于肺癌晚期的老同学以念杜甫《赠卫八处士》的方式“隆重”地欢迎她,当念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时,两人都已泪不能止。最后,鲁巧珍在床榻上气息奄奄地对她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如此简单的愿望,竟是她们那一代人中没有几个能够享受的奢侈。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