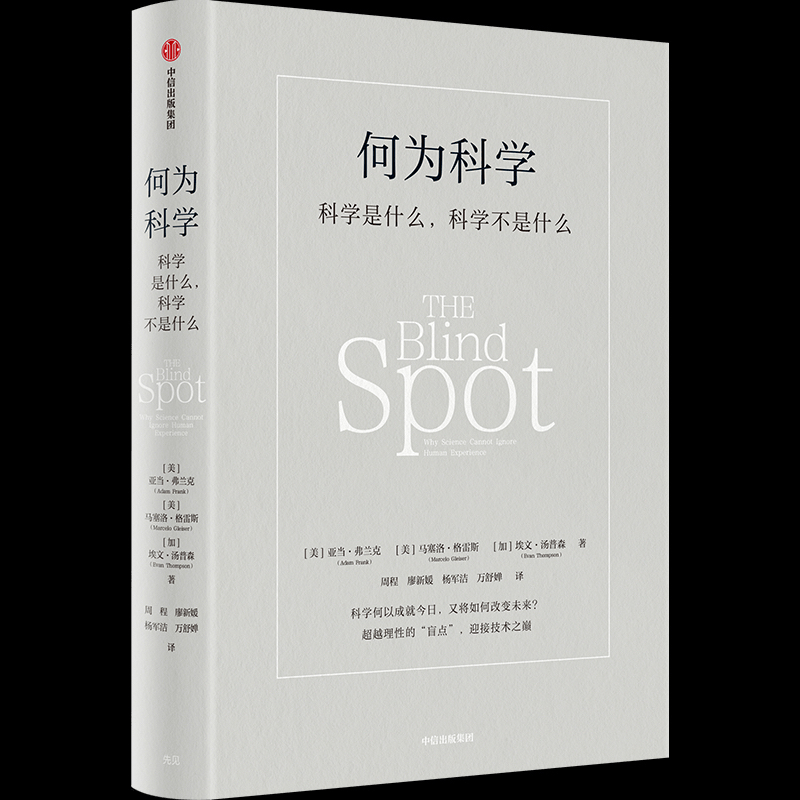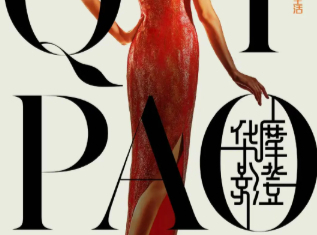闹钟响了。你不情愿地挣脱了残存的睡意,开始迎接新的一天。
墙上挂着日历,圈出了这个月里一些重要的日子:朋友生日,预约看牙,好不容易抢到门票的演唱会。你匆匆扫了一眼,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并没有大事要发生。
地铁列车准点到来,你挤在人群里,心想着出门又晚了点儿。你已经很习惯这条通勤路线了,知道到哪一站要花多久。
走出车站,突然就碰上大雨。每年夏天都是这样。你小跑了一阵,在公司楼下打上了卡。离迟到还差三分钟。
工位上的时间总是要比在床上走得慢,一坐就是半个世纪。你感到一阵腰痛,锤了几下,想起来前两天看过的一篇推文,说什么“许多老年病正在年轻化”。你从浏览历史记录里翻出了这篇文章,和绝大多数推文一样,说了等于没说。
但你确实感到自己正在变老。学生时代能熬一整个通宵,现在不到10点就哈欠连天。健忘程度也在加深,老是想不起来昨天把东西放在了哪儿。
终于磨到了下班点,抬头一看,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你回到家,打开冰箱,掏出上周末屯的食材,看了一遍标签里的“最佳赏味期限”。很不幸,有几样菜已经过期了。
好不容易吃完、洗完,时针已过九点。期待很久的网剧上线了,你迫不及待打开pad,躺在床上看了起来。现在的网剧,总是会设置会员超前观看,也不知道超前在哪里。
但你连一集都没看完。剧里男女主还没正式相遇,你已经在梦里跟周公相遇了。窗外雨声渐止,只有滴滴答答的闹钟,还在等待天明。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普普通通的一天。更准确地说,是被各种各样的时间支配着的一天。
与我们可以随意前后移动的空间不同,我们无法控制时间的流动。我们在衰老,我们周围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它们要么是自然发生的,要么是我们行为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控制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待自己存在的方式。
然而,究竟什么是时间呢?我们从手表、闹钟、日历上看到时间,也从一餐一饭、春去秋来中感受时间。在科学哲学家看来,这两种“时间”是不同的:前一种“时间”由物理测量得来,拥有相当的数学精度,并且被人为设定了公共的标准。而后一种“时间”则来源于我们的直接生活经验,即使我们扔掉一切计时设备,它依然在我们的生命里发生、流逝。
在阿信今年出版的《何为科学》一书中,三位科学哲学家为我们展开了上述“时间”之辨。书中为我们回顾了近代以来科学哲学界中“时间”观念的演变,并指出,现代人所身处的“被时间所支配”的困境,正来源于一个认识上的“盲点”:
把物理学中的时间——时钟所测量的东西,视为唯一实在的时间,却忽视了真正作为基础的、我们在生活中经验到的时间。
以下为书中有关内容的整理摘编。
时间的空间化
盲点出现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考时间的方式之中:把时间作为生活时间(来自经验的时间)和把时间作为时钟时间(时钟测量的时间)。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思想家是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在柏格森的第一本书《时间与自由意志》中,他提出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概念:时间空间化。
什么意思呢?想象一下,当我们提到“时间”这一概念时,最先映入我们脑海的是什么?一个划分成12格的表盘?一张历史课本中的大事年表?还是一个沙子在底部不断堆积的沙漏?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在使用几何中的“点”和“线”这种通过数学语言表达的空间属性来表征心灵中的时间。当我们把时间看作一系列相互外在的点时,我们就把时间空间化了,将时间概念化为一系列离散、同质且相同的单元(如秒)。这就是时钟时间。
时钟时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便于测量。我们已经知道,为了测量某样东西,需要用标准来规定计量单位。例如,标准米曾经被规定为保存在巴黎的一根特定铂金棒的长度。现在它被定义为“原子钟在极短的时间间隔内测量出的光在真空中行进的长度”。但请注意,用于测量长度的标准米本身就有一个长度(铂金棒的长度、光行进的长度)。也就是说,我们用长度来测量长度,用体积来测量体积。因此,标准单位本身就是它所测量的属性的例示。
让我们将其应用于时间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见,我们用时间来测量时间,但是随后我们却把时间转化为空间。假设我们想测量一个物体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所需的时间。古希腊人(以及古希腊之前的许多其他文化)意识到,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运动来测量另一个并行的运动,比如用日晷上影子的运动(或者水钟里水的流动)来测量物体的运动。随着物体的运动,物体的影子也在运动,我们可以感知和记录这两种运动和位置变化的相关性。如果我们对日晷上影子的位置进行编号,我们就可以按照前后顺序来排列它们,尽管它们同时存在。因此,我们说位置5在位置6之前、在位置4之后。这样一来,我们把时间——从并行运动之前到并行运动之后——转换为空间中同时存在的已被编号的相对位置。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一书中所说:“但是,不论何时,只要有一个前和后,那么我们就说这是有时间的,因为时间就是吻合前后顺序的关于运动的数字。”前和后是由日晷上影子的运动给定的,运动的数字是由相对位置给出的。需要注意的关键是,为了测量时间,我们必须使用时间,但在构建时间标准(即时钟时间)的过程中,我们将时间空间化了。柏格森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一旦我们试图测量它,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用空间代替它。”
绵延:时间如河流
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中,时间并不是这样的。
在牙科诊疗椅上的一个小时和与朋友共酌的一个小时是非常不同的。一群跑者可能会在两小时内跑完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但这两小时的流逝对于每个跑者来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是生活时间。
对柏格森来说,生活时间是真实的时间,而时钟时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生活时间就是“生成”(becoming),它是连续的、不可逆的、非对称的——孩子会成长为成年人,而不是相反,同时如果我们抛掉“18岁”的人为规定,我们甚至没有办法确认,孩子究竟在哪一刻成为了成年人。这表明,生活时间不是一个个“点”,因而也就不是由这些点组成的“离散的连续”。它是由无数(准确来说,是无法“计数”)重叠和变化的阶段组成的,每个阶段在质上都是独特的,并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阶段相互渗透。童年的回忆会一遍遍在成年人的脑海中放映,对死亡的恐惧也绝不只是在死亡的一瞬间才会降临。
将时间比作河流,是许多古文明共同的智慧之喻。河流不是一条线,在它一定的宽度中,岸边的流速也许不同于河心。来自上游的一朵浪花会在下游重新被你发现,与此同时,尽管它一刻不停地注入大海,却从未在人们的视线里流尽;尽管它一刻不停地更新自己,人们依然称呼它以同一个名字。在柏格森看来,生活时间就是与河流一样的一种“绵延”,而将时间空间化则让我们失去了这种绵延。
音乐和舞蹈是理解绵延的好例子。旋律和舞蹈只存在于绵延中。它们既不存在于某一瞬间,也不存在于一系列离散的时刻。旋律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个体特征,同时又与前后的其他音符和无声处相融合。舞蹈中的每一个手势和舞步都格外突出,同时也与其他手势和舞步合为一体。前面的音符和舞步在当下的音符和舞步中留存,后面的音符和舞步已经渗透到当下的音符和舞步中。即使是模仿离散的序列性的旋律和舞蹈,也无法避免将其独特的元素融入其间的无声处和停顿中,从而也融入彼此。旋律和舞蹈从根本上看都是绵延的。
柏格森并不反对时钟和测量。他反对的是用时钟时间悄然替代绵延,用空间量代替时间性。他反对那种认为用时钟测量的时间是客观实在的,而绵延仅仅是心理上的想法。相反,自然作为流逝,作为一种纯粹的生成,是在绵延中被赋予的,而绵延是用时钟构建时间系统的源泉。
当我们将时钟时间客观化,并将其视为唯一真实的时间,却忘记了它在流逝的具体实在中的必要来源时,盲点就出现了。时间作为流逝,是在绵延的经验中赋予我们的。柏格森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测量以绵延为前提,而绵延则回避测量。
时钟不测量时间,我们才测量时间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用长度测量长度,用体积测量体积。那么,如果要用时钟来测量绵延,那么时钟本身必须具有绵延。它必须是一个持久的时间实体。它必须是其所要测量的属性的例示。
当然,我们认为时钟是持久的时间性事物。但柏格森要求我们仔细观察。时钟的任何状态——在他的例子中,指钟摆摆动的任何位置——都是外在于其他状态的,就像一条直线上的点或钟表上的数字一样。时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拥有有限状态的机器,其中的每个状态都是外在于其他状态的,每个状态都是空间中一个位置与另一个位置的并列。每个状态都只是现在,没有任何过去的痕迹。过去的状态不能在现在的状态中持续。过去钟摆的摆动或时钟的报时并不与现在钟摆的摆动联系在一起,而是被理解为与之相关的过去。我们在记忆中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但时钟本身做不到这一点。
然而,如果没有这种过去和现在的结合,绵延就不能被记录下来。所有能被记录的是一个又一个不与其他状态重叠的状态,但是这样的顺序本身是不能被记录的,因为这需要我们记忆的参与。
记忆是绵延的一部分,每一个绵延在它的现在中都包含着最近过往的线索。然而,时钟没有记忆。它缺乏绵延,因此无法测量绵延。
柏格森并不否认我们可以测量时间。
相反,他的观点是时钟不测量时间,而我们会测量时间。一个钟表显示10:59,然后显示11:00,这不是在测量时间。测量要求我们看着时钟,读取钟表上的数字,并注意到出现了变化。我们必须把时钟的先前状态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保存在我们绵延的意识中。若拿走测量者的记忆,你就不再拥有对时间的测量。时钟时间以生活时间为前提。
这一点很好理解。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房间里,身边只有一个不显示日期的钟表。当他迷迷糊糊一觉睡醒,他其实无法确认到底过去了多久:是睡了8个小时,还是20个小时,甚至是32个小时?没有生活时间的参照,时钟时间将失去它一直以来约束我们的效力。
柏格森意识到,我们测量时间的精确度越来越高。但他坚持认为,我们无法在测量中确定绵延。绵延没有也不可能有标准单位。当我们测量时间时,我们不会测量绵延。相反,我们从绵延中抽象出一些东西,并以此构建一个时间序列。
即使我们测量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所说的“主观绵延”,也就是与感知者有关的刺激的时间长度,上面的论点仍然是成立的。主观绵延是应用于感知的时钟时间,而不是柏格森意义上的绵延。事实上,将柏格森提出的关于绵延的概念等同于与物理时间相对的心理时间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柏格森并不是说绵延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时钟时间在物理上是实在的。相反,柏格森断言物理学中定义的时间(时钟时间)不能脱离作为流逝的时间,就像在对绵延的经验中体会到的那样。时钟需要读钟者,读钟需要意识,而意识本质上是绵延的。
盲点、矛盾与失忆
从日晷和水钟,到沙漏和重量驱动的机械钟,计时设备有着悠久而迷人的历史,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人们对更高精度的不懈追求。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任何计时装置的有用性取决于我们通过自身的感官收集到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是通过观察得来的,比如观察日晷上投射的影子的位置、时钟指针的位置、石英晶体振动频率的读数,因此计时装置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直接相关。计时装置将无法形容的流逝经验转译成数字语言。这样一来,计时装置似乎将时间物化,使时间具有与物理测量(如距离、重量、速度或压力)相当的数学精度。时钟越精确,时钟时间似乎就离生成、流逝和绵延越远。
然而,任何物理测量都不可能绝对精确。每一种工具或装置的精度都是由其设计所决定。如果一个时钟的精度为纳秒(十亿分之一秒),那么就不能相信它能捕捉到皮秒(万亿分之一秒)尺度上发生的现象的细节。因此,对于特定尺度的测量而言,每一层的实在都存在一个难以把握的更底层的实在。即使在数学上,我们可以把时间分成越来越小的块,我们也不能期望无限地测量这种不断缩小的时间间隔。无限可分的物理时间是一种数学抽象概念,它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时间轴,即一条标上了实数的直线,它是一种用于模拟时变现象的有用工具。然而,时间轴和时钟表盘一样,都不应该被认为表征了时间的实在。
时钟并不能揭示时间的真正本质;它是一种工具,人们发明时钟是用它来抽象经验中时间流动的某些方面,并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测量时间。现代时钟是科学工作间的产物,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将经验的各个方面分离出来,并从中构建出可测量的不变量。但是,不管工作间中出现的钟表有多精确,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仍然植根于绵延,这是一种关于生成的不可还原的经验。
把物理学中的时间——时钟所测量的东西——视为唯一实在的时间,是导致盲点思维链的一个明显的案例。首先,我们用数学时间悄然替代了生活时间。接下来,我们通过宣称抽象的数学时间是实在的时间而犯下了具体性误置谬误。最后,我们忘记了,在绵延里所给予的关于流逝的具体存在,是时间概念意义的初始来源和条件。这种遗忘就是经验失忆症。
盲点的时间观给我们带来了困扰。在数学方面,当我们考虑更短的时间间隔时,我们所谓的对现在的经验就会消失而变成无绵延。无绵延不仅与我们对时间流逝的当下经验和它永远流动的本质相冲突,而且还将数学奇点上升成了谜题和矛盾:持续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由被定义为无绵延瞬间的点状时刻构成的?
我们需要将特定时间概念的目的与由于经验失忆症而认为这一时间概念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的冲动区分开来。为了描述自然现象,科学叙事需要最大程度地从人类对绵延的经验中抽象出时间的流逝。在科学中,时间的流逝必须是有序而精确的,对于所有拥有相同时钟时间的观察者来说都是一样的,至少对于那些处于同一参照系的观察者来说是一样的。物理时间必须有一个普遍的标准,这一要求导致了牛顿绝对时间的上帝视角。
然而,科学需要使用一个数学上的精确的时间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定义具有任何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坚持认为关于时间的定义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是导致经典物理学盲点的一个主要因素。
人类时间包括生活时间和抽象的数学时间线,后者产生于前者。如果最初没有时间流逝的经验,我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抽象的物理时间概念。时间的数学化——表现为由无绵延的多个瞬间组成的连续线——构成了一幅地图,自然的流变是地图上的风景,我们对时间的流动拥有的难以言喻的经验——柏格森所说的绵延——是我们穿越风景之旅的载体。
这份地图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以尽可能高的精度对自然现象进行数学描述。但如果你不懂地图绘制的是什么,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地图绘制者。地图绘制者不应该忘记那些无法在地图上显示出来的东西——在土地上行走的经验、山顶刺骨的寒冷、穿过森林树木的斑驳光线。哪些细节对哪些特定目的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地图绘制者不理解地图的目标,就会让地图的使用者迷失方向。
自柏格森提出“绵延论”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钟时间,已经深入每一块大陆的每一座城镇、每一个家庭。它是如此统一、精确、标准,变成公司的规章、学校的铃声、工厂的制度、马路上的红绿灯。它们成功支配了我们的生活。
但正如柏格森所说,这些时钟时间,永远无法取代我们在生活经验中真正感受到的绵延。生命的价值,从来不在于要“赶”在什么时间之前完成什么目标;无论赶不赶得上,生命都是一场值得回味、值得经历,也值得期待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