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鲁克纳来到天堂,李斯特、瓦格纳、舒伯特、舒曼、韦伯、莫扎特、贝多芬、格鲁克、海顿、亨德尔、巴赫都来迎接他
先讲几则布鲁克纳的轶事。
年老的布鲁克纳曾这样对马勒讲 : "是的,亲爱的孩子,我现在不得不非常努力地工作,这样至少能写完《第九交响曲》,不然我就无法通过上帝的考试。我不久就要去上帝那儿报到了,他将对我说,'你这个畜生,我给你那些天才,除了让你赞美我的荣耀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可是你在这上面取得的成就实在太少了。'"
有一次最后彩排他的《第四交响曲》,结束时,很满意的布鲁克纳给威严而富有的大指挥家汉斯•里希特塞小费,"拿着这个," 他把一枚硬币塞进里希特的手里,"去买一大杯啤酒,祝我健康。"大指挥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枚硬币,然后把它放进自己的衣袋。后来请人把它镶嵌在自己的怀表链上。
1865年,布鲁克纳去慕尼黑出席《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首演,被瓦格纳的音乐强烈震撼,几乎立刻就成为全欧洲最热情的瓦格纳拥趸。此后,他见到瓦格纳好几次。其中一次,见瓦格纳向他伸出了手,布鲁克纳感动得竟然单膝跪下,把这只手抓住按在唇边说,"哦,大师,我崇拜您。"他的第三交响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崇拜,被称为"瓦格纳交响曲"。
布鲁克纳被归类为瓦格纳派。有段时间,维也纳的媒体全被勃拉姆斯一派所控制,无论布鲁克纳的作品何时上演,以爱德华•汉斯利克为首的官方评论家就会把他一通狠批。有一次,奥地利皇帝问布鲁克纳,自己能为他做点什么?"行啊,陛下,您只需告诉汉斯利克先生,让他别再写那些关于我的可怕文章就行了。"
布鲁克纳是一位富于自我批判精神的音乐家,常常校订、修改他的交响乐总谱,这些修改并非是细节上的小修小补:他的第1、第3、第4和第8号交响曲修改得几乎和重新写过的一样。这造成他的交响曲作品版本众多,甚至产生了音乐学中著名的“布鲁克纳难题”(The Bruckner Problem)。

上奥地利布鲁克纳的出生地,现在是安东·布鲁克纳博物馆

圣弗洛里安修道院,布鲁克纳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在那里生活

圣弗洛里安修道院的“布鲁克纳管风琴”
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 1824-1896)在圣弗洛里安修道院担任管风琴师时,已经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一部大型B大调弥撒。1855-1868年,他谋得林兹一个教堂管风琴师的职位,移居林兹。也是在林兹,他成为男声合唱协会的指挥,经常率团演出。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瓦格纳的作品,如《汤豪瑟》、《漂泊的荷兰人》、《罗恩格林》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些作品对他影响深远。
这位终身没有摆脱乡下人本色的奥地利人,性格内向,甚至略有古怪和笨拙。但在他的整个成年生活中,布鲁克纳表现出对"精神世界"的强烈追求与奉献——他以谦卑执著的姿态写就了气息悠长、沉思冥想的九部交响曲,将自己对基督教的信仰融入其中。归功于管风琴方面的经验技巧,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具有丰富的音响结构、多重的复调特性和宏大的结构。同时,他依靠时长及不同寻常的重复营造出特有的美学效果——一种带着拯救与悲悯 , 包容一切的情怀。
布鲁克纳的音乐生涯终于在他60岁时迎来转折。1884年12月30日,由亚瑟·尼基什(Arthur Nikisch)指挥,他的《E大调第七交响曲》在莱比锡歌剧院的首演大获成功。第七交响曲是作曲家最著名的交响曲之一,创作于1881年和1883年之间,题献给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当时正值瓦格纳的弥留之际,作品的英雄主题无疑和瓦格纳有关,第二乐章柔板也被称为“悼念瓦格纳的颂歌”。从令人神往的大提琴开场主题,到谐谑曲乐章开始时的戏剧性狩猎号角,再到光芒闪耀的恢宏尾声,第七交响曲充满了阳光照耀山谷般的雄浑与圣洁。
布鲁克纳曾每周一次去维也纳师从西蒙•赛希特(Simon Sechter)学习和声与对位法,这个赛希特也是让舒伯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还想拜其为师的人。所以,布鲁克纳精通对位法,他所有的和声转换都是根据低音而来。布鲁克纳总是在五线谱总谱的最后一行下面标注低音声部的基础行进,他的低音声部,有种发自内心的深沉和庄严,就像灵魂深处的影子那样陪伴着和声的行进。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布鲁克纳和声的那种崇高、神圣的气质——他是某种宏伟和声的建筑师,酝酿构思着音乐大教堂的和弦与和弦关联,他的音乐里处处都是自然法则和秩序,乃至神圣性,它们是他通向天国的阶梯。实际上,布鲁克纳的音乐创作就是建筑在这两个强大而坚实的支柱之上 : "基础低音"与"自然和声"的理论。
正是这种缓慢坚定、庄严神圣的和声行进,构成了布鲁克纳音乐的精神实质。他成熟时期的作曲风格在形式、和声和调性方面是大胆的、独创的,他高超的复调技巧允许他将个性化的风格融入古老的形式之中。在他的交响曲和合唱音乐中,一切都是那么从容和慎思 :
他的第一乐章经常会有三个大型主题,宏大而庄严,不屈不挠地进行着,他采用和声来塑造力度与音色的变化,他的重复是取之不尽、不断更新的东西,并通过循序渐进的重复达到音乐的高潮 ; 他的慢板乐章可以长达30分钟,通常由ABABA曲式中两个主题及其变化组成,饱含深情,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庄严气质 ; 他的谐谑曲乐章常常使用奥地利民间舞曲素材,让人联想到某种包含大自然的宗教理想 ; 他的终乐章更是精彩纷呈,那些闪闪发光的弦乐和史诗般的号角涌动,予人一种与"永恒"和"无限"相关联的感动。
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是布鲁克纳五部交响曲,以及他的《赞美诗》(Te deum)首演的地方。早在1873年,他的《第三交响曲》曾在这里遭遇重创 : 维也纳爱乐乐团拒绝演奏,震惊之余,布鲁克纳改写了这部作品。可惜,1877年第二版的首演依然是一场滑铁卢,观众们在演出期间纷纷离席——只有12位听众坚持到最后。当《第七交响曲》在莱比锡旗开得胜后,1892年《第八交响曲》在金色大厅的首演成为布鲁克纳在维也纳最扬眉吐气的时刻,甚至勃拉姆斯和汉斯利克都来捧场了,据好事之徒的描述,这两人在音乐厅里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当晚,布鲁克纳收获了观众最热烈的喝彩与掌声——但在此之前,当指挥家赫尔曼·利瓦伊拒绝第一个版本时,他经历了一次地狱般的痛苦,不得不又重写了另一个版本,就像他的其它交响曲一样。

Bruckner Room "布鲁克纳的房间",1920年

Bruckner Room "布鲁克纳的房间"现在的样子
即使在离开圣弗洛里安修道院后,布鲁克纳也经常回来拜访,并总是在修道院的4号客房留宿,这间客房至今仍然被称为“布鲁克纳的房间”

应他自己的要求下,1896年10月11日,布鲁克纳被安葬于圣弗洛里安修道院管风琴正下方的地窖内。石棺的基座上刻着“Non confundar in aeternum”(在永恒中我不会迷失)的铭文,这也是他的赞美诗"Te Deum"的结束行
这个生活在19世纪的中世纪的心灵,为寻求一种通向上帝的艺术关系的问题锲而不舍 :
他有一种癖好,喜欢数建筑物的砖块和窗户,也喜欢数他那庞大的管弦乐乐谱中小节的数量,以确保它们比例上的正确。毫不奇怪,他的音乐俨如哥特式建筑的圆拱顶,兼具巨大的跨度,管风琴般的音响,以及时间与空间上的恢宏 ;
他深受瓦格纳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戏剧作曲的倾向,对瓦格纳的艺术理论也不感兴趣,而只是醉心于瓦格纳管弦乐队的辉煌威力 ;
滋养他的,还有舒伯特的史诗般的气息、贝多芬的独创,以及多瑙河畔修道院的巴洛克式的丰富和热情,他把这一切与中世纪的宗教神秘感和后期浪漫主义的冗长、膨胀的表现手法相结合 ;
他对调性戏剧性地使用,由此构筑起庞大的乐章,他将"规模大小"视作使作品音乐内容完整的要素,而不是偶然或形式,就像绘画作品本身尺幅的大小也是作品风格和精神表现的重要因素那样 ;
他使慢乐章成为严肃交响曲的中心,承接、发展了贝多芬音乐遗产的一个方面,其它19世纪的作曲家均未回应这一点——即使是勃拉姆斯,其最显著的慢乐章也具有间奏曲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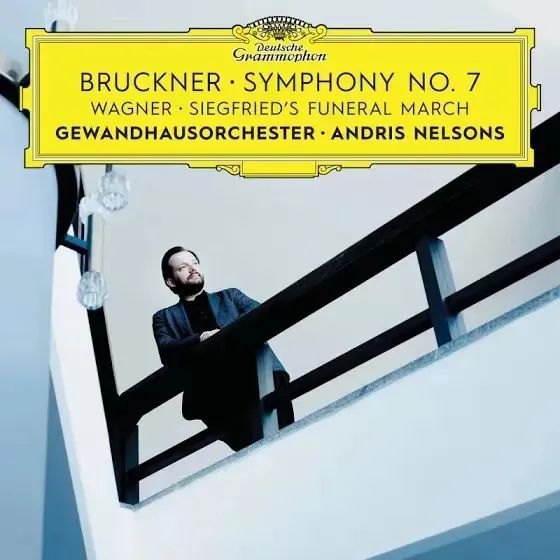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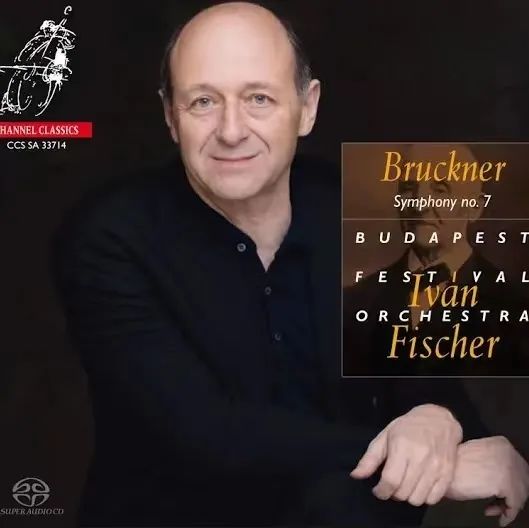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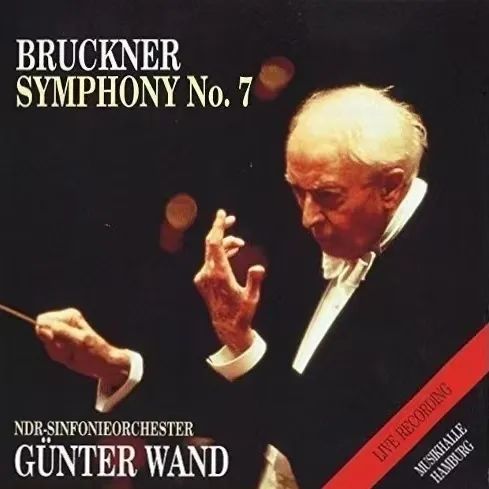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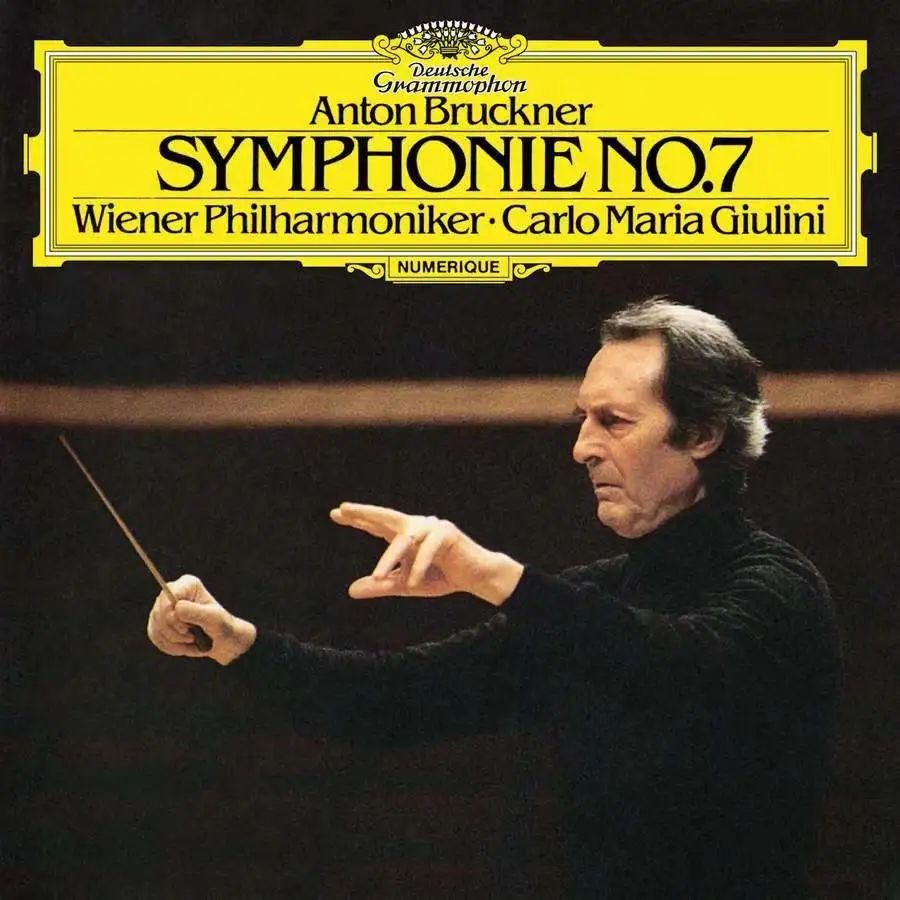
对于布鲁克纳来说,世俗与宗教、生活与艺术之间没有区别。他并非一个超越时代的作曲家,而是站在时代之外——他的交响曲从一开始就带着史诗般的语调,音乐像洪流,像宏伟的赞歌,广阔泛滥,因而也与交响乐思维的本质——逻辑与精简——相冲突。他的交响曲是纪念碑似的,但又墨守成规 ; 有创造性,但又经常使人想起舒伯特、贝多芬、瓦格纳。特别是贝多芬——他写的所有慢乐章在情绪和音调方面,都仿佛贝九的慢乐章在它们周围翱翔。或许,从一个教堂管风琴师和弥撒曲的作曲家转变为交响乐作曲家,布鲁克纳从未完全丢掉他原来的职业——所有这一切都暗藏着一个教堂音乐家经过多次犹疑而最后占领"交响乐"这个园地时所感到的局促与不安。
像他这样完全不合时宜的艺术家是少见的。
重要的是,他在倾诉内心感受时,从来不掩饰其虔诚的朴素性和在技巧上的笨拙。你总是能透过他的音乐,听到淳朴、温暖与纯粹。
我想,他的交响曲之所以有魅力,甚至是魔力,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朴素的宗教情怀,平和的心态,以及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这些品质正是现代人所欠缺和渴求的。

熊琦/文
展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