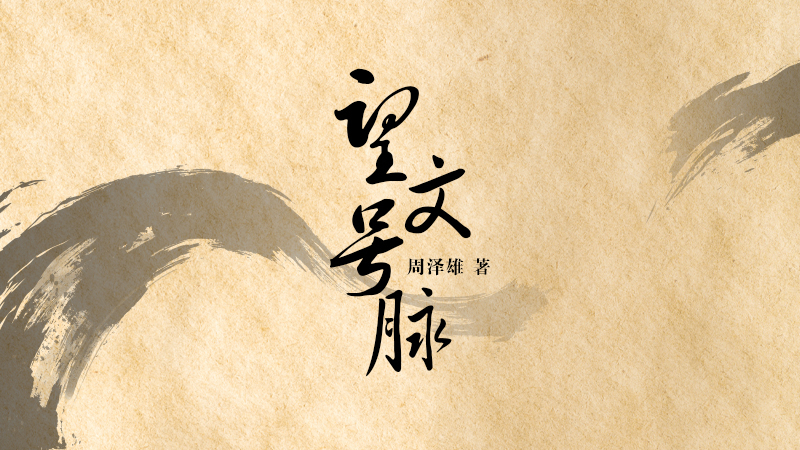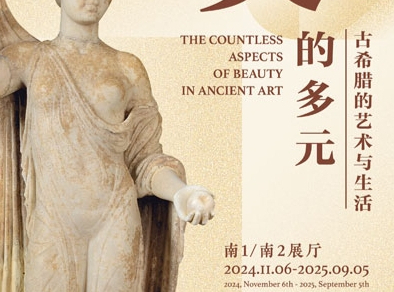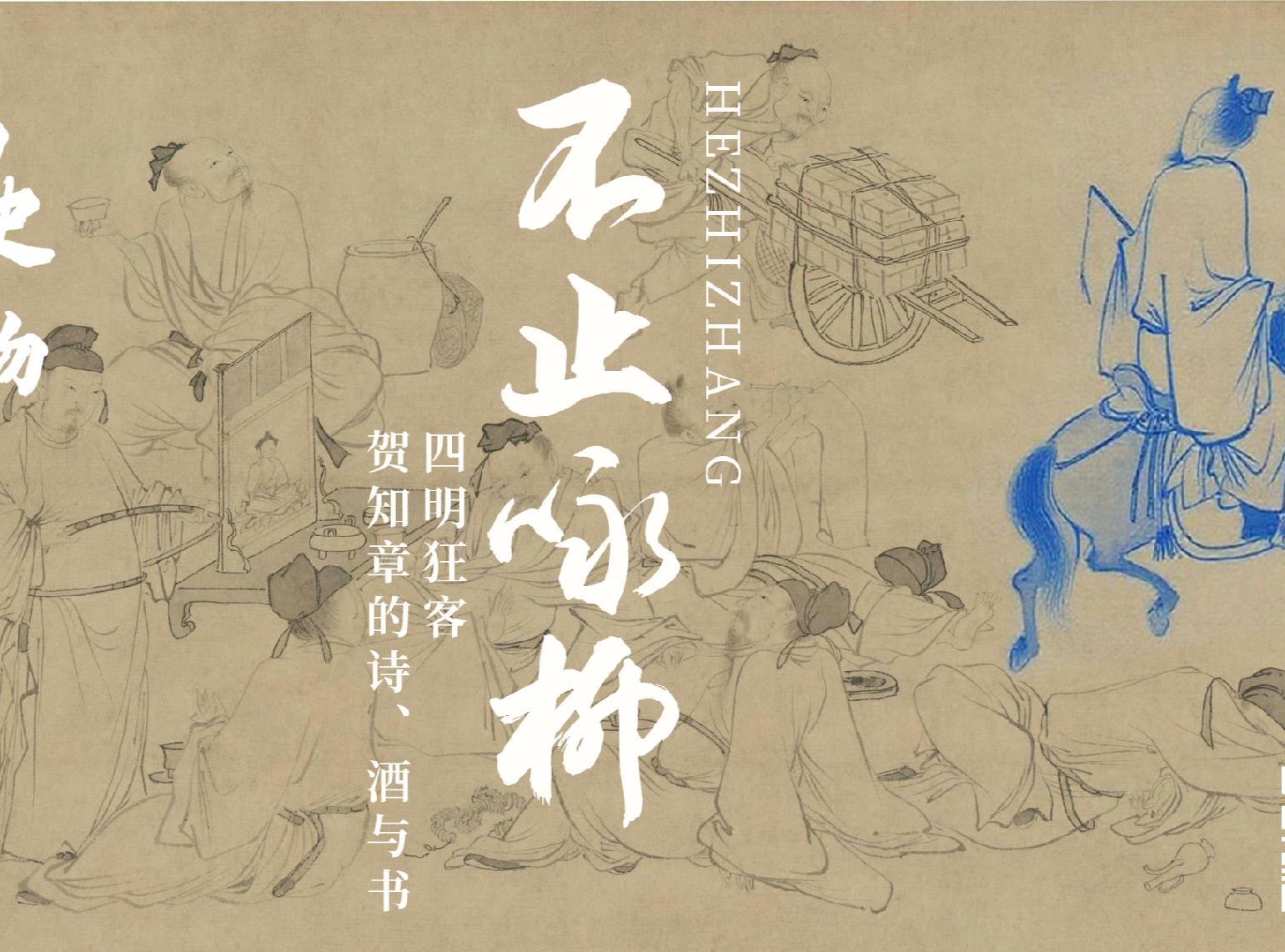周泽雄/文 不见刻薄文人,久矣。
这恐怕是一种文学软骨症的症候,表明我们无力供养非凡的刻薄鬼。欲说明大文人和刻薄鬼为何同体连枝,费时费字,不如顺手举些名字来得便利。以20世纪为限,掰开手指数数,我们悠闲地发现,那些称得上“大”的文人中,独多刻薄鬼。我提到鲁迅、张爱玲、钱钟书、王小波等名字,大概够意思了。你能找到反例吗?即,刻薄度不如上举四位,优秀度却有过之?难。也许沈从文算一位,但那不过说明,文学上的事不比科学,不宜追求物理定律式的精确,我且观其大略,可矣。
大略地看,在那些距大作家尚缺一口真气的中国文人里,挤挤擦擦着大量好人善人义人和高人,他们除了步调一致地做不来“刻薄”,还异口同声地谋求用自身的人格——而不是文字的美感和力量——来争取读者。他们擅长把写作问题还原成做人问题,他们坚信,读者只要认可自己具有出众的美德、超凡的境界,自身的文学成就也就水涨船高了。于是,我们不断听到他们提及自己如何殚精竭虑,如何饱含热泪,如何把心交给读者。
说到最后一条,我对已故巴金先生也稍存异议。我毫不怀疑巴金对读者的深情高义,但喋喋再三,难免造成负面影响。大要有二,其一,当读者视“把心交给读者”为巴金的优点兼特点,也会对其他作者构成贬低,好像别人只会“把肺交给读者”。其二,将写作问题置换成做人问题,还会造成文学观上的错觉。曹雪芹人品如何?他是为自己的抱负而呕心,还是为满足广大读者对优秀文学的饥渴、繁荣大清国的文学创作而沥血?老实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是,他写出了《红楼梦》。我还知道,有些大作家不惜与读者为敌,立志展示一种冒犯之美:冒犯读者,冒犯世俗,冒犯这个世界。——难道,与声称“把心交给读者”的善人型作家相比,他们低上一头吗?巴尔扎克为了还债而写作,雨果也曾迫于生计,司汤达对读者夷然不屑,然其成就如何,神人共见,无待赞词。当普鲁斯特用数万字篇幅惟妙惟肖地再现了一个小男孩的心灵创伤(起因不过是母亲没在临睡前和他吻别),从而像一位把世界纪录大幅提高的运动健将那样,大幅提升了人类文学情感的水平,他还需要将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另行昭告天下吗?他写出了杰作,文人的精彩和荣耀悉在其中。
文人自夸美德,不过让人起腻,若是侈陈境界,则会把读者活活愣死。不久前读到一篇刘再复先生的访谈《漫游者和苏格拉底寓言》,其中有些表述,把我愣了好久。在金庸题签的“再复迷网站”上,我看到该访谈以压轴形式收入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一书,足见作者的认同和重视。
刘再复提到了一种“第三空间”,他说:“在思维方式上,以前我也是单向性思维,现在完全转向双向性思维了。我完全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框架,因此强调必须有第三空间,价值中立的话语空间。”结合下文,我发现所谓“第三空间”只是一种涂抹了玄学色彩的田舍翁理想。刘再复对李慎之的取向进行了非议,贬为“只是谭嗣同情结,并不是政治理性”,同时又对禅宗及陶渊明遥致了敬意。当然,我尊重任何自愿隐逸遁世的选择,但不会视它为值得尊敬的第三空间。当周边充斥着三聚氰胺化的丑行,不去张扬知识分子的介入立场和批判精神,而是把退避三舍的无为标榜成玄而又玄的“第三空间”,以便用它来替代批判精神,则我恕难从命。我不怀疑刘先生的耳边时有牧笛悠扬,及至人生晚境,得以在一种禅房情境里呼吸吐纳,我也愿意送上人微言轻的祝福。但是,把这份禅房心得漫无节制地夸大,甚至声称找到了“精神家园”,享受到了“回归家园的大快乐感”,就过分了。——附带一提,这话苏格拉底可不敢说。作者一面呈现出“得大自在”的大士模样,俨然每个字里都嵌着一颗念珠,每句话里都闪着思想精光,一面却不过告诉我们,他有休息的权利,有吟唱“归去来”的自由。这份权利和自由,本来是不消多说的,但因为作者提到了“大快乐感”这一凡人难以问津的生命境界,读者就只配连连点头,并在他带功报告般的笑声感应下,相信作者确已“进入很深的精神层面”,并且“穿透了很多书本,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一些血脉”吗?
这类把自己善人化、高士化的倾向,若是任其滋长,确会生成一种负面生态,并迫使真正的刻薄鬼文人难以存身。大家都把劲儿使在人格矜夸之上,长此以往,文学用以烛照人世的功能难免随之消歇。我之前提到刻薄鬼文人,你会发现,他们无一热衷此道,个别家伙还宁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我说刻薄鬼,只是一个抽样,大文人不乏刻薄鬼,不等于刻薄鬼即大作家。此事甚明,幸毋误会,我就不多解释了。
2009年4月25日
(《望文号脉》,作者周泽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定价:32元)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