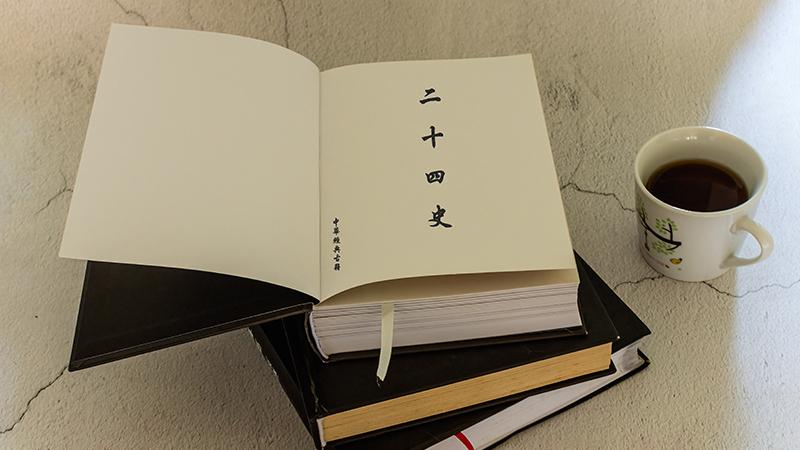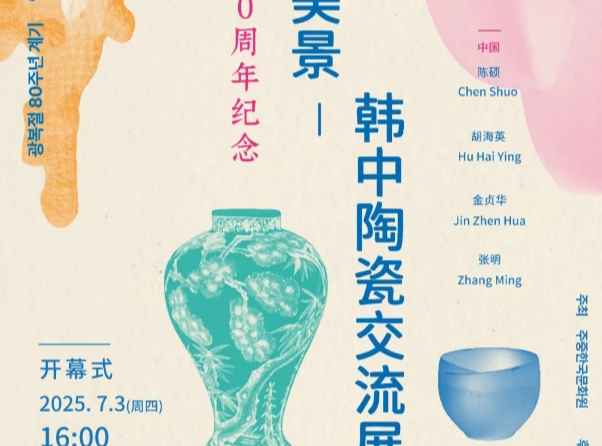历史如何书写,是个老话题。
孔子讲"述而不作",基本就代表了中国的传统史观:官方修史,重在史实,讲清楚,说明白,足矣。史官书写历史,是还原,是回归,不是说故事、讲话本。就好像杀人现场的复原,本质是很枯燥的专业法律程序和医学过程,若变成侦探小说里的推理,一下就好看多了。
所以茫茫中国浩浩荡荡二十四史,只出了一个司马迁。他的作品,既是史家绝唱,又是无韵离骚。就算没读过原书,司马迁三个字,总归是家喻户晓。"前四史"的其他三部,文采公认,作者名字班固、范晔、陈寿,还算熟悉。再往后就难说了,《隋书》是谁写的?《晋书》出自何人之手?《辽书》作者姓甚名谁?恐怕绝大多数普通读者,都要挠头。
我倒觉得这恰好是历史书写者必备的职业素养。本来么,个人仅为沧海一粟,唯有历史不朽。但凡能和历史一道共存,被人长久铭记的个体,本身就已经成了历史。要么得拥有不世出的才华和视野,要么就是刻骨铭心的亲历者。司马迁算是两者兼备,难怪《史记》最伟大。
读《史记》中的描写,我常疑惑,太史公的笔法栩栩如生,仿佛每个场景,他都亲历。事实上,后期的一些历史著作中,有学者就引用最新出土史料来质疑过司马迁书写的真实性。
这丝毫不影响《史记》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先天优势明显,可以接触第一手史料,自己并也不是枯坐书斋,而是走南闯北,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加上对史料的爬梳融合以及编排布局能力均属一流,作品流传后世,就无可厚非了。简而言之,比他能写的,没资格没渠道没背景,和他同僚为官的,文采没他好,又不如他努力。
关键在于修史的资格。世间不缺老实干活的,缺的是天才。司马迁只有一个,剩下的皆为芸芸众生。渐渐地,界限开始明晰起来,一边是正襟危坐主旋律,一边是谈笑风生故事会。一为正史,一为野史。有人会在前者中找寻为政为官之道,有人靠后者打发时间找乐子,有人从前者中学会了敬畏历史,有人把后者变成最为重要的创作源。
世人喜读野史笔记之类,倒也正常。居庙堂之高,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这种人毕竟少。更多人身处江湖之远,嘴里吃着江湖饭,脑子里想的,也是江湖事。落到历史阅读上,就是正史束之高阁,少有人问津,野史、故事、传说之类,津津乐道流传甚广。不信去问诸多所谓历史爱好者,别说二十四史,就看前四史,甚至光《史记》,通读的能有几人?能把后世改写的通俗版白话版通史纲要读完,已是难事,何况更多人普遍时间紧张,好像只够花半小时读完漫画中国史。
正史不易读,有其原因。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大一统,史官修史是国事,著书立传,登堂入室,代代相传。普通老百姓,本来就不是目标读者。而坊间写史,只能口述耳闻,寻章摘句,流到哪算哪。这和西方的历史书写,截然不同。希罗多德写历史,是零散的碎片,是个人的视角,与中国的国家行为政府动作,完全两码事。为何?西方就没有大一统的概念。
此中差异,影响深远。读中国传统历史书写,纲举目张,条块清晰,而且多为宏大叙事;西方常见零敲碎打,以小见大,往往倒也别出心裁。中国读者读来,自然感觉新鲜,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社科文献旗下甲骨文丛书,包括前两年大火的《讲谈社中国史》和《哈佛中国史》,都是这样的套路。
中国的历史书写,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近年比较受欢迎的龙应台、王鼎钧、齐邦媛等人,拥有港台和海外的背景,与传统的史学训练无涉,加上本身就是经营文字的行家,他们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作品,给国内读者带来了巨大的视觉与心灵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书写方式的悄然变化,口述史、个人史蔚然成风,民间写史论史如雨后春笋。
这或许就是历史不断书写的意义所在。有些场景,我们无缘亲历,有的时代,我们已然错过。但是我们有权利去记录当下,也有责任去回望过往。一方面,我们的史学传统依旧秉承宏大叙事,让我们的历史书写永远保有条分缕析的逻辑性,另一方面,时代的便利也赋予了每一个人从自身视角诉说历史的无限可能。
抚今视昔,我又一次想到了《史记》。它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由于太史公对历史本身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同时苦心经营笔下的人物与场景。历史可以被不断书写,观念立场可以各有不同,唯有对史实和文字怀有充分的敬畏,才能在长河之中,有份立足之地。
图片来源:CFP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