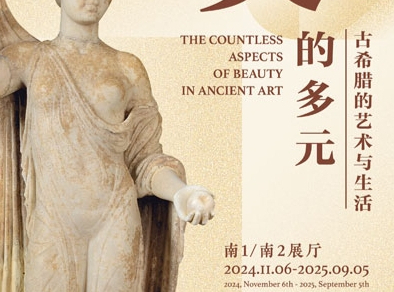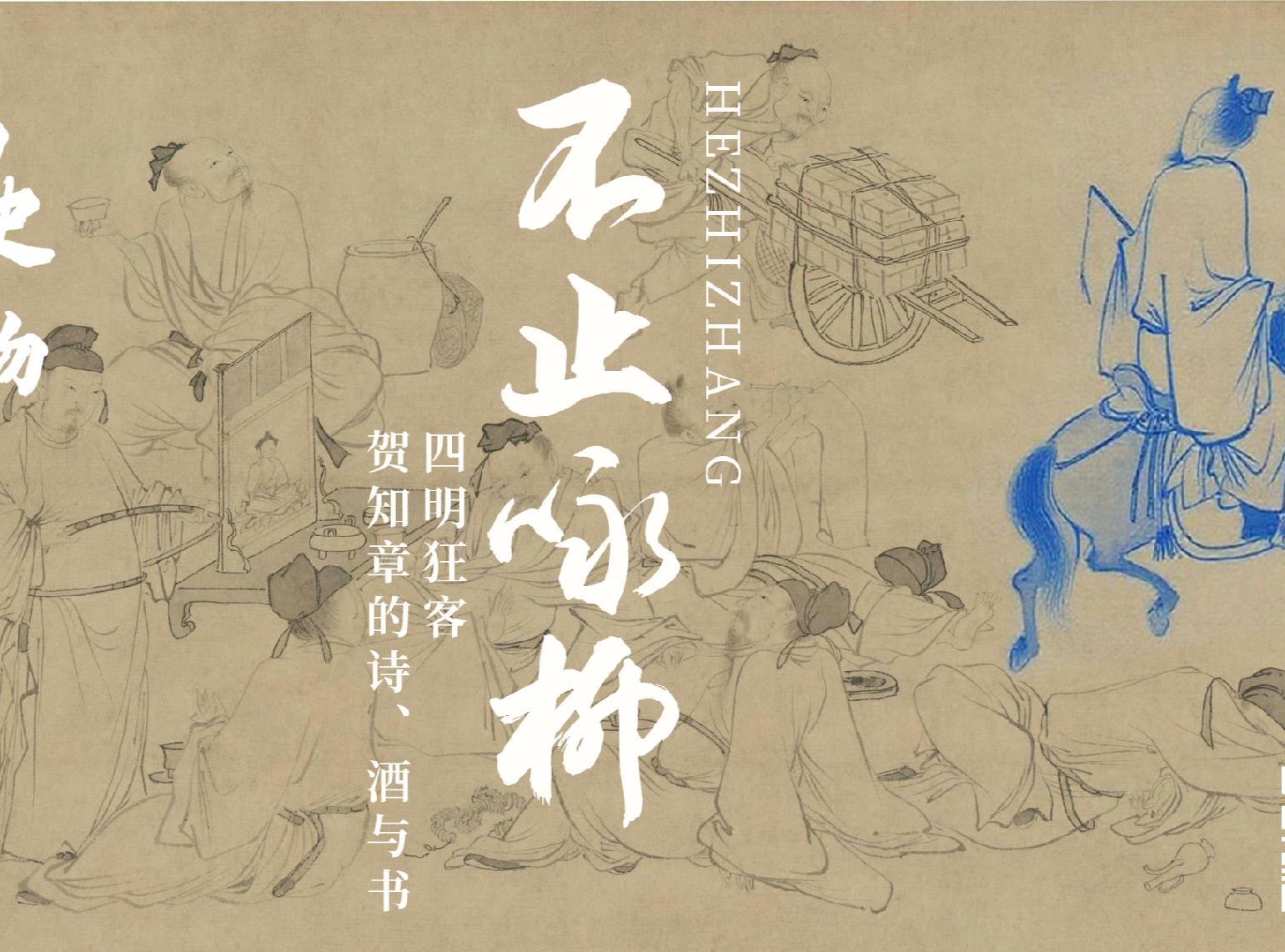关于《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多数的研究都顺着隐含作者的思路,批评她们的人性缺陷。隐含作者、作品中的男性人物把鲍小姐、苏文纨、孙柔嘉、范懿等界定为“围捕”男人的可鄙又可笑的女人,读者、研究者往往也对她们嗤之以鼻。只有倪文尖的《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围城〉拆解一种》等少数论文,能敏锐洞悉《围城》的“男性沙文主义”特质,指出这些女性“在男性中心的叙事结构、叙事语态里,被歪曲了、被淹没了、被‘阉割’了”而成为“空洞的能指”,可谓犀利深刻、独具慧眼。《围城》在塑造鲍小姐的形象时延续的是传统男权文化既消费女性欲望又鄙视女性欲望的思路;在塑造苏文纨、孙柔嘉等形象时,隐含作者又放任笔下的人物,对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提出种种不公平的指控,并运用作者和叙述者的权威剥夺这些女性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围城》的男性偏见由于与作品的现代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尤其富有遮蔽性。

鲍小姐:禁欲的女性才可爱?
按照作者的叙述,鲍小姐的性格一点儿也不可爱。她欲望强健,主动诱惑方鸿渐。
这样一个看来似乎是一无可取的女性,为什么能够让方鸿渐看都不看苏文纨一眼就去接受诱惑呢?根本原因是方鸿渐自己的欲望在作怪。这说明方鸿渐仅仅是勇气不足而已,他在性爱观念上与鲍小姐并没有什么差异。也就是说,方鸿渐其实还是需要女人的行为不检的。行为不检的性感女郎,不仅符合方鸿渐的欲望,而且还能够补充方鸿渐的勇气不足。“她的所谓主体性是男性的恩准,是男性主体欲望的映射”。“有贼心没贼胆”的书生一贯需要行为不检的性感女郎来帮助他们实现欲望。
但是,这一类女性在完成她们帮助男性实现欲望这一任务的时候,常常要受到道德批评。“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这既是方鸿渐对鲍小姐变心行为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鲍小姐欲望的否定。鲍小姐是否如叙述者、男性人物所言只有欲望没有心灵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围城》中除了一句“她看方鸿渐是坐二等的,人还过得去,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外,对鲍小姐的心理感受都没有交代。“人还过得去”,到底仅仅是肉的尺度、欲望的尺度呢,还是包含对方鸿渐的整体评价呢,亦不得而知。也就是说,小说中鲍小姐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是缺失的。读者根本不知道鲍小姐在想什么。一夜情之后,第二夜,她就不理方鸿渐,到底是因为对方鸿渐不满意了,还是因为“要把身心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呢,抑或只是没有理由的喜怒无常呢?文本中由于缺乏对鲍小姐心理逻辑的交代,读者照样不得而知。小说先从男性视角大量铺垫对鲍小姐性感形象的鄙夷,而后仍然从男性视角大量铺写方鸿渐在一夜情中断之后的受挫感,从而让鲍小姐的形象永远定格在“鲍鱼之肆”的臭气中得不到申辩的机会;而方鸿渐却由于鲍小姐“无言”的主动,既能满足欲望,又能金蝉脱鞘而成为纯粹的受诱惑者、被抛弃者。把富有欲望的女人归为道德不好的一类人,正好可以从侧面把这场“一夜情”所可能产生的道德缺憾都归之于女性,使得男性人物的道德纯洁免受挑战、免受玷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既不爱鲍小姐又要热衷于消费鲍小姐性感肉体的道德缺憾,从而能够以实际上并不可靠的纯情面目来迎接唐晓芙的出现。对女性的这种道德批评有利于男性对自己进行道德粉饰。
方鸿渐既在欲望层面上等待鲍小姐的诱惑,又在道德人格层面上批评鲍小姐,正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男性文化既要消费女性欲望又要否定有欲望的女性这一思路。塑造妲己、潘金莲,就是这一类男性文化立场的典型体现。现代男作家老舍塑造虎妞的形象(《骆驼祥子》)、当代男作家曲波塑造蝴蝶迷(《林海雪原》)、古华塑造李国香(《芙蓉镇》)的形象,和钱钟书塑造鲍小姐的形象一样,延续的都是这一类思路。现代作家茅盾在《蚀》三部曲中则完全转换立场,用仰视的态度来膜拜这类性感女郎,延续的则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赞美性爱主动的女性的思路,但是这种赞美仍然是从男性利益出发而对用性爱奖励穷书生的女性狐仙表示感谢的思路,并不包含对女性生命逻辑的理解。曹禺的《雷雨》、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才真正从女性生命逻辑出发塑造了蘩漪、蔡大嫂等正面而又主动的女性形象。

苏文纨:男人“心太软”,过错全在女人吗?
《围城》中,作者常常是从方鸿渐的视角来叙述苏文纨和方鸿渐之间的感情纠葛的。这样,关于苏文纨与方鸿渐之间的是非,在《围城》文本中常常是以方鸿渐的一面之词作为依据和结论。作者既没有描写苏文纨的心理活动,从而剥夺了苏文纨为自己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审视、批评对苏文纨进行不合理指控的方鸿渐,这就使得《围城》文本陷入方鸿渐的男性偏见中。撇开方鸿渐的评价,回到叙事层面对苏文纨言行的描述中、回到苏文纨的心理逻辑中,就可以发现方鸿渐思维的不公正之处、发现作者对这种不公平的偏袒之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心理体验对苏文纨所作的第一个指控是苏文纨利用方鸿渐 “心太软”的弱点诱惑方鸿渐,使得方鸿渐受到了心理压迫。回国的邮船上,苏文纨以“善意的独裁”为方鸿渐“洗手帕,补袜子,缝纽扣”,让方鸿渐感到“毛骨悚然”,因为 “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她每钉一个纽扣或补一个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责任。”方鸿渐“毛骨悚然”的感受,就提示读者说苏文纨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是个貌似温柔的阴谋家。回到上海后,苏文纨的种种情话让方鸿渐产生如坐针毡的感受。这也让我们体会到苏文纨是方鸿渐的精神压迫者。
然而,到底是方鸿渐“心太软”差点落入苏文纨的婚姻圈套;还是方鸿渐不负责任让苏文纨落入恋爱游戏的圈套呢?是苏文纨压迫了方鸿渐的心理,还是方鸿渐游戏了苏文纨的情感呢?
香港鲍小姐上船后,“鸿渐回身,看见苏小姐装扮得嬝嬝婷婷,不知道什么鬼指使自己说:‘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呀,没资格呀!’”
正是这句明显献殷勤的话,才使方鸿渐、苏文纨的恋爱故事有了个开端。苏文纨正是领会了方鸿渐这句话中的仰慕之意后,才开始给方鸿渐“洗手帕,补袜子,缝纽扣”、含蓄表达自己的爱情。倪文尖对此分析说:“虽然叙述者在此加了按语‘不知道甚么鬼指使’,但有一点终算客观:即是有‘鬼’,这‘鬼’也在方鸿渐自己内心!……甚至,换个角度解读,点明‘鬼指使’又有为男性主人公进一步推脱的嫌疑,因为从意识层面降到无意识层面,一般来说总能减轻个人作为主体应负的责任。”
回到上海,方鸿渐伤春感怀,就决定去看苏文纨,他“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图眼前的舒服。”
“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见他对苏文纨的情感、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完全了然于心,只不过不想去顾及后果、不想严肃对待而已。他在“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的情况下,把一个爱自己而自己又不爱的女性当作暂时的情感安慰,根本不管她会在这件事受到怎么样的情感伤害。此后方鸿渐一直假戏真做,只是苏文纨一直蒙在鼓里,还以为方鸿渐真的在和自己谈恋爱呢。但这并不能怪苏文纨自作多情,因为除了最后的一封信之外,方鸿渐从来没有给苏文纨种种的情感暗示作过一点否定。倒是两个人共处的时候,方鸿渐有 “伸手拍她的手背”的亲昵举动,还写了表示嫉妒王尔恺、曹元朗这两位男性的信件。月夜在花园里,又是方鸿渐率先向苏文纨表达自己的欲望,他说“我要坐远一点――你太美了!这月亮会作弄我干傻事。”正是因为方鸿渐有种种暧昧的情感表达,苏文纨才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摆在情人的位置上表现出种种脉脉温情。
这样看来,是认真恋爱而又不明真相的苏文纨落入了把恋爱当儿戏的方鸿渐的圈套。苏文纨在这场恋爱中却是动中有度、自尊自爱、也尊重他人的。方鸿渐“心太软”、不善于说“不”的实质是:当他女朋友缺乏的时候,他需要把苏文纨当作暂时的情感替代品;当他已经有明确的爱恋对象的时候,他意识不到自己有不能误导苏文纨情感的责任。归根结底,是方鸿渐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情感、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也不懂得自尊自爱。他“心太软”,是对自己太放纵,以至于不能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心太软”是方鸿渐值得批评的、不能对自己对别人负责任的道德缺陷、人格缺陷,而不是他值得同情的、受制于女人的弱点。
方鸿渐把自己在这场恋爱误会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全部转嫁到苏文纨头上,是对苏文纨的不公平。隐含作者也以悲悯的态度来同情方鸿渐不负责任的“心太软”,以嘲弄的态度来讥讽苏文纨认真诚挚的爱情追求,使得苏文纨成为一个可鄙可笑的喜剧人物。《围城》并没有把苏文纨的言行本身过度夸张化、漫画化,而是每当对苏文纨的言行进行一次符合女性心理的合度刻画之后,总是让方鸿渐从旁悄悄来一番否定性的心理独白,使得苏文纨动中有度的爱情举动在男性视阈的无情审视之下显出自作多情的滑稽相来,成为叙述者、隐含作者、隐含读者暗中共同嘲笑的对象。这正好印证了这样的男权逻辑:
“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
同样是刻画女性由于误会而自作多情的故事,女性作家凌叔华在《吃茶》中,就采取女性视角叙事,叙述者对女主人公芳影小姐的爱情渴求有细腻的理解与同情,故事的悲剧性压倒了喜剧性,小说由此获得了尊重男性选择自由、同时也理解女性人生伤痛的思想深度。而《围城》的男性视角,把女性爱情失败的生命伤痛界定为咎由自取、甚至还是使男人产生心理负担的不应该的行为,使之完全失去了被悲悯、同情的价值,而成为喜剧嘲讽的对象。得不到男性世界认领的女性恋情,在叙述者、隐含作者的眼中就成了应该“撕破给人看”的“无价值”的东西。这样,一个女人受男性有意误导的、悲剧因素大于喜剧因素的爱情失败,就被隐含作者从男性本位的立场出发,作了完全喜剧化的处理后成了冷嘲的对象。从中可见作家审度苏文纨爱情举动的价值尺度是:一是看它能否契合男性需求,也就是说看它能否被男性认领;二是看它是否符合压抑女性主体意识的封建男权道德准则。这就暴露了隐含作者的人的观念中并没有整合进女性群体、依然坚持把女性作为第二性看待的价值缺陷。

孙柔嘉:真的是“绿茶”吗?
读者对婚前的孙柔嘉一般也印象不好,主要是因为作者让赵辛楣提示方鸿渐、同时也提示隐含读者说孙柔嘉工于心计、长于阴谋。赵辛楣在去三闾大学的船上就“先知先觉”地对方鸿渐议论孙柔嘉说:“……唉!这女孩儿刁滑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
方鸿渐、孙柔嘉订婚后在香港遇到赵辛楣,赵辛楣又对方鸿渐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孙小姐这人很深心么?你们这一次,照我第三者看来,她煞费苦心――’鸿渐意识底一个朦胧睡熟的思想像给辛楣这句话惊醒”。
顺着赵辛楣的提示,读者回想孙柔嘉的种种表现,很可能会觉得孙柔嘉刁滑阴险、富有心机、最终才把方鸿渐捕入婚姻圈套。在赵辛楣的这种提示之下,孙柔嘉第一次与他们见面时,“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也像是一种伪装,至少是一种做作。她那张平常看来并无修饰痕迹但其实却是件“艺术作品”的脸,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她在恋爱问题长于作伪。她时常请方鸿渐拿主意,更是以弱取胜的阴谋。然而,我要指出的是这种评价在事实认定和价值判断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偏颇。.
首先,被赵辛楣描述成像“张开了口”的“鲸鱼”一般可怕的孙小姐,其实并没有任何侵犯他人的恶意,只不过是对方鸿渐早就“有了心事”、有了爱情而已。女人一旦以自己的爱情去暗中期待男性的爱情共鸣,在赵辛楣看来便成了要吞噬男人的可怖可恶之物了。孙柔嘉“千方百计”、“费煞苦心”谋得方鸿渐这样一个丈夫的爱情追求,在赵辛楣的点评之下,罩上了一种阴险的气氛,让人不禁联想起狭邪小说中妓女对嫖客的引诱、暗算。赵辛楣的点评,一是承袭了把性爱当作一种性别对另一性别的征服、而不是两性相悦相知这一野蛮时代的文化观念,二是承袭了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的封建性道德。它使得作品从根本上模糊了女性爱情追求与妓女暗算嫖客这两种不同行为的本质区别,遮蔽了女性的爱情是女性对男性世界的一种真挚情意、女性的爱情追求不过是要与男性携手共度人生这一基本性质,背弃了女性在爱情上也拥有与男人同等主体性地位的现代性爱伦理。
其次,孙柔嘉在搞不清楚方鸿渐爱不爱自己的情况下,把爱情隐藏在心里完全符合常理,不能作为她富有心机、长于阴谋的证据。在这部作品中,方鸿渐爱不爱孙柔嘉是一个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问题。方鸿渐从来没有像爱唐晓芙那样刻骨铭心地爱过孙柔嘉,但是听范小姐说孙小姐跟陆子潇“天天通信,要好得很”,他当场就感到“刺心难受”。他可能是已经爱上了孙柔嘉而自己没有明确意识到而已,至少说他对孙柔嘉很有好感。这种情况下,孙柔嘉把自己的爱情藏在心理,不像范小姐那样直接把爱情暴露出来,只能说明她性格比较含蓄、处理事情比较有分寸而已,不能作为孙柔嘉富有心机的证据。在这个文本中,女人把爱情暴露出来,如苏文纨、范懿那样,是要受到男性人物乃至隐含作者的嘲讽、鄙夷的。女人如果把爱情藏在心里,如孙柔嘉,又要受到男性人物乃至隐含作者的厌恶、敌视的。归根结底,在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中,女人大约是只能等待男性来挑选、而不应该有自主爱情追求的第二性。
再次,孙柔嘉不直接表达爱情,而是创造各种机会让方鸿渐先表达感情,正是女性在男权文化压迫下的无奈。孙柔嘉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她总以弱者的面目在方鸿渐面前出现,表达自己无助的感受:
“怕死我了!……我真不会教呀!……我真不知道怎么教法,学生个个比我高大,看上去全凶得很。” “我什么事也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
这些往往被阐释成是有意做作,阐释成是以弱取胜地来诱骗方鸿渐入套。然而,孙柔嘉大学毕业初次出远门工作,虽然性格中有坚强独立的一面,但同时还有一些无助的怯惧之感,亦符合常理,不可武断地把它判断为作伪。孙柔嘉爱慕方鸿渐,把自己性格中柔弱的一面真实地展示在方鸿渐面前,含蓄地表达渴望得到怜爱的愿望,也是恋爱中人的正常心理,未必是阴谋。
孙柔嘉为人诟病的第二件事是,借助外部力量促成方鸿渐确认婚事。她对方鸿渐假说有人写信给爸爸造自己和方鸿渐的谣;李梅亭、陆子潇出现的时候她又“伸手拉方鸿渐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尽管从没有与方鸿渐商量过婚事,却当着李梅亭、陆子潇的面“迟疑地”对方鸿渐说:“那么咱们告诉李先生――”。这是孙柔嘉假借外部舆论力量促使方鸿渐向自己表白爱情,既是情动于中,又有计谋有策略,因而确实失之于不够光明磊落。但是,孙柔嘉为什么不愿意直接向方鸿渐表白爱情,而要假借外部环境力量促使方鸿渐表白爱情呢?这是因为男权文化传统规定了女人是应男性需求而生的第二性,女性主动的爱情追求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谮越。孙柔嘉在这种文化压力之下不得不把追求异性的权利留给男人,而竭力保持女性被动、矜持的形象。尽管如此“煞费苦心”地使自己合理的爱情追求隐秘化,孙柔嘉终究仍然没有赢得“好女人”的声誉。这是由于文本内有赵辛楣为首的男性群体以火眼金睛严密审视着女性的任何谮越女奴道德的行为。如此“千方百计”、“煞费苦心”,其可怜甚于可鄙。赵辛楣及隐含作者等毫不悲悯女性受压抑的生命无奈,而笼统地把它归之于女性的品格缺陷,有违文学关怀生命、关怀弱者的基本准则。
读者对结婚后的孙柔嘉一般也印象不好。文本外,杨绛那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可以代表这种印象:“……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杨绛的批评成为对孙柔嘉的权威性评语,使得孙柔嘉难脱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精打细算的庸俗小女人形象,因而在可怖可恶之外,又增加了一层可鄙可怜的渺小来。但如果孙柔嘉果真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的女性,她何以独独会爱上方鸿渐这样一个不仅毫无心计、连基本的生存应付能力都欠缺、倒是充满了机智的幽默感、且心软善良的“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男人呢?何以自始自终都能坚持“我本来也不要你养活”的女性自主性呢?虽然孙柔嘉在方鸿渐讲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这些人生哲理的时候,忍不住哈欠,体现出思维、兴趣的有限性,但文本在孙柔嘉与方家二奶奶、三奶奶这两位只会在“围城”内外搞家庭斗争的妯娌的对比中,在与认定“女人的责任是管家”的方老先生、方老太太的对比中,分明已经从叙事层面确立了孙柔嘉自主谋事、独立承担人生的现代女性品格,使她从根本上区别于在家庭小圈子内斤斤计较的依附型女性。《围城》的叙事层,实际上既与赵辛楣对孙柔嘉的不公正指责形成对峙,也与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对孙柔嘉的鄙夷不相符合。而这文本内外的评点、议论,恰如层层枷锁,紧紧压制着小说的叙事层,使得叙事层中本来无辜的女性主人公在读者眼中变得阴险鄙俗。其实,即便是最让孙柔嘉显得琐屑凡庸的种种夫妻口角,也不过是婚姻中日常人生的常态之一,并非是由于孙柔嘉独具小女人庸俗品格才带累了并不庸俗的大男人方鸿渐。这种琐屑凡庸,正是人必然要坠入的一种生存境地,而不是女人独有、男人原本可以超越的处境、品格。也正因为如此,《围城》关于人生“围城”困境的现代主义命题才显得深刻且更具有普泛性。《围城》的这一深刻人生感悟正与其男权文化视角的狭隘、不公共存。
作者简介:李玲,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性别文学研究、知识分子研究。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冰心研究会副会长、海峡两岸梁实秋学会理事。学术代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200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曾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2003年)、1999-2000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1年)。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做《想象女性--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和《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学术讲座。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