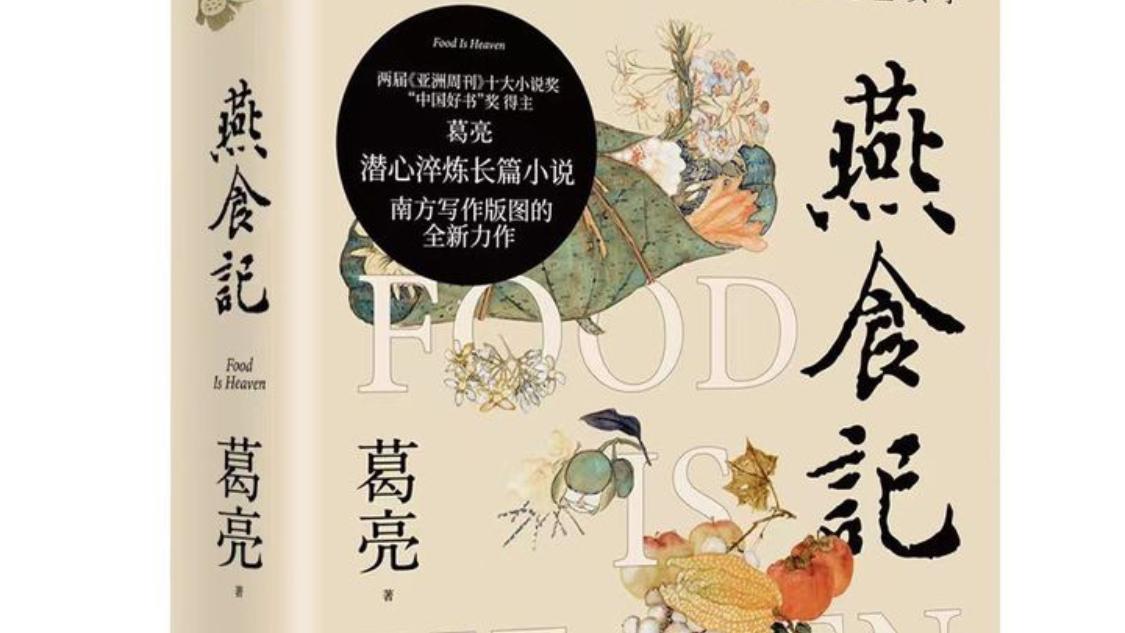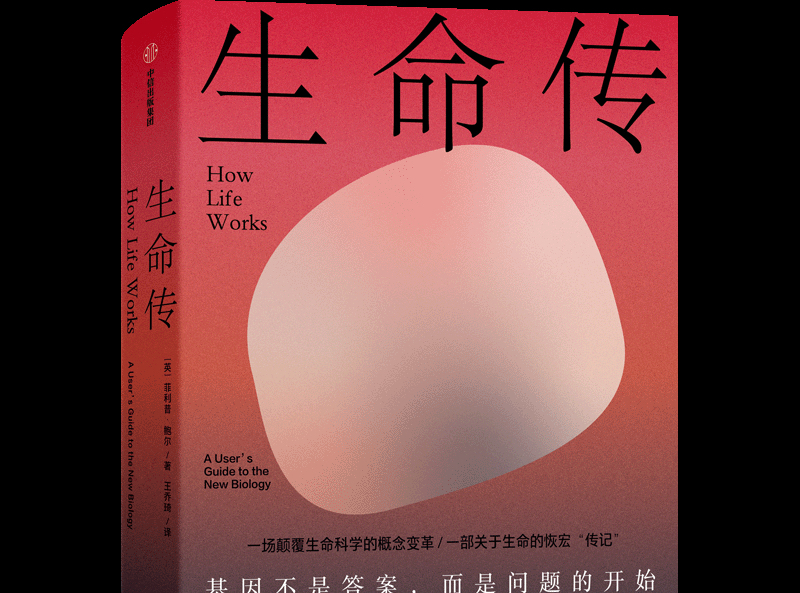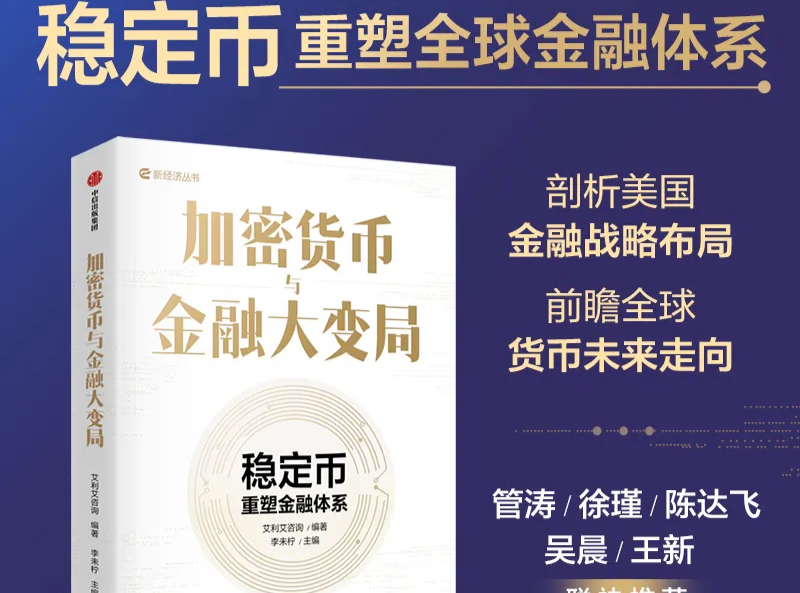近日,青年作家葛亮出版了以宏阔的笔力书写岭南的饮食文化的长篇小说《燕食记》。小说沿着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以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为线索,见证辛亥革命以来,粤港经历的时代风云兴变。学者王德威评价:《燕食记》从岭南饮食风物着眼,写出大湾区世纪沧桑。
同钦楼最负盛名的“大按”师傅荣贻生因打得一手好莲蓉而声名远扬。但做了一辈子,他最想念的,恐怕还是小时候在太史第中第一次吃到的莲蓉枣泥月饼。时隔多年之后,凭着这个味道,他一下子就认出“得月楼”的名厨叶凤池的手艺。当他终于能够复刻这份味道,成为其他人心中的念念不忘时,广府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不可追忆的前尘往事。世事渺茫,但味道永存。
《燕食记》以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露露等为代表的五代厨人的命运遭际,写出了普通中国人心中最朴素真挚的家国情怀以及心存向往、溯流向上的风骨。在以粤港美食作为故事和人物落脚点的同时,葛亮的笔触还深入近代岭南的聚散流徙,从商贾政客、革命志士、钟鼎之族、行会巨头等传奇人物到市井民生,借关于美食的跌宕故事,以细致入微的文笔,生动描摹出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雄浑画卷。
饮食不仅是生活,也是文化切片和容器
记者:小说定名为《燕食记》,“燕食”作何解释?在《北鸢》这部作品中,已经初露您要写作一部关于饮食小说的想法。从那时到这本书完稿,其间您做了哪些具体的功课?
葛亮:小说题为《燕食记》,意为古人日常的午餐和晚餐。周朝确立“三餐制”,意味着礼制的开始,由此确认了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日常俗理。这中间涉及到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吃是属于谁的?“燕食”这个字是突破了所谓的阶层,从王到士大夫,以至平民,实际上便是“民以食为天”。我选择这个主题,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我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归属或者说归宿。
其实想写一本关于饮食的小说,可说是经年的积聚。早在《朱雀》时,主人公许廷迈就是因一碗鸭血粉丝汤联系了与原乡的根脉。经历了《北鸢》《问米》,这种感觉日益强烈。食物是日常,但其背后埋藏着莽莽的历史与幽微的人性,甚而是民族的文化密码。而这密码是在不断地薪传与变革中,也在自我更新与递变,内有“活气”。
所以我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做大量的案头,在有关古典饮食的典籍中,寻找叙事的因由;一方面也做田野考察与访谈,这是关于人的部分,也是小说中的“活气”所在。写这本书的过程是很愉悦的,深入了一个行业和领域,当然会有难点。但这也是延展知识结构的过程,进而是拓展世界观的过程,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是相当有益的。
记者:想必真正热爱美食的人才会写出如此细腻和丰富饮食之作,您肯定是热爱美食的人吧?您谈到,在香港读书期间母亲托人带了一只南京盐水鸭,不仅是味蕾的触动也是文化的认同。美食之于您,意味着什么?
葛亮:首先当然是一种情感的落点。味觉会使得感情的抵达变得十分具体。一切味蕾的触动,都伴生着对于文化轮廓的想象和塑成。因此张光直先生说,到达一种文化的核心首先要通过它的胃。其中包含了文化间的试探与吸纳,亦包含对记忆的唤醒。
中国人对地缘的概念,是绕不开食物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其中已包含食物对空间的定义。《北鸢》卢家睦异地商贾,灾年施济发放家乡食物“炉面”,是德行,亦是不忘其本,实质是出于对“血缘”与“地缘”念兹在兹的块垒。这其中所包含的,是食物对时空的穿透。以我所生活的岭南来说,饮食是十分重要的非遗类型,同时也是一枚文化切片和容器,将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化气性放入其中。
个人记忆与家国记忆的纠缠,凝结于味觉
记者:评论家们说,我作为普通读者也感受到,除了饮食,《燕食记》写了包括粤剧、陶瓷在内的万千生活,还有近百年诸多大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在其中。但都不是直接写,而是点染。这让我想到了石黑一雄在《长日将近》里写二战的手法。这种直接写食物,生活,间接展现历史风云的写法,出于一种怎样的考量和构思?
葛亮:《燕食记》是一部以“食”为题的小说。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穿透岭南漫袤的近现代史;也以一间老字号由粤至港的发展历程,穿透地缘、人心世相的变迁。饮食空间的流转与历史的推进所交汇,成全日常与时代的同奏共跫,甚而被相互见证。
审视史传传统的渊源,久远如“鸿门宴”,区区三字,已包含食物、地点与时间的交缠,更指向人性与政治的博弈。《燕食记》中,向太史说,“当年我和兄长,同师从追随康南海,同年中举,同具名公车上书,但命运殊异。我和他吃的最后一餐饭,只一道菜,就是这菊花鲈鱼羹。只一壶酒,是他从晋中带来的汾酒。”个人记忆与家国记忆的纠缠,凝结于味觉,可说是一种化繁为简,也是一种可被当下复刻的文化密码。
如屈大均所言“天下所有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也。”由此可见,饮食也成为关于岭南最重要的文化隐喻之一。这隐喻中包含历史的流转,也包含了文化的纷呈。二者结合了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一座茶楼的变迁,由得月阁至同钦楼,由粤至港。它在历史中流转,围绕于斯的各种文化元素的叠合,仿佛时代的缩影。
从望族的钟鸣鼎食至最平朴的粥饭光景,从风雅绮丽的《独钓江雪》到铿锵有声的《梳洗望黄河》,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长,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在时代的淬炼中愈加坚韧。有关于食物的记忆都成了民族记忆最深层次的铭刻,这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的辉映。
连接虚构和非虚构两种叙事角度
记者:就您目前的创作版图来看,《燕食记》在其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又体现出怎样的叙事特色?
葛亮:《燕食记》或可视为对现阶段写作的某种总结,特别是有关历史观的表达方式。这是我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想要去探讨的面向,甚至也构成了叙事的脉络所在。
《朱雀》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里面能看到较多叙事者的声音,“我”怎样去看历史,当时确实非常年轻,想要说很多东西。但是到了《北鸢》,叙事者基本上是隐没在文本之下的,我更倾向于让历史自己说话。到了创作《燕食记》,我开始试图通过叙事人的角色与历史之间发生对话。这三部作品或许代表着我在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不同层次。
在《燕食记》中,也连接了虚构和非虚构两种不同的叙事角度,同时穿插了陈五举这个角色。在阅读的时候不知读者是否能感受到,陈五举这个角色在历史现场和在当下的语境里,人物命名是有所差异的。在历史现场他叫“五举”,而在当下现实里,他叫“五举山伯”。之所以叫“五举山伯”,因为想表达他是一个有来处的人。“山伯”二字就像是五举身上的一个烙印,他是带着过去来到当下的。有关于当下的陈述带有某种主观的情绪,这个情绪也未必总是通过山伯本人来体现,其中还有“我”这个代言人。
“我”这个角色作为今人,在一个从过去走来的人身上,看到了当下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与过去的历史呈现存在砥砺之处,而这种差异就成了“我”省思的原点。其后读者会看到五举和师辈之间慢慢走向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五举和“我”的历史逐步嵌合。所以到故事结尾的时候,“我”是隐没的。他就此完成了与历史之间的对话。
因为在这样一个当下,历史即现场,当下即历史。
来源:新黄河
作者:徐敏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