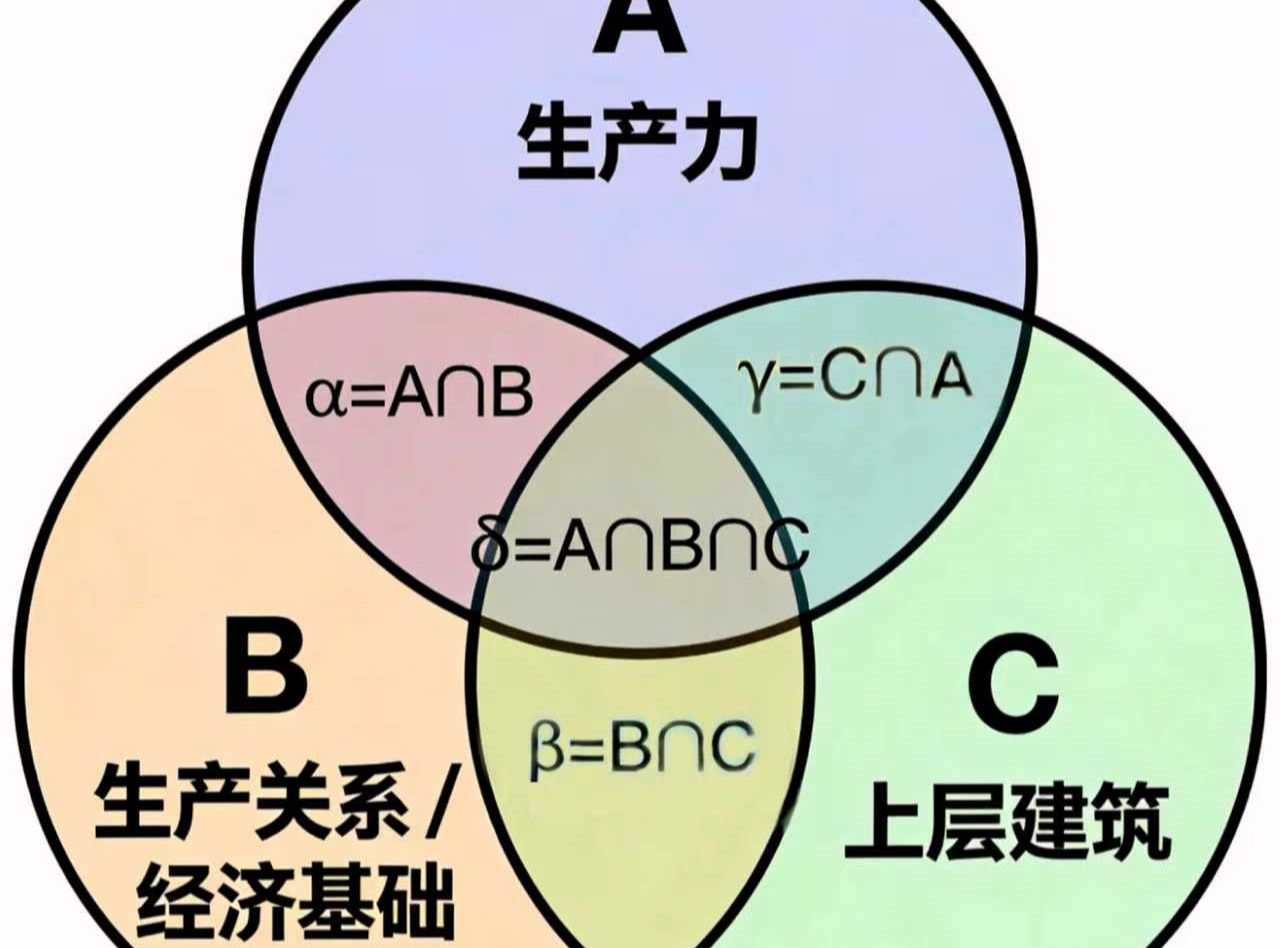6000年前,草鞋山人“穿衣戴帽”吗?
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不仅“穿衣戴帽”,而且还会戴项链、挂胸饰、吊耳环等。从裸身到饰体,草鞋山人见证了人类在自然和社会双重进化中如何自我创造、成长为精神人的“自赎”过程,从自然人进化到社会人。
进化之于人类,既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人是自然的产物;但,人也是自己创造的成果,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
人类有了“创造人自我”的苏醒,便从自然进化转向社会进化,“创造人自我”是人的本质,是人类脱胎于自然、走向社会进化的第一动力,这动力,初始于人的审美意识,有了审美的精神活动,人类才走向文明开化一路。
石器时代,不管旧石器,还是新石器,都是人对自然物的外部加工,差异在于加工程度,是打制,还是磨制,打制要粗糙一些,而磨制显然更为精致,但从一个大的体系上来看,都属于对自然界的既定之物的外部加工,还是自然属性的延展,是自然进化的一部分;而制陶、纺织、构屋的出现,则是人类借助自然的物质特性,通过思想和智慧的加工创造,生成自然界不曾有过的事物,是人类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它开启了人的社会进化的一次伟大的超越。汉语里称之为“天工开物”。如果说葛藤是“天工”,那么将葛藤纺织成麻布便是“开物”,“开物”属于人的创造。
人类以织布穿衣的方式,将人与自然区分开来,这既是社会进化,也是文明开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于文明初创时期,尤为鲜明。而关于“文明”,若非寻诸初始的汉字造字意图,就很难释读不同风土上的人类进化图景。
也许汉字思维更适合我们认识本土初人的独特进化路径。比如“文”字,在甲骨文中形似一个站立的人,人的胸前饰有一个图案,这就是“文”字诞生的第一义,意为“纹”,即纹饰或装饰人自己,以别于那个曾经的自然人。用什么来纹饰或装饰?特指用人的创造性行为、以及“人为”所表达的人的自主意识来纹饰或装饰,在自然的底色上留下了人的行为痕迹。诸如,为心灵描绘以信仰之神纹,为身体美饰以衣玉或建造房屋等。又如“明”字,甲骨文为“日”“月”两字并肩,会意为日月交辉、光芒织映。而“文明”组词,即指人类的创造之纹,明亮如日月交辉。
汉字确有“见字如面”的象形功能,人类社会进化的“文明”之“纹”,为我们认识史前“草鞋山人”的进化梯次打开了一扇窗。
感谢考古人,从六千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三片“葛麻织物”,据说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最早的织物,残片已碳化,纹痕尚在,却愈发引起我们对草鞋山人“纹身以衣”的“文明”遐想。
草鞋山人的“名分”
1956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苏州市吴中区唯亭镇草鞋山遗址。其实,发现一处遗址并不难,因为在中国大地上随便触摸一下,都是滚烫的历史热土,困难的是,经历整整16年,直到1972年10月份,才开始由南京博物院组织正式发掘。发掘面积也并不大,仅550平米,但出土的文物惊人,草鞋山遗址呈现了史前马家浜文化的样貌。
马家浜文化,大约距今7000—6000年,那时的马家浜人活动范围,西濒太湖,东临大海,北靠长江,南抵杭州湾。他们以群落定居,农耕渔猎,如繁星缀络于江河湖海间,享泽国之利,自成一体,不受外界干扰,大抵形成了江南文化的地理雏形,以及江南文化的生态底版。
也许正因为富庶而又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处于文明脆弱期的草鞋山史前文化地层才得以传承有序近千年,而且文化类型迭代分明。1973年4月,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大学联手再次发掘草鞋山遗址500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春秋时期的保存完好的地层关系。尤其史前三种文化类型依次叠压,前后承继,序列鲜明而从容,进化的痕迹在这里没有发生断层,为人类发展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极为完整的经典坐标。马家浜人、崧泽人、良渚人,定居并被滋养在这一方富庶的风土上,繁衍为江南文化的源头,这就是草鞋山遗址和草鞋山人的来历。
但考古学界目前尚未有“草鞋山文化遗址”的称谓,为什么?
按惯例,对于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学界一般以遗址所在地行政名称命名,以标明遗址的文化类型。然而草鞋山遗址的发掘,虽负有“四最”之盛名,如最早的玉琮礼器、最早的水稻田灌溉系统、最早的葛麻织物,以及最具经典标尺意义的考古地层序列等,却没有被冠以“草鞋山文化”或“草鞋山人”。每当人们谈论草鞋山史前遗址时,必以马家浜文化层、崧泽文化层以及良渚文化层来分别称之。
原因是,当考古学界关注草鞋山遗址时,早已有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重大发掘和命名。而从草鞋山第一代居民的遗存来看,他们就是第一批创造马家浜文化类型的分散在太湖流域的“马家浜人”,是在草鞋山一带创造性进化的第一批江南人。
1959年,浙江嘉兴南湖区城南街道马家浜村的村民在挖土时,发现了大量兽骨和人类使用过的遗物。随后,各方考古人入驻现场发掘,第一次发掘的面积是213平米。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发现晚于并第一次发掘面积亦小于草鞋山遗址的马家浜遗址,有幸于1975年因学者吴汝祚第一个提出“马家浜文化”的概念而闻名于世,两年后又得到考古学家夏鼐的认同,正式提出“马家浜文化”的命名,此后,这一文化名称在考古学界立定,直到2009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才真正体系化地确立了马家浜文化类型的文明进程。
距今6000年之际,草鞋山的第一批马家浜居民们,在这里种稻渔猎,筑屋打井,磨玉制陶,穿衣戴帽,作为江南文化的第一代创业者,一路进化,到崧泽人、良渚人,二千年一脉相承,从容有序,完整呈现了史前草鞋山一带在创造中进化的文明样式。为表达对他们创造世界和自我创造的敬意,本文称之为“草鞋山人”。
从文化地缘关系来看,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良渚人应该来自河姆渡人,但当我们顺着进化的轨迹来看时,它们的呈现则更为复杂和充满想象的趣味。原来,良渚人是从与河姆渡文化并行的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草鞋山人是马家浜文化的一支。河姆渡与马家浜这两支文化,分布于杭州湾南北,成长于钱塘江两岸,反映了史前古吴越文化的分布雏形。
看来,马家浜文化的进展要快一点,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从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又与河姆渡文化会合,形成了统一的史前古吴越文化的地理空间,直至良渚人迁徙,形成良渚化世界。
草鞋山人可能是一群衣冠人物
草鞋山遗址出土文物近2000件。
从草鞋山遗址看,“马家浜人”在这里,生有房屋居住,死有墓穴安葬。有玉玦饰耳,还有玉璜饰胸。如此顾盼生辉的打扮,怎能衣不蔽体?的确,他们穿衣戴帽吗?他们为什么要穿衣戴帽?
在草鞋山遗址的第10层也就是最底层,考古人发现了3块早已碳化的纺织物残片,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纺织品实物,据此似乎可以断定草鞋山人开始穿衣了。考古人还在少数墓葬里发现了古笄,表明他们长发有笄可挽,或有葛麻巾包之并以簪插之,妥妥的一群衣冠人物。对草鞋山来说,穿衣戴帽与吃住已经同等重要了。
经鉴定,三片织物为野生葛质地。看来,那时这种草本植物的悠长藤蔓,就在草鞋山人脚下野蛮生长,甚至有可能纠缠他们的步履。但青碧如染的葛藤蔓,经过潮湿沤腐、风吹日晒,竟然纷纷解体成纤,带给人们丰富的联想空间,是否可以利用它们编织成另外一种绳索或者布片?他们开始尝试,不过,他们究竟花了多少时日才完成纺线工艺?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创造过程一定有一个草鞋山人所憧憬的动力。
或许我们可以从《诗经》之《葛覃》或《采葛》的诗景中获得某种美的启示,“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遥想6千年前的草鞋山人会不会有相思的执念?正如“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葛麻至今依然是衣饰审美的宠儿。
一般来说,织造工艺的复杂来自信仰或精神性的执着。三块残片并非简单的平纹织造,而是有着非常复杂工艺的罗纹织物。以纬起花的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并嵌有罗纹边等。织物的密度,经密每厘米约10根葛线,纬密每厘米约26或28根葛线,地部纬密每厘米约13根到14根葛线。草鞋山人缘起于穿衣戴帽的审美意识,也许就滋生在这种由线组成面的具体创造的过程中。
罗纹组织,是由一根纱线依次在正面和反面绕线圈式的纵行编织工艺,如同我们今天熟悉的条绒一样,而罗纹组织经纬凹凸,更具有立体的质感和自由的弹性,它还可改变麻线的干脆和粗硬而趋于柔软,随着人的进化而适应人体对舒适度的需求,想必草鞋山人最早的衣饰就是这种织有罗纹花的葛麻了。
考古人还同时发现了磨制的石纺轮,有了石纺轮开端,人类因纺织牵线而发生的审美意识,与玉石上磨刻的审美意识一样,成为草鞋山人的精神成长之源。
1万年到4千年之际,全新世大暖期是孕育人类文明原创力大爆发的温床,人类定型文明的所有“第一个”创造,几乎皆诞生于这一温床期。如织布、制陶以及构屋等。
墓葬和房址,表明草鞋山人开始了定居生活。不但结束了人与动物争抢洞穴的自然状态,而且开始了构屋穿衣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新时代;定居,意味着人有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从自然循环中独立出来,才有可能停下来缝制衣服。如果说自然界还是自然形成的,或神创的,那么构屋穿衣的定居方式,则是人类自己的创造,成了文明进化的标志性事件。
草鞋山人“衣”欲何为
值得注意的是,草鞋山人穿衣戴帽,带给自身精神指数的成长密度,三片早已碳化的葛麻罗纹织,表现的工艺“文明”,仍然可辨草鞋山人坚定、鲜明以及极具考究的装饰意图,传递出六千年前人类精神成长的审美倔强。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着装?着装与精神成长有什么关系?
据说,人类着装始于体毛蜕变的渐进过程,或为保护性遮蔽或为御寒等功能性需求。而大部分学者的“御寒”推断,皆来自1万8千年前北京山顶洞人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的启示。但随着1万年以后的大暖期到来,御寒说恐怕就不适于鸟语花香、渔利舟楫的温暖之地。当然,大暖期的全新世难免有寒冷小冰期的造访,热带和亚热带也会有寒流突降。距今4千年以后,小冰期便开始迫使人类不断向温暖的地方迁徙,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锯齿式交战,多半也起因于小冰期南下的打劫。诸如西周的灭顶之灾,就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了最后一掌,即北方游牧族“犬戎”部,因被寒冷追逐而席卷了镐京。
韩非子在他的《五蠹》篇中说,尧治理天下时,人们“冬日麂裘,夏日葛衣”,想必在4千年小冰期以后四季分明,显然葛衣并非为御寒。
韩非子所说的尧之时虽然是神话时间,但大抵可以与考古或文献所呈现的4千年光景相呼应,同时期的埃及人已经能够生产精致的亚麻织物了,而且审美品位与现代无异,甚至更加绮丽。据说,在瑞士的一个干涸的湖底,也发现了人类使用的麻织物,恐怕这件麻织物难以抵挡北欧的冬寒。截至目前,葛麻是被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纺织物,而这种人类最早出现的织物却并非为御寒,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说人类穿衣戴帽的历史,始于以土石颜料涂身或羽毛饰头的话,这种审美性的装饰需求似乎更适于解读人类穿衣戴帽的起源。200万年前,当人类获得了直立行走的自由,视野便从二维的平面空间拓宽到了三维的立体世界。直立的人类,脖子可以扭上一扭,脑袋亦可上下左右灵活转动,天地瞬然开朗。这种视野自由带来的信息刺激,密集而丰富,使人的视觉感官能力不断增强,思维则开始对色彩、光线、形象等做出审美意识的敏感回应。想必这种回应大概与当下AI给予人类面临被超越时的惶恐、兴奋一样,人类再也不愿回到四腿爬行的低劣状态,哪怕被捷豹、猛虎吞噬,直立成为人的第一本质。
人类直立源于美的启蒙,在理性未萌、灵性充盈之时,人类的一切判断,皆基于灵性的审美需求。因此,审美与生俱来,作为人的本能,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第一属性,仍然是当下与未来直立人的终极标配。
人类从自然界向文明世界转化时期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创造,不同于自然进化,表现为人的“创造性进化”,而审美是“创造性进化”的第一动力。
“原始”是什么,是蒙昧吗?启蒙主义者历来这么认为。而我们不这么看,在我们看来,所谓“原始”,首先跟本原有关,其次跟原创有关,而原始人,就是直立本原,创造世界的人。
草鞋山人深谙草木之华给予人类共生的美意,凭借与生俱来的审美想象力,将葛藤创造性编织为人类的衣冠。我们还是不妨问一问,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失落了什么?如何将失落的原始性——创造与想象的本能找回来?
人之异于蛛织网、蜂筑巢,在于实用功能服从审美需求,行动追随想象,先在想象中形成,再将想象付诸实施。这样的活动方式是艺术,而其本质则为创造。通常,我们都说“劳动创造人”,当然不错,可仔细一想,蚂蚁、蜜蜂也都劳动,猴子采摘、狮子狩猎不也是劳动?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创造人”,而应该说“创造性的劳动创造人”。功能性必取悦于精神性,才有可能永恒。
创造,超越进化,进化是在自然的空间里进行,而创造则在想象的空间里展开,想象,并非来自进化,创造,也不是自然的成果。如果人类命中注定要从自然里面异化出来,那他就必然要从自然的产物变成自然的改变者和创造者,从自然安排好的食物链和循环圈里解脱出来,从而具有对自然作选择的自由,选择基于审美的需求。
考古学,不能太唯物,不要过于看重遗址、遗物的“物”的一面,那些不过是时间的碎片化存在。当我们面对三块碳化葛麻织物时,不妨问一问,人类穿衣,表达了一种怎样的超越的心情?无疑,他们又找到了一个人类自我意识的表达或叙事空间。
对于人类穿衣戴帽的缘起,从古希腊哲人始,争论到如今,有太多的丰富联想和说法,可以归类为以下五种。诸如保护说、羞耻说、吸引异性说、辟邪说、装饰说。除第一种“保护说”之外,其余皆与审美和精神相关联。
有时,思想的历史无法依赖历史的思想来表现,更何况那时又尚未思想,但人是自然的产物,当然得有个自然的形态;人还是自我的产物,还得有个超越自然的样子,索性,这副超越自然的“样子”便在创造中开启了。
人类为什么要穿衣服?因为审美。
当草鞋山人织布穿衣时,全新世大暖期环球同此凉热,但进化的步调却并非一致。在考古学的框架里,与马家浜人并存的河姆渡人、仰韶人、红山人、古埃及人、苏美尔人,以至于更多的史前人定居之地,如满天星斗,覆盖在地球之上,他们是人类第一代拥有审美意识的“造物主”,在创造中进化,第一个表达符号、第一件陶制水杯、第一座房屋、第一片葛麻布等等,在全球化的社会进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文化圈,表现为不同文化此消彼长,呈现出文化类型的样子,因审美而原创了人类不同的文明样式。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