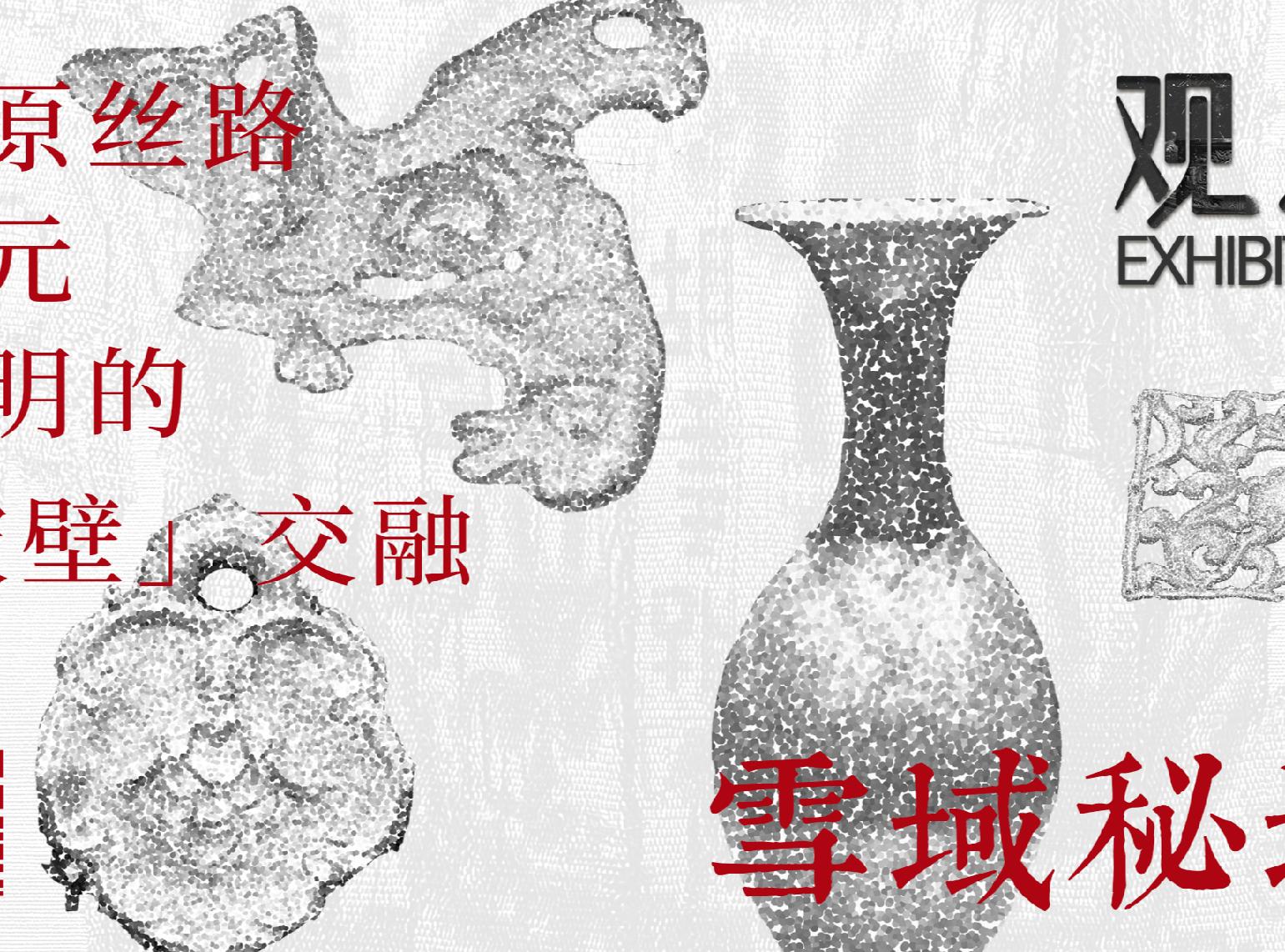我们要了一壶金骏眉。他看了看价目单,反复说,这个茶馆太贵了。
他叫张景,纪录片《寻找手艺》的导演、摄影、录音、灯光、剪辑、撰稿、旁白、调色、音乐、吉他、混音,及其他。感觉他身上有数不清的插座。
其实那天他带了一块来自云南勐海的古树茶饼。但这种茶是“慢”的,应该泡在紫砂壶里,让茶叶慢慢松开自己的手掌,一片片飘落下去。那是时间的重量,就像他拍过的那些手艺人。
我们还是喝了更方便的金骏眉。这是本世纪才问世的一种红茶“新贵”。
01
他曾经梦想拍一部“伟大”的纪录片。为此,他自筹资金,卖掉在北京的一套房子。他杜绝一切摆拍,全片随机,第一人称,诚实,素朴,自带毛边感。
太“狠”了。朋友这样说他。在很多人眼中,他固执,“就是一块硬石头”,一意孤行,已“无可救药”。
2014 年,他组建了一个非专业的 3 人摄制组:导演张景,录音兼“交际花”喻攀,司机兼临时摄影师何思庚。除了张景之外,都是地道的门外汉。何思庚的摄影兼职,还是在原摄影师有事退出后临时“试一试”的,后来人们的评价是:应该是摄影师当司机了。
他们所用的摄影设备,也是二手市场淘来的残次品。
就这样,他们凭着“伟大”梦想辗转全国,用 3 年时间,跨越 23 个省份,打造了《寻找手艺 1》。
《寻找手艺 1》一共 5 集,寻访了散落在中国各个角落的 199 位手艺人,记录了陶器、铜像、英吉沙小刀、印蓝花布、油纸伞等 144 项“老掉牙”的传统手艺。这是一个时间的幽暗仓库。仓库中的大部分物品,被时间的流水不断冲刷,即将化为乌有。那积攒了千百年的生活细节,正在一一消失。
手艺不是工艺,而是“上手”的,重在劳作,重在身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说的也是一门手艺。手艺是经验,是糊口的东西,但是也可以升华到艺术。那是简单生活的岁月,是人情温润的岁月,一代又一代的叠加。换句话说,那是农业社会的记忆。
如今,人人都忙着玩手机,谁还需要学手艺?
这是一个争先恐后、崇拜未来的时代,这种消失是不可逆转的。中国人骨子里的农耕基因,如应时、尚俭、循环、取宜、自足自洽、乐天知命等等,正在被“发展”彻底改变。利器取代了人力,求新、求快、同质化,摧毁了那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生活世界。“现代化”君临天下,我们最终要被技术统治,被数据统治。
回头是不可能的,也无法想象。变化,是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变化,是不是可以更精细一些呢?
张景和他的《寻找手艺》,想记录下这些已经“过期”、正在消失的生活细节。世界在前行,时代在翻篇,人们一直在“拥抱变化”,张景却一直在往后跑。他像是在跟这个时代拔河。
最后,他被拖拽了起来,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只风筝。

▲ 万能的喻攀

▲ 左为导演张景,右为“司机兼临时摄影师”何思庚

▲ 张景在拍摄中
十几家电视台都拒绝了他的片子。电视台更喜欢大团圆的调调。在他们眼里,这部片子跟那些民间手艺一样,不规范,不光滑,不平整。他只好把《寻找手艺 1》免费传到年轻人扎堆的B站上。没有任何推广,B站也不给任何宣传。
感谢互联网。他的片子收获了“新世代”的鲜花和礼赞。B站上有几百万人观看,仅弹幕数就有几十万条。弹幕是东亚文化独特的产物。他感受到了这些寂寂无名的年轻人的力量。“他们包括十多岁的青少年、在校大学生、文艺青年等,当然也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喜欢,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用为生计而忙碌的原因吧。”
最火的时候,他一个月内居然接受了四十多家媒体的采访。他被高校邀请前去讲座——我做过许多年的财经媒体,后来我才知道,拜金时代的大学生们,也并不是更喜欢听明星企业家的励志。他拒绝了央视的采访,但乐于接受大学生的采访。
片子获奖无数,他也拿奖拿到手软。“金鹰金鸡奖这些我没想过,我也从来没想过国外的奖,那是不同的体系。但我梦想的我全拿到了。”
由于口碑爆棚,《寻找手艺1》也实现了“逆袭”,有一些电视台买下播放。虽然不多,但已经给了张景足够的信心。
4 年后,他又借来 50 万元,找回了在香格里拉打工的喻攀,还有何思庚,买了新的设备,《寻找手艺 2》启动,“三人团”再次上路。
《寻找手艺 2》的主线是对《寻找手艺 1》的回访。但是张景的野心“膨胀了一百倍”。他希望《寻找手艺2》不仅再是一部电视纪录片,他希望它能在院线上映,并且取得一个亿的票房成绩。
在片中,我们又看到了那个有形有色、道法自然的中国。随机拍摄,会经常有意外的不期而至。悲欢离合,冷暖人间。土旦,李腊补,江庸次仁,胡大拜尔地,坎温,做枫香染的奶奶,每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旧世界。生活被时代推动,悄无声息地变化着,而他们的内心依旧安然、宽仁,逆来顺受,但,“什么事来了他们都能抗住。”
这可能就是中国人的“精气神”。他曾经向一位好兄弟讨教,怎么拍一部能影响中国的好片子。对方说,“很简单,你拍出中国人的精气神就够了。”当时张景并不知道“精气神”是什么东西。他还上百度,花了一个星期去看什么叫“精气神”。
他至今无法直接定义它。
他希望自己能改善这些手艺人的生存状况。他希望通过他的拍摄,这些素面朝天的手艺人也能被大公司签约,或者把他们的手艺品卖到全世界。
但事实证明,他拍的片子,不可能实现票房一个亿的梦想。甚至,当他把最终的成片送到各个视频网站时,就像两次踏进同一条冰冷的河流:通通被拒绝了。这也意味着他投入的那 50 万块钱,就此打了水漂。
有反馈说,片子太土了。土,是时尚、潮流的反面。它经常用来形容那些与大地距离最近的人们。这次被用来形容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所记录的人和事,和泥土基本是分不开的。因为大地是他们的母亲。
最后,他又把《寻找手艺 2》免费传到了B站上。
片子卖出去卖不出去是一回事,受不受观众待见则是另一回事。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豆瓣的分数有没有出来,“这个动作每天会重复好几次。”
《寻找手艺 2》也获得不少奖,但在当时的张景看来,豆瓣评分才是一部作品的最高奖。
喻攀有一天酒后电话:“你能不能更酷一点,不要管那些评论、那些弹幕、那些豆瓣评分……”
这个“质问”让他心头一耸:是不是还不够放开?是不是太在乎这些“虚无”的东西了?还没等他反驳,喻攀又说:“可是,好像除了这些,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他也在想,除了这些“虚无”的东西,还有什么呢?
后来,《寻找手艺 2》的豆瓣评分出来:9.1。而当时“大红大紫”的《寻找手艺 1》是 8.9。对于一个“草台班子”来说,9.1,已经足够高了。
他犹如坐上了高速盘旋的过山车,体验着失去重心的眩晕与恍惚。
03
2014 年之前,他和老婆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两辆车、两个可爱的女儿,年收入三四十万,看上去,一切都还圆满。
但是《寻找手艺》一路拍下来,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窘。全家靠借钱过日子,而老婆的信用卡早就停了。最穷的一个月,全家 4 口人的生活开支是 2700 多,如今,他们一个月 1 万左右,“紧一紧是可以过的。”
而在没拍《寻找手艺》之前,他们每个月的开支是 2 至 4 万。
“贫穷”会限制很多人的想象力。但这不包括张景。他似乎“被海浪托着”,再次上路。这是《寻找手艺 3》,66 人掏钱支持,总共 12 万多一点。有几百个人帮他找选题,靠谱的和不靠谱的,他天南海北一通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寻找手艺 3》的团队,由“三人团”变成了张景一个人。单兵作战,好处是来去自由,坏处是手忙脚乱,而且让这次拍摄看上去有些随意。他“无限怀念”喻攀和何思庚,但 12 万块钱显然无法养活 3 个人。而他已经停不下来,只能孤独的一个人上路。
“想想都觉得刺激。”
从“三人团”时代,到“一个人的战斗”,他自己的那个“伟大”梦想,磕磕绊绊地实现了。但是他发现,他并没有给那些他拍摄过的手艺人带来境遇上的改善——即便有改善,也是因为外部大环境的改善。“我帮不到手艺人,自己也越来越穷,而且穷的状况我自己短期内也没法解决,怎么办?”
他失眠,忧思百结,陷入到了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当中。那时他仿佛站在珠峰的北坡上,他是一个登顶的人,但是他想纵身跳下去。
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十天。这天,他无意中去看了一下他的的片子,一条弹幕像流星一样划过,“那条弹幕把我彻底救醒。”
此前,网上的评论他几乎从来不去看,他怕自己被人左右了。
“一个新疆吹巴拉曼的,有可能他是唯一的传人,周边除了他没有别人了,我拍完他以后没几年他去世了。我没有去做统计,我只能猜测,如果我没有拍他,也许这个手艺就失传了,但是那条弹幕说:我按照这个想法做了一支,我居然吹响了!”
他说的这位老人,就是牧羊人胡大拜尔地。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维语意为“上天赐予的”。在片中,胡大拜尔地的儿子试着想吹响父亲那只巴拉曼,一直没有成功。
当时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一下子被提起来了。老人的儿子都吹不响的巴拉曼,在内地却有一个年轻人按照老人的方法把它做好了,吹响了。这意味着以后谁想按照那个方法做,就有可能做成、吹响,意味着他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巴拉曼就可能不会失传了。
看到那一条弹幕,他眼睛湿了,“觉得我值了,还有很多可能因为我的拍摄带来的那种积极的影响可能我还并不知道”,“我没有改变手艺人什么,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留下来了,我真的可以给这个社会留下点什么了”。
是记录,而不仅仅是去感怀。还是要做下去,还是要正心诚意地拍下去。拍下去,也意味自己的生命在不断延续。
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梦想”?——而不是拿到多少奖杯、赚到多少钱。

▲ 吹巴拉曼的牧羊人胡大拜尔地

▲ 胡大拜尔地的弹唱,在张景的眼中碾压了一切“专业”歌手
04
他从小在湖南西部的一个小山村里长大。小时候他随考上大学的父亲来到长沙,全家挤在一个十多平米的房子里面。“成绩又不是很好,所以是极度自卑的。”
他真正建立起“信心”,还是高中时的一次骑自行车远行。那是 1993 年冬天,春节后不久,从长沙到北京,他整整骑了 12 天。名义就是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他最大的收获是要来了张百发的题词。
班里成绩最好的以及家里最有钱的同学,一开始都说要一起去,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成行。他用这次“又疯又傻又魔怔”的远行,“打倒”了成绩最好的同学和最有钱的同学。
他是在杭州读的大学。1997 年暑假,他又从杭州骑车到新疆霍尔果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交界。那一趟,他骑了 58 天。他如今是光头,他的朋友笑说,他的头发就是那段漫长旅程中被“烈日灼焦”至没的,但因此变得更加有味道。
钱是从同学们那里搞到的。他在学校端个纸箱,写上“我要骑自行车穿越中国”,见人就堵。他们学校小,才 600 多人,几乎彼此都认识,最后居然搞到了几千块钱。他说,他在那个时候就学会了“厚颜无耻”。
果然是一个“吃得苦、不怕死、霸得蛮”的真湖南人。
他骑车经过了不同的“世界”,见过了不同的生活场景。人们也许生活在海边,也许生活在草原,也许生活在沙漠,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会充分利用身边的一切自然之物让自己生存下去。越是偏远农村,现代化抵达的速度越慢,就越能保留原始的生存技巧,自给自足的能力也越强。
这个年轻人,穿越了一个古老中国。
而在央视那些年,由于职业关系,他再次跑遍全国。当时“农民兄弟”招待他的是各式各样的茶、各式各样的杯子,他还能见到种类繁多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这些东西会直接连通他小时候的生活记忆,充满了温暖。
然而这几年,工业化直接抹平了人们的想象。他再到农村去,“看到最多的是‘营养快线’这类饮料和一次性的塑料杯子”。人们好像活在一个雷同的空间里。“乡村的人口也越来越少,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赚钱了。老人们身怀古老的生存技巧,但大多数时候用不上,需要什么东西,让他们在外赚钱的儿女们买来便是。”
“少年中国”终于彻底成为我们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在这种价值体系下,一切必将焕然一新。
而这个乡村少年已步入中年。进入城市三十年,他已经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他现在无需也无法将他的山林生存技巧传授给他的孩子们。而孩子们也用不上这些了。
“但是,这些智慧至少可以作为影像保留下来,毕竟正是这些智慧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千年。我们也有必要让孩子们知道,中国,远远不止你身边经常看到的那些现代文明。”
这是《寻找手艺》的精神起点。
05
现在,他已经拍完了《寻找手艺 3.5》和《寻找手艺 3.9》。他在 3.5 中展示了自己“搞钱”的“手艺”,就像大学时期“厚颜无耻”端个纸箱化缘类似,兄弟们你三万我两万的, 凑了 13 万。
在 3.5 中,他的老爸老妈扮演了喻攀的角色,寻找拍摄点。从某个角度说,效果甚至比喻攀还要好。他原来以为老爸上过大学,文化水平比较高,在外面肯定唱主角,没有想到的是,只上过三年学的老妈却主动得很。老太太像一个孩子一样睁大了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
3.9 也是“顺手化缘”。出乎很多人意料,他去拍书法,“是一个极其枯燥的片子”。3.5 的点击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3.9 也可想而知。不过,他已经越来越不管受众的感受了,而是首先让自己“舒服”。他相信只有首先感动了自己,然后才能感动别人。
此前,有朋友一直劝他,张景你妥协吧,人家电视台让你怎么改你就怎么改,至少你还能播出,否则砸在你手里。
但是他没有。“搞钱不难”,让他妥协很难。其决绝,如同一块天外飞来的顽石。
“我想挣钱吗?当然想,但一定不是以纪录片挣钱。我在做的时候一直告诉自己这不是挣钱,不是挣钱,不是挣钱,是要寻找一种价值并且传递出去。这样才有可能把纪录片做好,否则的话你根本没可能。”
不过他有一个底线,“无论任何时候,我这片子要适合我两个闺女看。”于是,他的两个女儿,张涵一和张艺以,担任了这部片子的“艺术总监”。
人到中年,每天都是闯关。他不是天生的苦行僧。他觉得应该把家里的生活费先挣个两三年,为此他想要商业合作了。他欠了一百多万的债,这让他内心压力很大。他得先把债务解决了。其实对他而言,这不是太困难的事,只是需要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个时候,“那个电话响了”。
所以他一直坚信自己不会被饿死。往往在青黄不接、弹尽粮绝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点支持过来,总能绝路逢生。这次是一位明星,表示愿意支持 30 万。“由于还在协议阶段,所以还不能说那个明星是谁,万一人家突然后悔了也不能怨人家。”
如果一切顺利,《寻找手艺 4》就准备开始上路了。这一次,他希望“重招旧部”,找回万能的喻攀,找回何思庚。
“即便这位明星不支持,但因为有这个电话,我就知道,老天爷不是让我放弃,是在考验我,我差点没经受住考验。老天爷觉得这小子跑偏了,你快去给他打个电话把他拉回来,所以这个电话大于 30 万。”
一条弹幕,一个电话,就已让他满满的力量感。他决定,他还是要做他该做的事。他已经 46 岁,他说,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感觉都是在写“遗书”。
他有很强的年龄感。大概从 40 岁开始他就害怕死亡,感觉这位不速之客正在向自己慢慢走近。“就觉得人都快死了还妥协什么?”
在他拍的片子中,有的老人不再出售自己的作品,而是将那些物件菩萨般供着,或者留给后代。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手艺人。
就应该一直“做做做”。

▲ 雕版手艺人江庸次仁



▲ 新疆,制作英吉沙小刀的麦麦提克日木。以前看到精美的英吉沙刀,总认为刀柄的花纹是工业化制作的,或者整个刀都是工业的产物。直到亲眼见到,才相信这全是手工一点一点制作出来的。无论是贝壳纹还是铜丝花纹,每一种颜色都是一种不同的材料,且基本都是废旧物品的再利用,比如听装饮料的铝皮、铜片、不同颜色的塑料片,然后通过镶嵌、热焊、胶水粘贴等方式组合成一个整体,最后再整体打磨、抛光


▲ 贵州,用土法造纸的真、养号两位老人


▲ 云南勐海,做油纸伞的傣族老人坎温

▲ 李腊补老人和何思庚。老人开朗、健谈,他屋里挂着的二胡、三弦、葫芦丝等乐器,都是他亲手制作的。他最擅长的是水鼓制作

▲ 山东高密,雷英华和她的面花

- 那段旅程才是《寻找手艺》的精神源头
搜神记:你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换句话说,我想知道《寻找手艺》是怎么来的。
张景:我考大学考了四次才考上,复读了三年。当时我复读班的一个好哥们儿,他说这样考大学太难了,他有个照相机借我用,我买了一两个胶卷学会了照相,陪他艺考考摄影,他没考上我考上了,然后就走入这条道了。如果说我第一次考大学就考上了,应该不会干这行。我是靠摄影考上去的,不过小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因为觉得记者主持公道,有那种正义感,所以就进入了这个行当。这么说行吗?
搜神记:你年轻的时候好像有段骑自行车穿越全国的经历,我觉得这对《寻找手艺》这个片子非常重要。
张景:那应该是我人生真正的一个“自信”的转折点。我是从山里面出来的,十一岁之前都没见过电器,十一岁从山里第一次来到镇上,在一个餐馆里看到一个东西在头顶上“呼呼呼”转,我想这玩意儿是什么?电扇,站在底下可凉快了!大老远那个车忽的就过来了,速度居然这么快!我当时觉得这个世界太神奇了。后来我爸考上大学了,就把我们整个家庭从山里面带到了长沙。但我完全没见过世面,我小时候在长沙有个外号叫“乡里宝”,这比说人“乡下佬”还要低。说一个人宝里宝气,傻里傻气,绝对的贬义。所以我一直很自卑。一直到 1992 年还是 1993 年的时候,那时候北京刚把亚运会办完了,正在申办奥运,头一次没成。全国热情很高,当然也包括我。我虽然是农村孩子,但是对这种东西也很热血。当时特别崇拜一个人,就是北京市市长张百发,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亚运如果申办不成功,我就从北京最高的楼上跳下去。我当时就觉得身体上某种东西被他点燃了,就和我们班上另外两个哥们儿商量说,我们寒假骑自行车到北京去,看能不能见着这位市长,用我们的行动支持北京申办奥运。就这么决定了。
搜神记:很英雄主义。
张景:对,觉得身体里有种东西在燃烧。现在看来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一个行动,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感染了很多人。过完年了,我给那哥们儿打电话说,咱们走吧!其中我们的班长说,天啦,你真的要去?我说,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他说,不会吧,我都没想过真的要去!他就不去了,我就再给我们班上另外一个家境最好的同学说,哥们儿,咱们走吧!结果他也同样惊异地说,天啦,你真要去?他就也不去了。那怎么办?最后决定自己一个人去。
回来以后,我就成为我们学校的英雄了,电台电视台也给我报道了,后来我还成立了一个自行车队,有五百多个队员。为什么说这件事情给我一个极大的信心、是我人生一个转折点呢?因为当时觉得,我们班成绩最好的班长没做到,我做到了;我们班上最有钱的同学没做到,我做到了。当时各种媒体对我的关注,让我从一个特别自卑的孩子一下子冒出来了,然后心里就开始有自信了。此前家里穷,从农村到城市,我爸一个人的工资三十多块钱要养活四个人,全家挤在一个十多平的房子里面。我成绩又不是很好,所以是极度自卑的。我就感觉到我用这一件事情“打倒”了成绩最好的以及家里最有钱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
搜神记:骑自行车到北京,有什么奇遇?
张景:有一件事情最难忘。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想见张百发。先是在市政府门口堵了一天,人家说小伙子,你别在这儿等了,他在奥组委。那我也进不去,就在外面堵。有一次我看见他了,车出去了,我跟他招手,他没看到我。我守了三天,没“逮”着他,没钱了,只好就回去了。但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居然回了。他问我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您给我题个字就行,就很小气地弄了个名片那么大的小纸片给他寄过去了,他果真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争办奥运,为国增光,张百发”,用北京市政府的信寄过来,发到我学校传达室。结果一下子就轰动了。
搜神记:你的人生曾经“辉煌”过啊。
张景:那一趟其实很艰难,因为在冬天,中间有想过放弃,因为太冷了。当时没有常识,但是我把它完成了。后来又骑自行车,花了 58 天时间把全国穿了,从杭州(当时我在杭州上大学)骑到了新疆霍尔果斯,那时是大二。
搜神记:经费怎么办?
张景:那个时候我就学会了“厚颜无耻”,在学校端个纸箱,写上我要骑自行车穿越中国,见人就堵。我们学校小,才 600 多人,几乎彼此都认识,最后居然搞到了几千块钱。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的《寻找手艺》 3.9 全是用这种方式。搞钱不难。
搜神记:但我知道,现在有些钱你是不要的。
张景:对,我拒绝的钱远远大于我搞到的钱。如果再年轻一点可能会把这个原则放松,因为现在 46 岁快 50 了,总觉得有些东西再不坚持一点,人就没多少年可以活了,就会留下更多的遗憾。我跟阿钟(歌手钟立风,我们共同的朋友——编者注)在外地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是晚上,忘记是我问他还是他问我了,“你害怕死亡吗?”——当时我俩一下坐起来了,感觉心里非常隐私的东西一下就被戳中了。我再回忆自己,大概从 40 岁开始就害怕死亡,感觉死亡正在向自己慢慢走近,就觉得人都快死了还妥协什么?所以当时给自己立的标准就是基本不妥协。但有时想想也后悔,比如拒绝了几百万的时候。当时觉得自己有几百万找我,后面可能有更大的,拒绝了吧,但是现在根本没人理我,就觉得当时太傻了。
搜神记:这好像也说到我的痛处了。当年自己做事情,给自己定下很多框框,总觉得未来会有更大的钱来找自己,就会拒绝一些眼前的利益,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太傻,哈哈。你年轻的时候骑自行车穿越中国,我也干过类似的事,风餐露宿,但是行程不如你远,也没啥心得。而你去了很多地方,见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和事情,发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那段旅程才是你《寻找手艺》的精神源头。
张景:对,发现很多。走了那一遍,百分之七八十是农村,所见所闻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是吻合的,但是又有新鲜感。那些人的眼神,你可以理解成抠抠搜搜的,甚至可以用呆滞来形容,一定不会看得很远,至今为止我们村里很多上年纪的人目光都是那样的,我一路发现全是那种。但是你也可以理解成质朴。他们会充分利用身边的一切自然之物,让自己生存下去。他们会制作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自给自足。他们用的工具让我想起小时候。制作这些工具的手艺人,在我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
搜神记:在人类发展史上,我们今天追认的那些伟大艺术家,其实大部分就是工匠,就是手艺人。比如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其实就是金匠、木匠、铁匠。
张景:是这样。在我们村里比较聪明的人才会点这个东西。但他首先就是干活的人。
- “我的指导思想是《道德经》”
搜神记:你说曾经“梦想”拍一部伟大的纪录片……
张景:我是从很偏远、很穷的地方出来的,所以我的梦想并不太高。后来进了央视,看到很多同事橱窗里那些奖杯,羡慕得一塌糊涂,也把自己的要求提高了。但是现在这几年,我的《寻找手艺 1》把所有这些全给我带来了,我想获的奖,国内的奖都拿到了。顶级的金鹰金鸡奖这些我没想过,我也从来没想过国外的奖,那是不同的体系。我梦想的我全拿到了。大概半年前,我突然抑郁了,短期的,有二十多天,失眠。觉得我人生没意义了,为什么?我的梦想全实现了,感觉就是在珠峰上,我下一步要往哪儿走?当时就觉得从那个坡上跳下去,这个方法是最容易的,但是还没到死那个程度,就是觉得毫无意义了,太没意思了。
搜神记:你可以从珠峰上下来,再去攀登另外的高峰啊。
张景:这里有一个前提是,我自己的梦想实现了,但我拍的那些手艺人,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改善。我拍过的 90 %的手艺人,生活得到了改善,但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人家都不认识我了,他们生活好转全是因为这个大环境,最后我发现我算个屁,我想帮这些手艺人,后来发现根本帮不上。我总以为自己的力量足可以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做点什么,一开始把自己看得特别伟大,无形中把自己放得很高很高,结果跌落感非常强烈。这人生往后怎么办?我帮不到手艺人,自己也越来越穷,而且穷的状况我自己短期内也没法解决,怎么办?你说从珠峰上下来,再去爬另外的高峰,我就想到站在珠峰北坡上砰地跳下去。
搜神记:你是说,手艺人的生存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张景:我说是国家的大环境使然,没有一个记者相信,他们总觉得手艺人还是很可怜的。实际上我拍过的至少一半以上的手艺人经济状况比我要好。我的梦想实现了,又很穷,又不想回去赚钱,那种感觉……就伴随着失眠,就是抑郁了。
搜神记:好在时间不算长,不到一个月。转机是怎么出现的?
张景:有一天我无意中去看了一下我的片子,我看到一条弹幕,那条弹幕把我彻底救醒。就那一条,一个新疆吹巴拉曼的,有可能他是唯一的传人,周边除了他没有别人了,我拍完他以后没几年他去世了。我没有去做统计,我只能猜测,如果我没有拍他,也许这个手艺就失传了,但是那条弹幕说:我按照这个想法做了一支,我居然吹响了!当时我觉得“噌”的一下被提起来了。吹响了,意味着他做好了。老人的儿子都吹不响,在内地有一个年轻人按照老人的方法把它做好了、吹响了,意味着以后谁想按照那个方法做,就有可能做成、吹响,意味着我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巴拉曼就肯定不会失传了。我当时就觉得,我没有改变手艺人什么,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留下来了,我真的可以给这个社会留下点什么了。
搜神记:这才是你真正的梦想,而不是得到多少奖杯。
张景:是,我才觉得我的梦想是真正实现了。我能做的,不是去改变手艺人,而是真的可以把这个东西留下来。我就觉得我还是要做下去。二十多天的抑郁、压抑就没了,又开始有动力了,又开始觉得我还是要拍下去。就那一个陌生人的一条弹幕救了我,很偶然,像流星一样一划而过,那种感觉无法形容,看到那一条我眼睛湿润了,觉得我值了,还有很多可能因为我的拍摄带来的那种积极的影响可能我还并不知道。因为网上的评论我几乎从来不去看,我怕被人左右了。
搜神记:我倒是去看过几千条弹幕。我是去看这些年轻人在说些什么。
张景:我的片子还救过我身边一个哥们儿的命,是我初中同学。他在县城里开了一个歌厅,黑白道通吃,是县城生意最好的一个歌厅,一年有几百万收入,有时一天的纯利有五万。后来环境变了,白道根本就不能碰了,他的生意一下就掉下来。他就觉得是自己的装修太老了,就把赚的钱全部用来翻新装修,结果仍然是那样。他从我们县城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变成了负债累累的人。他人很仗义,等到把钱还得差不多了,就想到一条道,死。他不会游泳,他找到县城一个桥边上,那里水最深,死过很多人,他就想从那个地方跳下去。跳之前他看了一下手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去死的,一看时间又该去接女儿放学了。他想,那我先把女儿接了改天再去。到了晚上肯定是失眠了,想到我曾经给他一部片子,要不再把兄弟这个片子看看。他一看片子,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生存,他把其中一个雕版艺人叫江庸次仁的片段来回放,反反复复不下十遍,一边哭一边看。他从那里面找到了他生存的动力。第二天他跟我说,为什么你的片子被电视台拒绝了?然后他让身边的朋友去看,结果他身边朋友发现不错啊。他在当地还算比较有实力的,他找了四所学校,二十九个班,让孩子们去看,结果孩子们反馈也不错。他给了我这么厚一摞调查表,给我的打分,8.33 分。他做这么一件事情,把我也救活了。我没有承认失败,但是所有人都在劝我说,张景你妥协吧,人家电视台让你怎么改你就怎么改,至少你还能播出,否则砸在你手里。但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结果这哥们儿给了我十多斤调查表,就相当于救了我。然后我再把调查表给我身边的兄弟,说这不是片子出问题,可能是电视台出问题了,然后在地面开始推广。
搜神记:你过去在央视什么部门?
张景:我一直在电视台做……也叫纪录片,但是我从来不觉得那是纪录片。包括Discover、BBC那些,我不认为那是纪录片。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摆拍,几乎每一个步骤都是摆拍。当然也有抓拍的。我原来是央视体制里面的,摆拍我也很在行,但是总觉得它不对,我觉得那不是纪录片,你可以叫做专题片,那是为了你想象的目的,在真实的基础上组织别人来扮演角色做了一个伪纪录片。所以在我拍《寻找手艺》之前,基本上没有出成片。拍野生动物不存在摆拍,按我这种风格做出来居然还可以,而且后来一直是我们那个部门的一个“编外样片”。比如来新人了,就把我那部片子拿出来,是在鼓励新人敢于创新的时候拿出来。
搜神记:你有宗教信仰吗?
张景:我算是有,但不是那种……因为在很多人那里佛是一个很高的存在。然后我说我就是佛,你也可以是佛。我现在是佛道混了,相信人之外有一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包括我现在看八字,我通过他的出生年月日,我就知道他的性格,这是看八字最基础的,这是道家的,但在佛家的密宗里面也是相通的。后来我又信了道教。包括《寻找手艺 1》,我的指导思想是《道德经》。到现在为止,我做什么东西仍然是只有方向、没有计划,无为而为,但是一定会做。包括商业合作要拍摄纪录片,我也是没有计划的,会失败吗?也许会失败,会成功吗?也不知道,但是我会一直做。这是道家对我的影响。这算是信仰吗?
搜神记:算是吧,没有什么钱,如果再没有什么信仰,就做不成《寻找手艺》这件事,做不了这么久。
张景:大概半年前,我有了一个新的体会。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铁定要做的时候,而且你知道有大部分人并不认同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不要说出来。因为你一旦说出来,你要跟别人讨论,实际上你想得到别人的认可,但别人觉得这个傻子肯定失败,潜意识里认为这个人肯定不成。虽然这是人家很小的念头,如果是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有这种不成的念头,那你这事就成不了。
我一个大学同学学佛学了六年,有一次我跟他谈我的感受,一个佛像为什么有力量?可能并不是佛像有力量,而是拜佛的人觉得它有力量,一万个人觉得它有力量,就把新的力量赋予它,然后再有人去求它,就会形成一种共振。他突然就哭了,说这是谁告诉你的,你太有慧根了。我其实就是自己感受到的。然后突然觉得,原来我这就叫有信仰了。我就觉得我也是佛,每一个人都是佛,就看谁的心力大。佛教道教不是说有个神在那里,而是有一股谁也看不到的力量,我们可以把它定位为佛或者道,但这个力量左右了我们,也左右了我们的意识,包括我们学八字,我们知道八字就是意识。

▲ 新疆,花毡,一种类似地毯的东西
- “我相信我不可能会饿死”
搜神记:刚才说到,你想拿的奖、该拿的奖也拿了。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奖?
张景:其实没有目标,大概就是我同事以前曾经拿过的奖我拿了,而且同事以前在台里拿了奖之后,奖杯和证书是不能拿回家的,只能放在单位橱柜里,我的全部能拿回家,天天看着好美。
搜神记:那对豆瓣评分会重视吗?有人觉得那个才是最高奖。我看了一下《寻找手艺 2》的豆瓣评分:9.1。
嘉宾:你这样说也算是。但现在我正在努力摆脱豆瓣评分以及观众评论对我的影响。2017 年火了之后,本来就已经很飘了,好不容易下来了,因为现在没人搭理我了,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了,别又给我一点评论抬上去了。就是说,我可以给这个社会留下点什么,但给这个社会带来改善的动力远不如以前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力量没那么大。
搜神记:你对《舌尖上的中国》怎么看?对你有影响吗?——你的前同事们做的。
张景:我是坚决抵制《舌尖》的,因为我是从那里面出来的,恰恰是反它的。也没想跟《舌尖》比,自己的力量差太远了。但是《舌尖上的中国》一部片子,改变了整个中国人对纪录片的这种认知。本来纪录片没人看,《舌尖》相当于一块石头往那个水里扔了一下。我很感恩《舌尖》,包括陈晓卿老师,因为他们制造、培育了一个良好的土壤,没有《舌尖》就没有我的纪录片。每个做纪录片的人都在享受《舌尖》带来的福利,不管他承不承认。
搜神记:《舌尖上的中国》也说明,目前只有食物、味觉才能把中国人团结在一起。投资这样的片子才安全,才有可能赚个盆满钵满。而《寻找手艺 1》、《寻找手艺 2》、《寻找手艺 3》,它们都是收不回成本的。
张景:包括现在正在做的叫 3.5、3.9,我已经彻底不考虑收回成本。谁要资助我的片子,我首先告诉他这肯定是不能赚钱的,你要想好。还有就是我的片子是没有拍摄计划的,有可能失败,你要考虑这一点。你能接受这两点那你就投我,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赚钱就免谈。所以商业的基本都拒绝了。
搜神记:可是有了钱,可以把《寻找手艺》做得更好啊。
张景:我想挣钱吗?当然想,但一定不是以纪录片挣钱。我在做的时候一直告诉自己这不是挣钱,不是挣钱,不是挣钱,是要寻找一种价值并且传递出去。这样才有可能把纪录片做好,否则的话你根本没可能。
搜神记:年轻人反响强烈,你感到意外吗?
张景:本来以为这部片子最能引起与我有类似经历或者相仿年纪的人的共鸣,后来发现最喜欢这部片子的居然是年轻人。他们包括十多岁的青少年、在校大学生、文艺青年等,当然也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这两个年龄段的人喜欢,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用为生计而忙碌的原因吧。
搜神记:你理想的目标受众是什么群体?
张景:我越来越不管受众了,越来越让自己舒服,因为只有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别人,没有想过要讨好谁。最开始是有讨好的成分的,包括 3.5。
搜神记:3.5 的效果怎么样?
张景:《寻找手艺》 3.5,现在已经发布了,发布一两个月,点击量才四千多,非常非常私人化的一个产品,没有任何计划,从出走第一部就已经做好失败的准备了,但是就是往前走,没考虑我的受众是谁。有一个底线,无论任何时候,我这片子要适合我两个闺女看。
搜神记:那你现在拍片子又没钱了。
张景:生活上也快没了,我现在穷得要死。不过这就是我有信仰的一个好处,从小到大,捡过垃圾吃,在马路上睡过,但是每次都会绝处逢生,所以我相信我不可能会饿死,总会在快要揭不开锅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点点支持过来,所以生计上我不担忧。前段时间,我这边弹尽粮绝了,突然微博上有一个陌生人,说是易烊千玺的粉丝,要资助我拍片子,然后我说好啊,我接受,但是一千块钱以下我不要,我懒得去惦记,十万以上不要,我会有心理负担,这中间随意,你捐多少我要多少,最后他资助了两万一千多,最后的要求就是出现“本片由×××资助”的字样。哪怕你捐一千块钱也会。然后我一下就缓解了。
搜神记:这是资助哪部片子?
张景:相当于他们资助了我的《寻找手艺》3.9,他们是最大的资助方,3.9 总共才花了两三万块钱。3.9 我是拍书法,是一个极其枯燥的片子。
搜神记:书法是艺术之极,它还被称为“中国式瑜珈”。我很好奇你会怎么拍。
张景:我定了一个目标,至少未来五年之内,关于书法的纪录片我这个应该是最好看的,而且比之前任何一个关于书法的纪录片都要好看,有感染力,有生命力。关键是它能对书法在老百姓之间的普及起到作用。我以前是书法盲,从来没写过毛笔字,我拍的这个老师就在七天之内,让我不光对书法有一定审美,还要爱上书法,还要能临摹出一幅像模像样的字。七天我居然都做到了,然后把整个过程拍下来了。当然很枯燥,但也有办法解决。
搜神记:你相信你不可能会被饿死,是因为还没有被饿死。
张景:我前面讲过,我经历了二十多天的郁闷之后,一条弹幕把我救活了,但那只是精神上,我不再悲观了,事儿还要做,但是没钱怎么办?我已经想好放弃《寻找手艺》了,这个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已经尽了最大能力了,老子不搞了。我要开始接商业的了,因为有一些也约了好久了,我随时可以去接。我就开了辆车,从北京往上海去,看看怎么能挣钱。结果开出北京才五个小时,到了山东境内,我接到一个电话,“您好,请问您是张景导演吗?我是×××经纪人,您现在还拍《寻找手艺》吗?”我说,“想拍,我现在想放弃了。”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一,没人看,二,没钱。”他说,“如果你还愿意拍的话我们愿意资助你。”当时我就停车了,我说,“你稍等一会儿,别挂电话,快到服务区了。”然后把车开到服务区,整个人又重新燃起来了,不行,我不能放弃,才七年,怎么也得熬十年,哪怕没有多少人看。因为我现在落差太大了,《寻找手艺 1》点击量将近一千万,关于这个片子乱七八糟的报道出来后,包括那些短片的综合点击至少超过一个亿,可到了《寻找手艺 3.5》的时候,只有四千多点击量,我就觉得这已经失败了,家里也开始出现问题了,老天爷是不是劝我别太固执了?适当的时候你还得回到凡人,把自己先养活了,把家里的生活费先挣个两三年。我还欠了一百多万的债,这个对我内心压力很大,家里饿不死,但是债务拖着很难受,我得先把债务解决了。我就开始找哥们儿,想要商业合作了,这时候那个电话来了。但是现在还在协议阶段,所以我不能说那个明星是谁,万一人家突然后悔了也不能怨人家。他任何时候后悔都行,就算签了协议只给一部分钱,那也不能怨人家,就像答应了给你三十万支持你拍片子突然不想给了就怨人家,那也不行。但这件事情就在告诉我,老天爷没让你放弃,你怎么就放弃呢?小子,咬紧牙,别放弃。
搜神记:这是什么时候?
张景:就几个月前。如果一切顺利,《寻找手艺 4》就准备开始做了。即便他不支持,因为有他这个电话,我就知道,老天爷不是让我放弃,是在考验我,我差点没经受住考验。老天爷觉得这小子跑偏了,你快去给他打个电话把他拉回来,所以这个电话大于三十万。再加上前面说的那条弹幕,已经让我知道,我在做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为我自己而做的,是有意义的。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唯心?但它们的确给了我很强大的力量感。

▲ 手艺不是工艺,而是“上手”的,重在劳作,重在身体
- “你拍出中国人的精气神就够了”
搜神记:拍《寻找手艺》,你走了这么多地方,你认为跟你最有缘分的地方是哪里?换句话说,你觉得你精神上应该是哪里人?
张景:我精神上应该是川西藏区的人。都说我前世是一个修行的喇嘛,我深信这一点。我心很善或者很软弱。我到了藏区没有陌生感,包括见了活佛,所有人都是跪着,我进去以后根本没想跪他,我觉得我跟他是平等的,临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人,我跟活佛点头微笑,他甚至露出了调皮的笑容,好像在说,小子,你这种感受是对的。当然还有很多。包括有一次在川西一个寺庙里面,大清早我起来了,寺庙后是一个山,我想到山上去看看,没有人走的道,全是狗走的,有好多野狗在那里,刚开始往那里走的时候狗就一直叫,我就把手这样(安抚状),告诉它们我对你没有伤害,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果然就安静下来了。逛了一圈下来以后喇嘛问我去哪儿了,我说去后面山上了。“你去后面山上了!那儿被狗咬死过好几个人,都是藏族的,你一个汉人你还过去了。”我说,“没有啊,上去的时候狗就很安静。”他就很惊讶。我对川西特别有好感,每次到了都有点回家的感觉,而那个环境也能接纳我,所以我觉得我精神的故乡应该在那儿。
搜神记:有点神秘主义的色彩。
张景:有天下午我在德格印经院丢了一个镜头盖,第三天我把该拍的拍完之后,在走的时候,在县城的主干道上,那个镜头盖出现了。我当时朝印经院和寺庙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依依不舍,再扭过头,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我的那个镜头盖就出现了。一捡起来从脚到头麻了一下。镜头盖干干净净的,三天车来车往没有粘上一点点土,但是上面有一个脚印,感觉比刚出生的婴儿的脚还要小,很神奇。回来以后身上就有刚才我跟你说的那股能量。
搜神记:你拍的人物,感觉都有一种逆来顺受的味道。
张景:我也是逆来顺受。我有时候觉得,拍他们其实跟拍我自己是差不多的,而且这几集拍完之后,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手艺人,而且是手艺人里比较固执的。逆来顺受是有什么东西来了,我就承受,但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你什么事来了老子能抗住,而且我不在乎你,我一直做做做。
搜神记:这才是劳动人民的性格嘛。
张景:你说这个我想起我的一个好兄弟,他已经去世了,是他把我引入道家这里面,到现在为止《寻找手艺》这个大方向仍然是他给我定的。我当时向他讨教怎么拍一部能影响中国的好片子,他就说,“很简单,你拍出中国人的精气神就够了。”当时我并不知道精气神是什么东西,我还百度,我花了一个星期去看什么叫精气神,当然都解释得很肤浅,但是等我把《寻找手艺》做完之后,我发现《寻找手艺》做到了,到底中国的精气神是什么?不好说,但是我的《寻找手艺》每一部都做到了。
搜神记:这种精气神无法言传?
张景:对,包括江庸次仁,典型的逆来顺受,包括山里边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他们都有那种无法言传的精气神。
搜神记:所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张景:有这种感觉。我这哥们儿跟我说,价值体现要聚焦中国人的精气神,在方法上,现在主流怎么做,你反着来。“反者道之动”。做纪录片的“道”在哪儿?一是自己从《道德经》领悟,还有就是我这个哥们儿对我的启发。我是慢慢感受到,纪录片没法挣钱。谁也不能通过纪录片主动地给自己带来名誉,纪录片的“道”就是传递一种价值,保留一种价值。守住这个才有可能得到一些名誉什么的,但是这个一定不能在自己的设想范围里,一旦这个片子想去牟利,一定做不到。
搜神记:当年你的《寻找手艺 1》也想去赚钱。
嘉宾:《寻找手艺 1》改了六十多遍,修改过程中,我把《道德经》通读通看,看了十七遍。每一句解说我都要反问一下自己,你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你是想证明自己还是想干嘛。每句解说都要反问自己一下。看《道德经》花掉的时间要比剪辑的时间还要多,每天睡觉之前必须要看《道德经》。现在已经延伸到《阴符经》了,它比《道德经》更狠,《道德经》泛泛地教你怎么打世界,《阴符经》则告诉你打世界的锦囊秘诀。我跟他们提到这个没人相信,没人相信《道德经》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道德经》我已经看坏三本了,家里一共有七八个版本,国外的版本、吕洞宾的版本、王弼的版本、任法融的版本,23 岁死掉的王弼那是最好的,好多个版本,通读,对照,看他们怎么理解,也许我确实还算有点慧根,会有自己的一些领悟。这是不是有点狂了?人家会觉得这小子怎么这么狂?

▲ 张景和《寻找手艺》“艺术总监”、大女儿张涵一。父女俩还是“情侣装”。张景说,这是 2014 年,女儿还愿意跟着他,帮他打下手当助理,“现在孩子长大了,不理我了,要飞走了,剩下老父亲失落的心”

▲ 张景在“寻找手艺”途中
- “学会了站在终点去思考问题”
搜神记:前面你说过,找钱其实不难,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厚着脸皮捧个纸箱子到处找钱,现在恰恰是没有厚着脸皮去找。那么找选题呢?难不难?
张景:选题很难。我正在考虑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前是我感兴趣了我才去拍,现在我得把自己剥离一点,它如果对社会有意义,我也要学会妥协去拍。
搜神记:对社会有意义,对大众有意义,对它的公共属性有所强调?
张景:对,但如果它和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我肯定不会去拍。比如类似于在鼻烟壶内画画这样的,很多人向我推荐,我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我宁可拍一个紫砂壶。
搜神记:它必须是跟生活、跟生命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用来“把玩”的。
张景:对,就这个意思。因为从小到大,走遍中国,真正有意思的手艺,我就没见过“把玩”的。那些“把玩”的至少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去拍。我说的这种“把玩”和给孩子们做的那些玩具又不一样。
搜神记:有很多人发弹幕说,强烈要求剧组开淘宝店,这样他们可以尽一份力量。
张景:想当然。这个想法从我筹备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有,当初我接触的是马云的私人助理,级别比较高了,他们说愿意在淘宝首页,每年给我飘一个星期左右,我觉得那价值就是几千万了。当然前提是双方都不谋利,已经到了具体操作阶段了。后来我向一个老兄询问该不该合作,他说你这些手艺人的东西不可能量产,顶多也就几百件,但是你这么大一个平台一出来以后,可能 90 %在淘宝网全是仿造的,你无形中把原有的打垮了,这跟你初心不一样。最后就不了了之了。没过几个月淘宝就上市了,再去找马云的私人助理也约不到了。不过再有这样的建议或者说有这样的机会,我就知道一个原则了,手艺人的东西不可能量产,一旦量产就完蛋了。
搜神记:这种消失、这种凋零是不可避免的。
张景:很奇怪,对于有些东西消失我并不感到惋惜,一点也不感到惋惜。很多观众对手艺人是一种占领视角,但是我在拍的时候,包括我从小对手艺人的认知都是仰视的,至少是平视的。年龄比我小一点,或者年龄跟我相长的,是平视的;年龄比我长的,我是仰视的。所以我片子里面的手艺人会很有尊严。我能做的就是记录一个时代的消失,我们无法挽留那个时代,但人的尊严是不会消失的。
搜神记:如果非要给自己贴个标签,你觉得你的标签是什么?
张景:我就想到两个,一,纪录片人,二,张景仁波切……但是这个说出去肯定会有无数人不理解。这有点狂,人家骂骂吧,无所谓。
搜神记:有这么穷的仁波切吗?仁波切在北京已经被污名化了,有人会认为你是在自我调侃。
张景:这绝对不是调侃。我把自己斗胆定义为仁波切,就是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做仁波切该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我八字里我自己就是张景仁波切。不是调侃仁波切,也不是调侃我自己。
搜神记:现在是全民刷抖音的时代,有人说纪录片也会消亡,你认同吗?
张景:肯定不会消亡,套用《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来得猛的东西一定不会持久。抖音是有很多民间智慧,也容易让人上瘾,一旦有这个特征我觉得是不会长的。但同时我也在疑惑,烟、酒同样让人上瘾,它同样有那么长的历史啊,想到这儿我就不想了。
搜神记:不想了,继续做就是。
张景:对,我做我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短平快一下哄然而起的东西,但能沉淀下来的,一定是能给人启发的、安安静静给人力量的东西。我拍《寻找手艺》是朝这个方向走,不是为了短时间博人眼球。我已经学会了站在终点去思考问题,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如果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演,是成为一个仁波切,该做什么我去做就行了,而最终能不能成为伟大的导演、能不能成为仁波切,那是另外一回事。
仲伟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