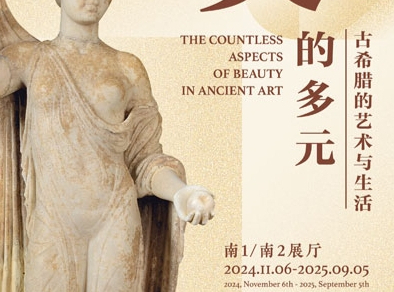境界与诗歌
——“人民性”与“主体性”的辩证思考
李少君
诗歌永远是寻求理解与分享的
主体性概念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康德强调之后,成为西方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康德认为人因具理性而成为主体,理性和自由是现代两大基本价值,人之自由能动性越来越被推崇,人越来越强调个人的独特价值。根据主体性观点,人应该按自己的意愿设计自己的独特生活,规划自己的人生,决定自己的未来,自我发现自我寻找自我实现,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在诗歌中,这一理念具体化为强调个人性,强调艺术的独特性。诗人布罗茨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但极端个人化和高度自我化,最终导致的是人的原子化、人性的极度冷漠和世界的“碎片化”“荒漠化”。
中国文化对此有不同理解和看法。在中国古典诗学中,诗歌被认为是一种心学。《礼记》说:“人者,天地之心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此解释:“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唯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人是有觉解的动物,人有灵觉。因为这个原因,人乃天地之心,人为万物之灵。人因为有“心”,从而有了自由能动性,成为了一个主体,可以认识天地万物、理解世界。从心学的观点,诗歌源于心灵的觉醒,由己及人,由己及物,认识天地万物。个人通过修身养性不断升华,最终自我超越达到更高的境界。
诗歌的起源本身就有公共性和群体性。中国古代诗人喜欢诗歌唱和和雅集。这是因为,诗歌本身就有交往功能、沟通功能和公共功能,可以起到问候、安慰、分享的作用。古人写诗,特别喜欢写赠给某某,这样的诗歌里暗含着阅读的对象,也因此,这样的诗歌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是必然包含着他者与公共性的。中国诗歌有个“知音”传统,说的就是即使只有极少数读者,诗歌也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诗歌永远是寻求理解与分享的。

什么是“心”?
诗歌是一种心学的观点,要从理解什么是“心”开始。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指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心,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既不是简单地指心脏,也不是简单地指大脑,而是感受和思想器官的枢纽,能调动所有的器官。
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由心来调动,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所有感觉,都由心来指挥。比如鸟鸣,会唤醒我们心中细微的快乐;花香,会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愉悦;蓝天白云,会使我们心旷神怡;美妙的音乐,也会打动我们的心……这些表达里都用到心这个概念,而且其核心,也在心的反应。我们会说用心去听,用心去看,用心去享受,反而不会强调是用某一个具体器官,比如用耳去听,用眼去看。因为,只有心才能调动所有的精神和注意力。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心是一切官能的总指挥总开关。人是通过心来感受世界、领悟世界和认识理解世界的。
以心传心,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是可以感应、沟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诗歌应该以情感动人,人们对诗歌的最高评价就是能打动人、感动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钱穆先生认为:好的诗歌,能够体现诗人的境界,因此,读懂了好的诗歌,你就可以和诗人达到同一境界,这就是读诗的意义所在。
心通万物,心让人能够感受和了解世界。天人感应,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感应系统,感情共通系统。自然万物都是有情的,世界是一个有情世界,天地是一个有情天地。王夫之在《诗广传》中称:“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
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观点,将他人及万物皆视为同胞。语出《西铭》一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天是父亲,地是母亲,人都是天地所生,所以天底下之人皆同胞兄弟,天地万物也皆同伴朋友,因此,我们应该像对待兄弟一样去对待他人和万物。中国古典诗人因此把山水、自然、万物也当成朋友兄弟,王维诗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李白感叹:“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清照称:“水光山色与人亲”。
在诗歌心学的观点看来,到达相当的境界之后,所谓主体性,不仅包括个人性,也包括人民性,甚至还有天下性。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

何谓“境界”?
那么,何谓“境界”?境,最初指空间的界域,不带感情色彩。后转而兼指人的心理状况,涵义大为丰富。这一转变一般认为来自佛教影响。唐僧园晖所撰《俱舍论颂稀疏》:“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境界,经王国维等人阐述后,后来用来形容人的精神层次艺术等级,境界反映人的认识水平、心灵品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学者张世英则说:“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境界可谓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
境界概念里,既包含了个体性与主体性问题,个体的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不断自我觉悟、自我提高,强化自己的主体性;也包含了公共性与人民性的问题,人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之后,就可以到达一个高的层次,可以体恤悲悯他人,也可以与人共同承受分享,甚至“与天地参”,参与世界之创造。

诗人杜甫的主体性与仁爱之心
杜甫早年“主体性”非常强大,在他历经艰难、视野宽广之后,他跳出了个人一己之关注,将关怀洒向了广大的人间。他的境界不断升华,胸怀日益开阔,视野愈加恢弘,成为了一个具有“圣人”情怀的诗人。杜甫让人感到世界的温暖和美好。
杜甫早年的“主体性”是非常突出的,他有诗之天赋,天才般的神童,七岁就有过“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壮举。年轻的时候,杜甫意气风发,有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也曾经充满自信地喊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世界慷慨激昂地宣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欲倾东海洗乾坤”。杜甫不少诗歌中都显现出其意志力之强悍,比如:“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何当击凡鸟,毛雪洒平芜”“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杀人红尘里,杀人在斯须”,何其生猛!即使写景也有“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何其壮丽!杜甫自己若无这样的意志和激情,不可能写出这样决绝强劲的诗句。
杜甫主体性之坚强,尤其表现在他身处唐代这样一个佛道盛行的年代,甘做一个“纯儒”,即使被视为“腐儒”“酸儒”。有一句诗最能表达杜甫的强力意愿,“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葵藿就是现在说的向日葵,物性趋太阳光,三国魏曹植《求通亲亲表》里有:“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杜甫认为自己坚守理想是一种物性,实难改变,尽管意识到“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但仍然甘为“乾坤一腐儒”(《江汉》),不改其志,仿佛“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茫”的战马。
杜甫的诗歌主体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自觉。杜甫写作追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对于写作本身,他感叹“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杜甫很自信,并且坚信“诗乃吾家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也虚心好学,“转益多师是汝师”“不薄今人爱古人”,他对诗歌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新诗改罢自长吟”“晚节渐于诗律精”。
惜乎时运不济,杜甫的一生艰难坎坷,他长年颠沛流离,常有走投无路之叹:“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奉赠李八丈曛判官》);再加上衰病困穷,因此常用哀苦之叹:“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赤谷》),“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散愁》其二)。杜甫一生都在迁徙奔波和流亡之中,但也因此得以接触底层,与普通百姓朝夕相处,对人民疾苦感同身受,使个人之悲苦上升到家国天下的哀悯关怀。
安史之乱期间,杜甫融合个人悲苦和家国情怀的诗歌,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杜甫以一己之心,怀抱天下苍生之痛苦艰辛悲哀,使杜甫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最著名的一首诗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诗里,杜甫写到自己草堂的茅草被秋风吹走,又逢风云变化,大雨淋漓,床头屋漏,长夜沾湿,一夜凄风苦雨无法入眠。但诗人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由自己的境遇,联想到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也处于流离失所的命运,诗人抱着牺牲自我成全天下人的理想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何等伟大的情怀!在个人陷于困境中时,在逃难流亡之时,杜甫总能推己及人,联想到普天之下那些比自己更加困苦的人们。
杜甫的仁爱之心是一以贯之的。他对妻子儿女满怀深情,如写月夜的思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他牵挂弟弟妹妹:“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我今日夜忧,诸弟各异方。不知死与生,何况道路长。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对朋友,杜甫诚挚敦厚,情谊深长,他对好友李白一往情深,为李白写过很多的诗歌,著名的有“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等;杜甫对邻人和底层百姓一视同仁,如“盘飱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杜甫对鸟兽草木也充满情感,他的诗歌里,万物都是有情的,他写鸟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他写草木:“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等等。

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由于杜甫的博大情怀,杜甫被认为是一个“人民诗人”,堪称中国古典文学中个人性和人民性融合的完美典范。杜甫的“人民性”,几乎是公认,不论出于何种立场和思想,都认可这一点。但由上分析,杜甫的“人民性”是逐步形成的,因为其经历的丰富性,视野的不断开阔,杜甫才得以最终完成自己。杜甫因此被誉为“诗圣”,其博爱情怀和牺牲精神,体现了儒家传统中“仁爱”的最高标准。
杜甫被认为是具有最高境界的诗人,到达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所以,诗人作为最敏感的群类,其主体性的走向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既有可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充满精英的傲慢,也有可能逐渐视野开阔,丰富博大,走向“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一个“人民诗人”,杜甫就是典范。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