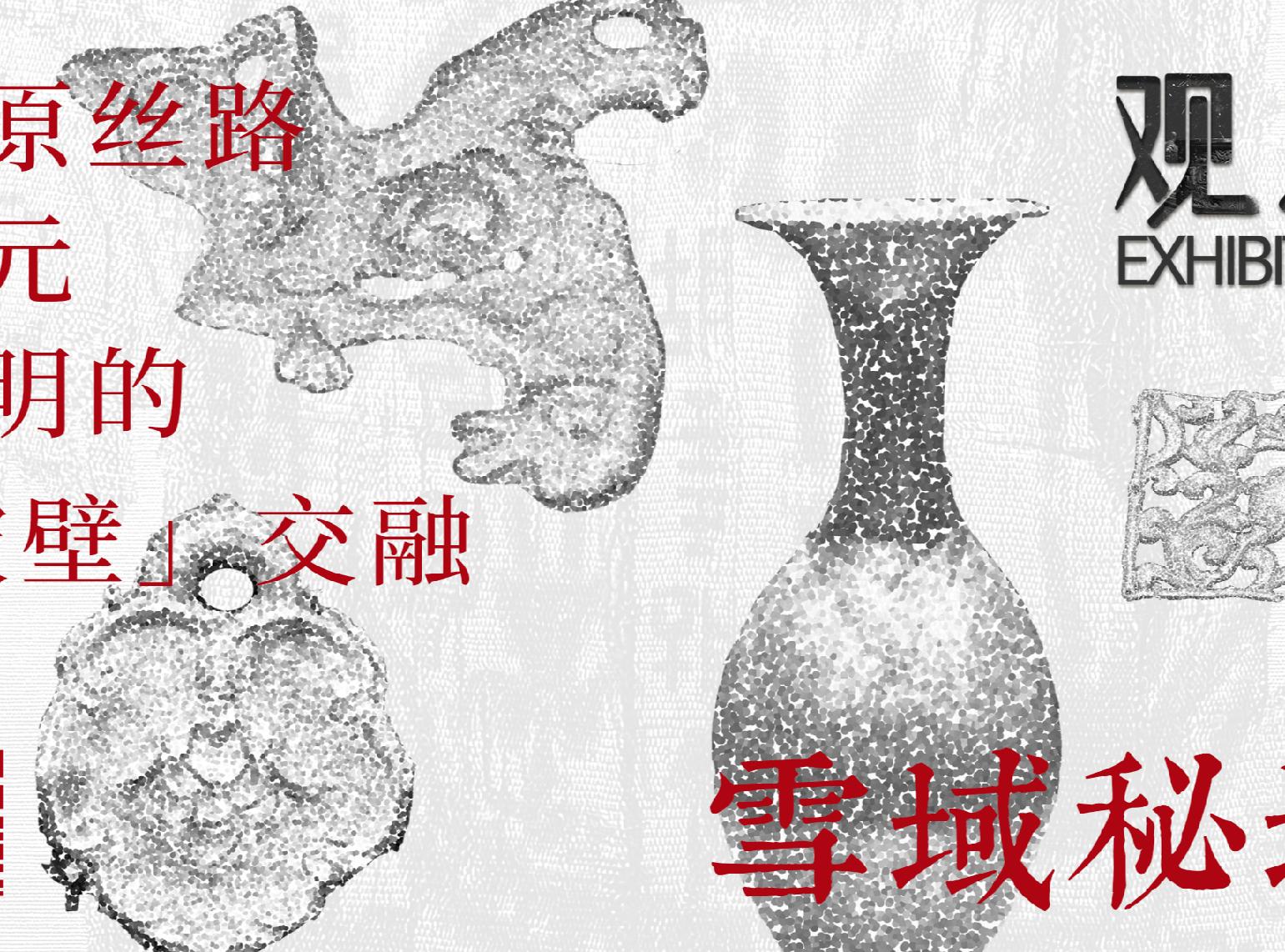他的视频号“庭山造园”,常有 10 万+以上的点赞量。那些坚定的庭山粉丝,评价他是“造园美学的启蒙导师”、“被造园耽误的哲学家”。一个只谈“美”的短视频号,却在不同信仰的人中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在文化和艺术圈,在社会精英阶层中,他的影响力大大超出我的意料。有朋友曾笑说,你有多少个朋友关注了庭山?——言外之意,含“山”量越高,朋友圈的质量越高。
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那个时候可能我恰巧抓住了时代的尾巴”。他认为那是他的造化。不过,更多人可能并不关心他的来路,甚至不关心他的真实姓名,反而更关注他的时代身份——百万“高净值”粉丝美学博主。“高净值”这个词,是我做财经媒体那些年常用的说法,一般来说,是指那些资产净值在 1000 万人民币资产以上的人群。我想,庭山一定不喜欢这样的概念,但我一时没有找到更好的表述。
最开始的时候,“庭山造园”就是讲造园,真实的造园,那是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毕竟,那个人群基数太小了,一万个人里头不一定一个人有花园。于是讲着讲着,他就开始讲美学——从园林美学扩展到更开阔的美学,再讲文化,后来讲历史,从真实的造园,慢慢转向了心灵的造园。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花园,这个花园都需要滋养,都需要灌溉,那么庭山造园就是,既造真实的园林,也同时滋润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花园。”
他因此失去了一些实用主义至上的粉丝。与此同时,他得到了更多拥趸。他感谢深刻改变了这个时代的短视频——技术的进步制造着让人应接不暇的机遇,也能把更多气味相同、灵魂相近的人紧密连接在一起。他并不担心短视频这种形式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他担心的是短视频平台背后的机制。很多人关心“庭山造园”是不是要商业化、如何商业化,一开始,这让他很挠头。因为这些短视频平台目前的变现方式,基本上都是带货机制。“如果我庭山去卖货了——别说去卖货了,现在一想到卖货我就焦虑——我能不给你传达焦虑吗?当我成天去想着一些九块九包邮的事,我还可能打动你吗?”这也是让他悲观的地方——“未来这一定会导致整个文化的没落。”
不过,他在“庭山造园”的评论区里面看到了另一番天地。
“特别多价值观相同、灵魂相似的人,因为我的分享——也并不是我说的内容有多么好——可能我说的某句话,恰恰是他的所思所想才引起共鸣。这些人如果只是在线上交流,不如来一次真实的旅行。我想这一定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这是商业化吗?——这也是商业化。他自问自答。
这首先得益于他的旅行。现在回过头来看,反而是人生中最没事干的时候,对他帮助最大——这也包括疫情那三年,他走遍了全世界。如今他说,他一定会组织这个美学之旅,根据自己十几年的旅行体验,把每一个环节都打磨好。他认为,自己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产品——高级不等于贵,当然不贵也不等于高级——时下,恰恰是这种满足精神愉悦的东西供给跟不上。
“我就想着和一群灵魂相似的人一起去旅行。”


一篇“文案”的诞生
搜神记:你曾经发给我“庭山造园”里的《死生和艺术》这篇——缘起于你最近回北大听课,记得你还说,写这一篇时,你对哲学有些吃力。
庭山:听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庄子、道教史、佛教史等课程,老师们从不同角度谈到了死生。能从老师那里获得智慧和开悟,非常感谢。但哲学对我还是很吃力的。
比如《死生和艺术》这个“文案”,涉及到很多哲学观点。最初的灵感来源于我听中国美术史的课,讲到兵马俑,讲到秦始皇,他为什么要这千军万马死后还陪着他?他对权力、对身后的这种事情,是怎么想的?他肯定有自己的生死观。就听了一上午,两节课。到下午讲西方美术通史,正好讲到古埃及艺术。古埃及那个时候,比秦朝还再往前 2000 多年,他们的艺术就更离不开生死,从帝王到百姓,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就为来生,为永恒。而此生的欢娱,他们好像不是很在意。他们的生死观是什么样的?
包括我们讲道教史的、讲佛教史的老师们,还有讲庄子的,都是北大哲学系非常优秀的教授,他们都谈到了生死。
再加上前一阵我去日本京都旅行,去了关西高野山。高野山开山 1200 周年,是空海大师从大唐取得真经以后回去开创的。上面有 100 多个寺庙,我就住在寺庙里面。山上有一个奥之院,很深很深的地方。空海就在奥之院尽头的一个庙里圆寂,那条路的两旁都是各种墓碑。织田信长、德川家康等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也葬在那儿,说明那个地方是他们都很向往的,可能会想到死后能够获得重生。我那视频里面没用那个镜头——我看到有三个和尚,一个和尚领着,两个和尚担着食盒,正要出来。那食盒上面有一个小牌,牌上写着两个字:仙膳。每顿饭恭恭敬敬的送进去,再出来,一直送了很多很多年。他们认为空海并没有死,只是生身入定,在多少亿万年之后——这个数字我没记住——他会再出定,会再救度众生。
就是东方的也好,西方的也好,他们对生死的理解,既有不一样的地方,也有一样的地方,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哲学和宗教。那么在听老师的这种讲课的时候,我就串在一起了,然后就形成了这篇《生死和艺术》,跨度比较大,既有中,也有西,也有古,还有未来。这里面一些哲学的观点,包括道家怎么理解,庄子怎么理解,佛家怎么理解,就是我很吃力的地方。当然也正是因为吃力,我在这篇文案的形成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提高。我还是希望一些事情能够稍微吃点儿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等各方面都在下降,有时候你学一个新的东西,不能太难,太难学不会了,但是也不能太简单,这样每学会一样东西,内心挺高兴的,就跟小孩一样,get到了一个新技巧,很欢喜。
搜神记:你写东西,一挥而就吗?还是反复修改啊?
庭山:主要的观点肯定是一挥而就的,至于一些文字的修改,可能说是更加委婉或更加温和的表达,但是有的段落是一个字不能改的,因为写这个段落的时候,是在很情绪的过程中,甚至泪流满面。有很多次,那个眼泪鼻涕——如果盘着腿的话——都已经流到了裤腿上。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是绝对不能改的,不管它对还是错,一个字儿不能改,因为改了以后它就没有当时的情绪了。这一点我还是知道,有些东西需要改,而有些东西哪怕它没那么完美,但是它足够真,那我就不会碰它。
“从真实的造园,我开始慢慢的转向心灵的造园”
神记:现在外界给你的定位,往往是“百万粉丝美学博主”、“园林艺术学者”,假如让你给自己贴一个标签,会是什么?或者说,你认为自己的人设是什么?
庭山: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感冒”——这个词有点不太友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挺拒绝给自己贴标签的。有的人还把“庭山造园”这个视频号分析了1234,我自己都看着有点懵,我说我就是这样吗?其实我也弄不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开始,这个视频号更多讲的是真实的造园,就庭山造园嘛,讲了造园的一些手法,造园的一些理念。有很多人就跟着来学这些技巧,或者学这些技术,都是知识层面的一些东西。但后来讲着讲着就开始讲美学——从园林美学扩展到美学,再讲文化,后来讲历史。我的粉丝一直是迭代的,最一开始是一些抱着实用主义的人,他或者从事类似的工作,装修、造园,或者自己有这个需求,但我一往上提,可能这些人就不爱听了,因为讲文化,对他而言就不如更实用了嘛。从实用主义,从真实的造园,我开始慢慢的转向心灵的造园。因为对花园的需求,这个人太少了。一万个人里头不一定一个人有花园。但是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花园,这个花园都需要滋养,都需要灌溉,那么庭山造园就是,既造真实的园林,也同时滋润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花园。这个名字也就一直没改,我也一直这样理解。
搜神记:个人感觉,“庭山造园”有点文化启蒙的色彩。
庭山:“庭山造园”这个号还是以美学、以谈美作为一条主线。这样每个人都能接受你,就是大字不识的人,他也需要美。只不过他认为这样是美,或者那样是美,但每个人都希望是美的,家里挂一幅画,哪怕是一个娃娃的年画,或者是大红大紫的东西,他认为是美,那种美给他带来愉悦,我觉得就OK。有些文化人觉得淡雅的是美,那能给他滋养,能让他安静下来,那他就OK嘛。向美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一定会坚持这条主线,一直是谈美,不管是东方的美也好,还是西方的美也好。当然,它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融合的状态,不是说中国的就是中国的,西方的就是西方的。中国之所以能延绵至今,就是因为它融合了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文明于一身,所以说这里面就会出现很多美。
“无所事事的时候,甚至情绪低落的那段时间,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
搜神记:你觉得,哪一段经历对你的人生帮助更大?……你是北京人吗?
庭山:不是,我是河北人。现在回过头来看,反而是最没事干的时候,对我帮助最大,而不是什么功成名就或者赚很多钱的时候。最没事干的时候,就有好多年,我就四处去转,去看,更多的时间是用在了出国去看。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发达地区都去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数学不好,但是我给自己算过时间,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世界周游完呢?而且很多地方得去很多次。要想看完这个世界,必须得增加出行的频次,这样才能保证在体力没有太衰竭的情况下看完这个世界。很多人说,等退休了以后去,我认为这是个伪问题,为啥呢?我年富力强的时候,我最有精气神的时候,而且财力等方面也是最旺盛的时候,我每天旅游下来几万步,回到酒店往床上一趴,连澡都不想洗,累的实在不行了。因为国外那些城市,不管是罗马也好,巴黎也好,还是一些小的城市,比如佛罗伦萨或者是威尼斯,基本上都是靠走路。中间你可以坐一段车,或者坐地铁,但基本上是靠走。那退休以后就不太可能有这种暴走的状态了。我觉得,如果大家以后有条件,真是可以三五岁就去旅行,或者一两岁就去旅行,但是目前可能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我昨天到颐和园去看花,也不是礼拜六,也不是礼拜天,就看到了无数的人戴着小红帽或者小黄帽,他们还得跟着旅行团来北京——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我自己是无比的幸运。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他那个认知的范围,而我却已经走了很远了。我觉得这种旅行对我帮助很大。
搜神记:疫情那些年,对你反而就是这样一段日子吧。
庭山:我觉得我还好,相对来说处于自由的一个状态。2020 年那个春节,疫情第一年的春节,我还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欧洲,把签证的时间用到了最后一天,一直是在行走的过程中。那个时候没有人,哪都没有人,即便是欧洲也没有人。有时候坐一个小火车,那一个车厢也就一两个人,就跟自己说,哎呀,包了火车了,就挺高兴。它是一个碰撞的过程,就是坐着小火车晃荡晃荡,你会有旅人的感觉,你的某些想法在旅行这个过程中,它就融合了。可能 20 年前你听过某个老师的课,或者他给你种的一个种子,可能在晃荡的过程中,在某一个小车站,它从你的脑袋里面就蹦出来了,发芽了。这个就对我来说帮助挺大的。所以我一直强调,无所事事的时候,甚至情绪低落的那段时间,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即便说这几年,比如去年(2022)春天,我从来没有那么多天在看花儿,买了把折叠的椅子,背包里头还有一个防潮垫儿,带着干粮就去花海了,躺在那里,旁边是一开始是油菜花,后来是那种二月兰,桃花呀,海棠呀,樱花呀,就在你身边。你说自在也好,自由也好,反正我觉得我是从来没有那么享受过春天。你看现在吧,桃花儿开了,但是我依然没有那么享受的去看它,虽然我已经看了几次了,可能比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看得多了。我还盼着过几天,我的那个秘密花园——就在我家附近——能够重现野花遍地的那种光景,那么我一定会去——我带上去年的罐头。
搜神记:你不久前去日本——你在“庭山造园”中也问过自己——疫情刚刚放开,为什么迫不亟待去旅行呢?
庭山:这个旅行,每个人都渴望嘛,就像我刚才说的,昨天我看到旅游迸发了,无数个旅游团,大爷大妈都来旅行了,只不过他们是刚有条件来北京,而我很幸运的是能去外面看看世界。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去旅行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重启他的旅行。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词,叫口红效应,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旅行就是这样一种效应。它不是说让你买一个车,或者让你够不着的一个东西,这个口红我能买得起,而且它能给我带来特别愉悦的感觉。如果没有照片,旅行就完全是一场梦。你去看两个小时电影,导演以及整个制作团队就给你制造了两个小时的梦。而旅行从你离开家的那一刻,就进入了一种梦境,这个梦境你认为是逃避也好,找寻也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一场梦,我想一次一次在那个或美好或悲伤的梦里面出现,跟庄周梦蝶似的,你不知道现在是梦呀,还是那个时候是梦,你弄不清,跟盗梦空间似的,哪个是梦哪个是真实,有时候确实是恍惚。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跨过千山万水,你会去进行一场注定要忘记的旅行呢?肯定要忘的,你不可能不忘,唯独不忘的可能就是意外,那种意外的美好。我们那天探讨,什么叫意外呢?刻意安排好的是不是意外?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次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那天要退房坐火车去马德里。早晨的时候我站在阳台往下看,怎么一个人没有啊?然后就去问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他说今天有马拉松,没事儿,一会儿拎着箱子,你去那边坐车就OK。然后退房的时候拎着箱子发现,那是一个小城市,所有的路上都没有车。怎么办?这时候火车马上到点了,我就推着箱子和马拉松运动员一起跑。绕了一大圈才跑到这个火车站。这个就是意外,这可能是上帝之手安排的一场意外。这个意外能让你记一辈子,甚至你转世回来还能记着这个意外。我觉得这种计划之外的事情是最美好的。这总有一种青春的感觉。当什么事情都既定不变了,按部就班,一切都在套子里面生活,就没有意思了,我们也就慢慢的变老了。为什么年轻人牛呢?他可以不拽你,因为他们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就得在这上班,你就得来打卡,我这个制度是合理吗?不合理,但是你必须得来,因为你已经丧失了可能性。
我觉得丧失可能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丧失可能性之前已经丧失了学习的能力,丧失了求知欲,丧失了走出去的勇气。那么我们在旅行中或者在什么之中,就找寻这种可能性,遇见这种可能性,而且在这种过程中,我们的勇气是一点一点往上递增的。比如我有一年去巴黎,正好赶上世界杯法国夺冠,决赛前两天他们那个球衣专卖店就已经排队了,买不上了。要知道大多数人是买不起的,因为一件普通的T恤 20 块钱就OK,而那个球衣就非常贵。等到了他们夺冠的那一天,作为老外,作为一个游客,就感觉那是一场暴动,所有的人都上街了。然后那个电线杆上呀,红绿灯上呀,都挂满了人,几乎所有制高点都被占领了。巴黎有很多黑人,光着膀子,露出很健美的肌肉,就坐在前面车盖上摇着那个衣服。几乎所有的车呀,只有司机在车里面,所有的人都挂在车外边。整个城市是一种所谓狂欢的气氛也好,或者在咱们东方守规矩的人眼里是一种乱也好,稍微有点害怕。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那种稍微有点儿害怕的心思立刻被打消了。不管这帮人多牛,飞车党也好,光着膀子也好,或者是凶神恶煞的人,到了红绿灯前面,红灯一亮,所有人都老老实实停那儿,绿灯一亮,又高高兴兴的呼啸而去。我一看,啊,没问题,他们的乱是在秩序范围之内的。OK,那咱就不害怕了,也加入到了狂欢的队伍,就很开心。世界是多元的,有不同的样子。你害怕的东西,可能是对别人是个常态。这就找寻到了不同的东西。而这些都是旅行带给我的。如果我没有走出去,我还在一个小城里面,那么可能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能性了。我到今天这个年龄,我依然认为我有可能性,因为我每天在学呀,我在保持好奇,我还想着出去玩,只要出去,就能遇见不同的东西。
“我们该担心的不是技术替代我们,我觉得任何一个新技术是为了解放我们。我们该担心的恰恰是教育”
搜神记:我们谈谈当下最火爆的人工智能。很多人担心技术会很快替代我们,你怎么看?
庭山:这两天人工智能一直在刷屏。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工业革命的时候有人担心,这个身体没啥用了,你都不用干活了,都是机器帮你干了,现在又有人觉得脑子没啥用了。既然脑子都没啥用了,你还担心脑子没用干啥?这就是瞎担心嘛,我们该担心的不是技术替代我们,我觉得任何一个新技术都是解放我们的。我们该担心的恰恰是教育。很多人在转那个视频——很多孩子还在那里死记硬背,在那儿狂吼着背,早晨跑步的时候就跟木乃伊一样噔噔噔跳着,就跟个方块队一样骨碌着往前走。这些知识机器上都有了,或者人家这个数据库里面都有了,你再怎么背,再怎么增长这些知识,也竞争不过机器。但现在教育模式并没有变,大家还是在求获得某种知识,或者获得某种技巧,还是实用主义嘛,把自己淹没在知识的海洋里面,而那些知识是可以重复记忆的东西。教育应该是,让每个人成为自己,让人成为人,可以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智慧,我就是我嘛。就是孔子那时候说的因材施教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受的是完全一样的教育,一样的知识的灌输。
我最近在学习,参加了不同的培训班儿,我也在比较。当然我非常感谢北大,我有校友卡,我可以回到校园里面听一些课,听到老师非常有智慧的分享。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太强调线上了,太强调知识性的一些东西,而这些恰恰是我特别忧心忡忡的。有两个陷阱,我们必须要避免。一个是反精英主义的阴谋,什么叫反精英主义呢?一到春天的时候总会有一两个专家跳出来说,或者英语没用了,或者农村人就不要上大学了,或者增加大量的蓝领呀。他不知道英语有用吗?他不知道智慧有用吗?他不知道受教育有用吗?这些人都是塔尖的人,他能不知道吗?他让大家反精英,反而是为了保持他的精英地位,一直是世代不断。这个就是很可怕。另一个,我们应该避免陷入这种知识的海洋里,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精力卷在那些题海里面,这完全是没有用的,反而是有害的。当一个人结束了那个相当凑合的教育的阶段,他需要用后半生的时间去洗掉他所受到的那些教育,但有意识的去迭代、去洗掉学校里面受到的这种教育的,毕竟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是注定成功的。因为他想脱颖而出,势必要跟别人不一样。这个观点极端吗?
搜神记:我并不认为极端。
庭山:他就需要不一样嘛,就是我要创新,我要和别人想的不一样,如果都跟别人想的一样,不就泯然众人矣了嘛。你区别于其他人的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智慧,而这些智慧不是靠这些知识的累积求得的。我们的智慧的传输,可能是在像咱俩这样聊天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你让我回去写文案,我也写不出来,可能回头我也忘了。老师们应该都恨死了那种线上的教学,没有一点思想火花,完全是文案上的。哪怕前面就一个人,比如咱俩这样聊天,会激发出来这种小火花,或者某一个跑题儿,恰恰是我以前所有的人生观、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见闻的一种累积的爆发。学生应该听的是这个,而不是说我给你讲 123456,这些东西回去看资料就OK。而我们这种聊天儿激发出的、这种你看似碎片化的东西——孔子当年那些思想也是碎片化的,只不过后人给他总结系统化了——恰恰是我们线上所不具备的,是现在我们教育所缺乏的。我们需要反思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教育是要解放一个一个的人,而不是为了束缚他们,我们要解放一个一个思想,如果没有 80 年代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后来这几十年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个话题永远不过时。从柏拉图,从孔子,我们的教育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思考世世代代了,我们今天其实每个人还都面临这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我觉得现在上课的方式,不管是北大、清华也好,还是一些外面的培训也好,哪怕是小学幼儿园,都是一种灌输的教育。我们缺乏一种提问的能力。这就回到刚才你说的人工智ChatGPT,首先你得提出好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了。我这次去学校上课,发现这些学生比我们 20 年前上课提问题能力差了很多。那时候上课,那简直蔚为壮观呀,只要是一些名师去演讲,或者讲座,那讲台前面地上全坐满了人,窗户上也挤满了脑袋,完全是一种热烈的场面——当然,这里面可能至少有一半是校外旁听的——很多人也提出颇有真知灼见的问题。因为有不同的人,我们的教育背景、成长背景都不一样,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不一样,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思想,才产生了这种碰撞。没有碰撞,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大学,也正因为不同的思想的碰撞,才成为了大学。说大学也好,说我们外边的这个教育也好,我们国家也好,都需要这种不同的碰撞。
搜神记:人工智能狂飙突进,个人思想之花趋向凋零,这方面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庭山:它不能这样泾渭分明,不能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悲观就是乐观。咱们中国人有一个太极的思维,我有时候就是灰,或者太极旋转起来黑与白、悲观与乐观都是交杂其间的,有高度的暧昧性,界线不分明。你问我这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他可能既是个好人又是一个坏人,我想每个人都有天使和魔鬼的一面。未来一定有非常乐观的一面,也有悲观的一面。就像前面说的,不管人工智能还是未来出现的什么新的技术,一定是要解放我们人,为我们所用,它就是一个好的嘛。就像工业革命有了机器,人不管用了吗?我觉得有的人失业了,可能有的人会生活得更好。
“想和灵魂相似的人一起开启美学之旅”
搜神记:你好像非常强调价值观。
庭山:不光是我强调,我想到了一定年龄,或者有一定经历的时候,这个价值观就显现的无比重要。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你工作,你遇见了很多的人,其实慢慢的这些人都已经在你的视线里消失了。我们不可能到这个年龄还跟小学同学一起玩儿,或者高中同学一起玩儿,我们总是一次一次清空我们的“朋友圈”,或者跟我们以前关系非常好的人相忘于江湖,这个是有必要的。我们甚至需要花力气去找一些价值观相同或者灵魂相似的人——我们需要花力气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人生的宝藏。宝藏没有说你不去找就能遇见的。人和人之间当然是一定是要有缘分的。但是我们确实也需要有这个意识,他的能量就是高于我,他就是比我有智慧,我和他待在一起,哪怕我一声不吭,但听他聊一下,我觉得比看了好几年的书都管用。
搜神记:我们再回到你刚刚去过的日本。你说看到京都之美,侘寂之美,而繁华的东京让人紧张。感觉这样的表达含有对“现代化”的某种批判。
庭山:我倒没总结那么高。说点轻松的话题吧。这次日本有两个点是我想去的。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展。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颜真卿书法展,我也看过了。另外就是奈良,我要去唐昭提寺,这座寺庙是当年由鉴真和尚主持兴建的。这两个人是我此次日本之行的缘起,我也确实看到了,有很大启发,节目我没做,但是感觉特别好。我就说个小花絮啊,到了东京,飞机从落地后就没有一次安检。这可以理解,因为坐地铁嘛,绝大多数城市是不安检的,坐火车也绝大多数城市也不安检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啊。但是我去博物馆,背着那么大的包,一直走到了王羲之的拓本真迹前,我觉得这是国宝嘛,依然没有人安检。我记忆很深。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留给咱们,可以自己去想,自己去思考。
搜神记:看你的视频,听你说“想和灵魂相似的人一起开启美学之旅”,有具体计划吗?
庭山:其实前面已经聊过了,比如我们的朋友圈儿里,你发一个东西,未必有几个人给你真心点赞。给你点赞、给你打气的人,往往是某一个在遥远的天边和你灵魂相似的人。或者你脑海里想的某一句话,你有一天看书发现,历史上的一个先贤和你说的完全一样,你和他也有相似的灵魂,你们此时此地已经碰见了。很多网友、粉丝特别记得这句话——相似的灵魂在此相遇。我在“庭山造园”的评论区里面看到了特别多价值观相同、灵魂相似的人,因为我的分享——也并不是我说的内容有多么好——可能我说的某句话,恰恰是他的所思所想才引起共鸣。这些人如果只是在线上交流,不如来一次真实的旅行。我想这一定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我们往往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旅行的时候碰到一个特别吵的旅行团,总会躲开,让他们先走,或者超过他们。但是几个真正彼此相懂的人,或紧密或松散的在一起旅行,旅行结束以后,我们在一个小酒馆里面推杯换盏,一起聊,像咱这样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能够开怀大笑,有时候拍桌子表示愤怒,有时候是痛哭流涕,那种微妙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最宝贵的经历。我们挣钱图个啥?不就想瞬间的欢愉嘛。可能很多人一掷千金去买笑,但那种欢愉它短暂的,而这种精神上的欢愉,反而是更永久的。我们希望得到这种精神上的享受。当然注定的是,获得这种精神享受的人,相对而言特别少。因为这种精神产品本身就少,不管是书也好,视频也好,这种满足你精神愉悦的东西供给跟不上。反而更多的是迎合大众,迎合大众势必带来庸俗化、娱乐化,还有把一些观点鸡汤化。总之我是要组织这个美学之旅,根据我十几年的旅行体验,把每一个环节都打磨好。我就想着和一群灵魂相似的人一起去旅行。
搜神记:也是一种高端定制旅行。
庭山:有的人一提到高端定制旅行,就觉得高级,贵,好像只有那些富人可以参加。但要弄清楚,豪华这个东西不一定是高级的,高级的东西不能等同于贵。当然你也不能反过来说,便宜的是高级的,一定会支付一定的对价。但一定要强调一点,贵的不一定是高级的,而且往往大多数不是高级的。比如我这次旅行的时候,住在京都一家很贵的酒店,七八千一晚,但没给我带来任何高级感,没有任何的惊艳或惊喜。反而住在庙里面,却可以让我达到灵魂上或精神上的愉悦。房间里面很暖和,但出去会很冷,我晚上穿着睡袍哆哆嗦嗦的去泡温泉,走廊里面特别冷。我到了以后发现,没浴巾,人这儿不是豪华酒店,不给你提供这个东西,我就哆哆嗦嗦的小步快跑回到房间拿。这个过程中啊,你一噔噔噔快跑,因为它是古老的寺庙,那个地板就嘎吱嘎吱嘎吱的响,这时候你就会放慢脚步,就会蹑手蹑脚的,冷,又想加快点速度,又不敢使劲儿。这个时候这种冷的体验让你想到,可能几百年前日本就是这样的。《源氏物语》那个光源氏,他去跟那个女主人或什么人偷情的时候,他也需要小心翼翼的拉开那个纸扇门,然后轻手轻脚走到那个和他一夜欢愉的女子的房间,而他们在欢愉的时候,肯定是不敢大声,这个时候你会更真切的感受到建筑和生活的关系。这个建筑是没有隔音的,而且冬天是冷的,你这时候你的思绪,你的体验,和几百年前的古人是一样的。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旅行的高级感。
“我担心的是目前短视频平台背后的机制”
搜神记:短视频深刻改变了我们。它甚至取代了文字。但更深层来看,短视频可能就是麻醉药,让大家减少互相交流,减少思想的碰撞,这想想有点可怕。你怎么看?
庭山:其实在短视频出来之前,也有报纸嘛,也有杂志嘛,是吧?其实都是不同形式而已,都是要很简短的说一个事情,或者表达一种观点,只不过短视频在这个阶段取代了以前的公众号或者是微博。微博已经很短了,那还怎么短呀,是吧?我倒不担心短视频这种形式,我担心的是目前的这种短视频平台背后的机制。你刚才问我是不是要商业化?目前这些短视频平台的变现机制,基本上都是带货机制,不管你是干啥的,你要卖东西。但你要知道,一个文化人,一个输出一种美好的人,他一般没有那个经商头脑。他一旦想着去带货,搞创作就会心浮气躁。因为每卖一个东西,他后面配着物流,或配着什么,就会牵扯精力。这也是我悲观的地方。未来这一定会导致整个文化的没落。路边的报刊亭也消失了,越来越没人去看书了,文字的东西大家一看就走神,过几秒钟就掏出手机看一看。大家都去刷短视频了,至少绝大多数人,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自控的。这也不能全怪咱们自己,也怪那些平台价值观的问题。我也是一个短视频的创作者,我深深的忧虑就是,大家都来看你了,你输出的又都是垃圾,都是一些“奶头乐”的娱乐信息,整个生态会好吗?
即便是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能用最简单的话,又不失深度的阐述一个问题的本质,那么这些人能坚持吗?会不会劣币一直驱逐良币?比如我庭山去卖货了——别说去卖货了,现在一想到卖货我就焦虑——我能不给你传达焦虑吗?当我庭山都开始变得俗不可耐,变得成天去想着一些九块九包邮的事,我还可能打动你吗?我的没落,实际上是更多人的没落。但这个平台就是这样的,你怎么办?平台的法则是所有创作者都必须遵守的。你不去直播,没人给你打赏。你不去卖货,你不给我分成,那慢慢我就不给你流量了。我现在之所以有流量,是因为我能给平台创造价值,价值是什么?我能留住你。这个圈层有人看,我能给他贡献流量。但是这些平台是商业单位,最终它要钱的,虽然流量对于它来说也是钱。未来我怎么办?可能不得不面对我曾经很鄙视的一种命运,要走向商业化。那怎么走向商业化?和一群有趣的灵魂一起去旅行,这是商业化吗?这也是商业化。我觉得它能够滋养我们,就是一个好的商业。我现在也参加培训,我也看书,我也听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智者去讲,那么我们能不能凑到一起,一起去提高和进步呢?如果有这样正向的东西往上走,如果大家来找我做这样的事,这样的商业化我是举手欢迎的。因为它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有帮助的。你让我去卖九块九,对不起,咱哥们真卖不了,也并不是说别人卖不对,比如董宇辉就挺好,他至少比那些扯着嗓子喊的要好很多。我们小时候也都看过电视购物,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只不过大屏幕换成了小屏幕而已,只不过现在每个人都随身带一个小电视而已,一点都没有高级。所以说我就想着,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文化上的体验,更多的美好,我也愿意尝试,也不得不尝试。
搜神记: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庭山:我希望每个创作者,都应该像一个真正的作者一样,你写了一本书,只要这本书畅销,或成为经典,你就永远有收入。就像油管一样,你做了一个好视频,你不用想带货,你也不用想广告,我都给你分好了。那么我就会全身心的投入这个创作,带给你美好呀,任何一瞬间的思想的火花,我要及时的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你,有更多的人看,我就有更多的收入嘛。但现在的机制不是这样的呀,是你要帮我赚钱,我才能让你有收入,而不是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思想或者帮助人有思想,你才有收入。我觉得一定要站在整个国家文化复兴的层面来看这个事情,口号都喊的好,但是你的价值观不对,实施起来抓手不对,我们就没法实现这种远大的目标,因为路就走错了。用钱堆的东西能复兴一个文化吗?一个以赚钱为第一目标的文化平台能实现复兴吗?就像教育培训,如果就是为了赚钱,为了产业化,让大家内卷,能实现复兴吗?都ChatGDP了,我们还让学生天天在那背背背,跟机器人一样,能复兴吗?我们一定要从根儿上去转变,现在短视频平台也好,或者现在教学方式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式也好,最终是要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来支撑。这种核心的东西,我们需要变。教育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我们求智慧,解放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创造力迸发出来,如果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他能够思考,能够提问题,能够跟老师平等的交流,那每个人都是巨大的发动机,我们中华民族这艘大船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行得稳,走得远。到时候不用谈复兴,我们就已经复兴了。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
搜神记:中国历史上你最喜欢哪个时期?
庭山:我也不是什么历史学者,什么春秋战国啊,宋代啊,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我倒是喜欢咱们 80 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思想解放的那个时代。也不是说我对那个时代有多么印象深刻,如果说我最喜欢哪个时期,也可以换一种表述——我无比怀念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恰巧抓住了时代的尾巴,或者离我较近,我能听到别人说那个时代。也正是那个时代我们思想解放,才有了我们今天中国 40 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每个人也从这个时代获得了巨大的改变。我从一个小镇青年,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去看了世界,我都要感谢这个时代。现在我还有一个北大校友卡,我还能去听课,每天能够面对那些智慧的光芒、真理的光芒,我觉得就特别幸福。这和那个时代解放思想是分不开的。所以说我特别喜欢那个时代,也感谢那个时代。因为它确确实实改变了我。
搜神记:在你看来,中国是否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呢?
庭山: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这 40 年,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复兴。它可以和文艺复兴相比。我们不能单从一种文学或者艺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就像刚才你问,我喜欢哪个时代?我喜欢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数的人从物质匮乏的时代,走向了一个相对富裕的时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经济没那么好,但我们能看到很多书,能看到很多作品,我们通过手机还能看到很多世界上好玩的事,看到不同人的生活。我觉得比起 40 年以前或者更久以前,这个阶段明显是一个复兴。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它也是在条件满足了以后才慢慢地开始了它那个时代,以佛罗伦萨为起点,那些人追寻到 1000 年前古典的书籍,在教堂或在修道院的库房里面,在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的地方,去追寻古人的智慧。从关注神到关注人,它有一个巨大的改变。当然这里面是离不开金钱的支持的,它有无数的赞助人,它需要富裕,富裕了以后,大家才更加重视这种精神上的创造。如果我们都吃不饱,那么我们关注的点可能就更在于温饱上。
搜神记:一个民族必须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你也是其中一位,在短视频时代,做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庭山:我对星空有两层理解,一个是忧虑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是仰望星空的一层含义,另外一个是真实的星空。我们是一群几十年没有见过灿烂星空的人,没有见过真实星空的人——你见过银河吗?我印象中就见过一次银河啊,银河原来真像一杯牛奶洒在了桌子上,怎么那么白呀!那就是我唯一的一次仰望星空,我看到了银河——而现在不管城里还是农村,其实能看到真正的星空,很少了。我们整个人类,我们整个民族,忧虑、仰望星空的人,其实也在减少,还是很令人悲观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发光,哪怕他只有萤火虫的光。不管你是谁,你在天上对应着一颗星星,那颗星星可能就是你,尽管那些仰望星空的人可能看不到你发的光,或者有的人亮一点,有的人弱一点,但并不妨碍你去发光。
仲伟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