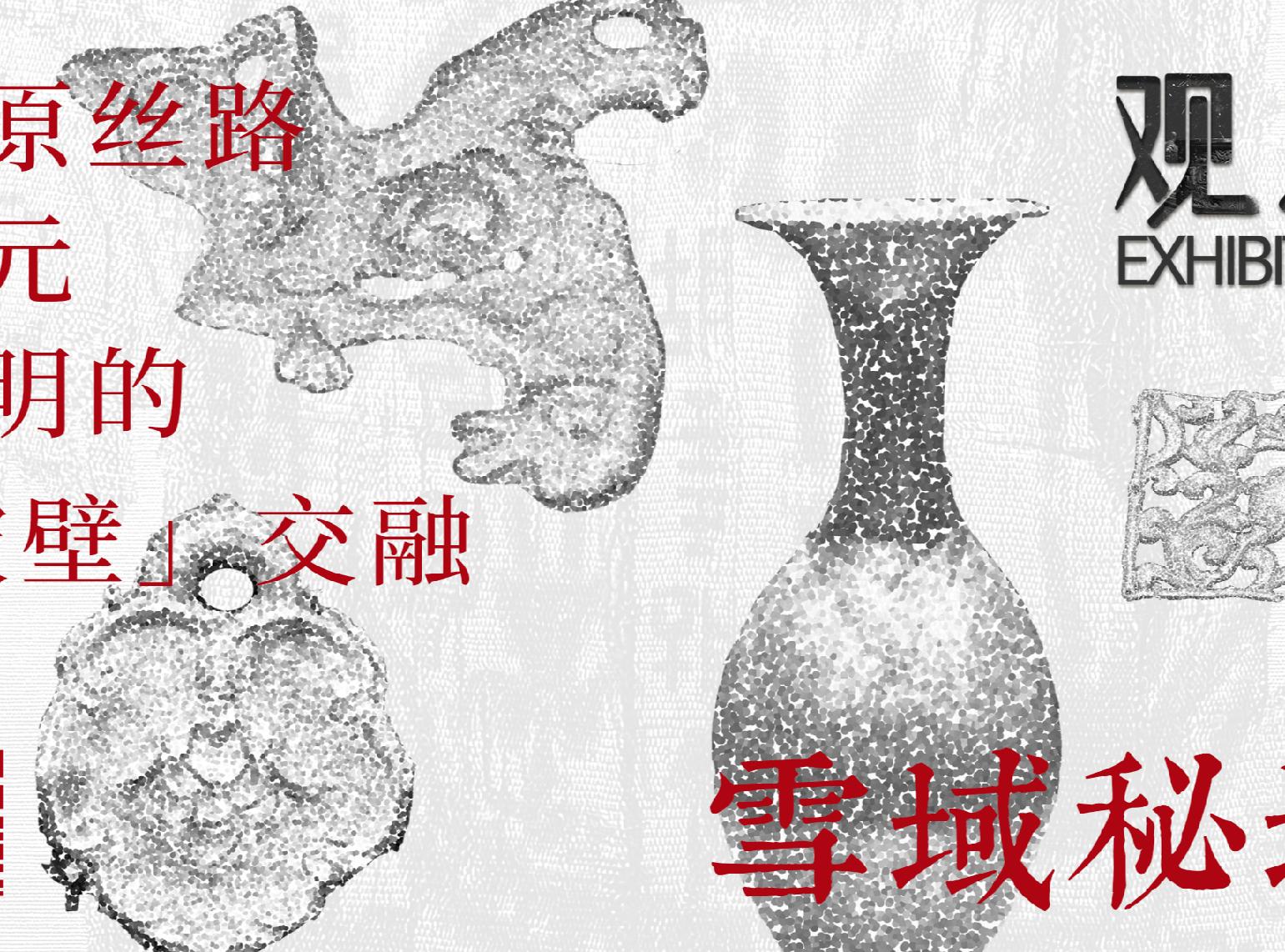亚当斯在《书林僻径》《书林漫步》中多谈诗、谈剧、谈小说,但他不写一本正经的书评与文评,而是在新书旧籍中选一些好玩儿的题目、有趣的角度或刁钻的话题,然后东采西撷,连缀成篇,神采立现,妙趣横生。所谓“僻径”与“漫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信步田野与小径,任性闲游,不事远足,随意采撷,删繁就简。这正是书话文体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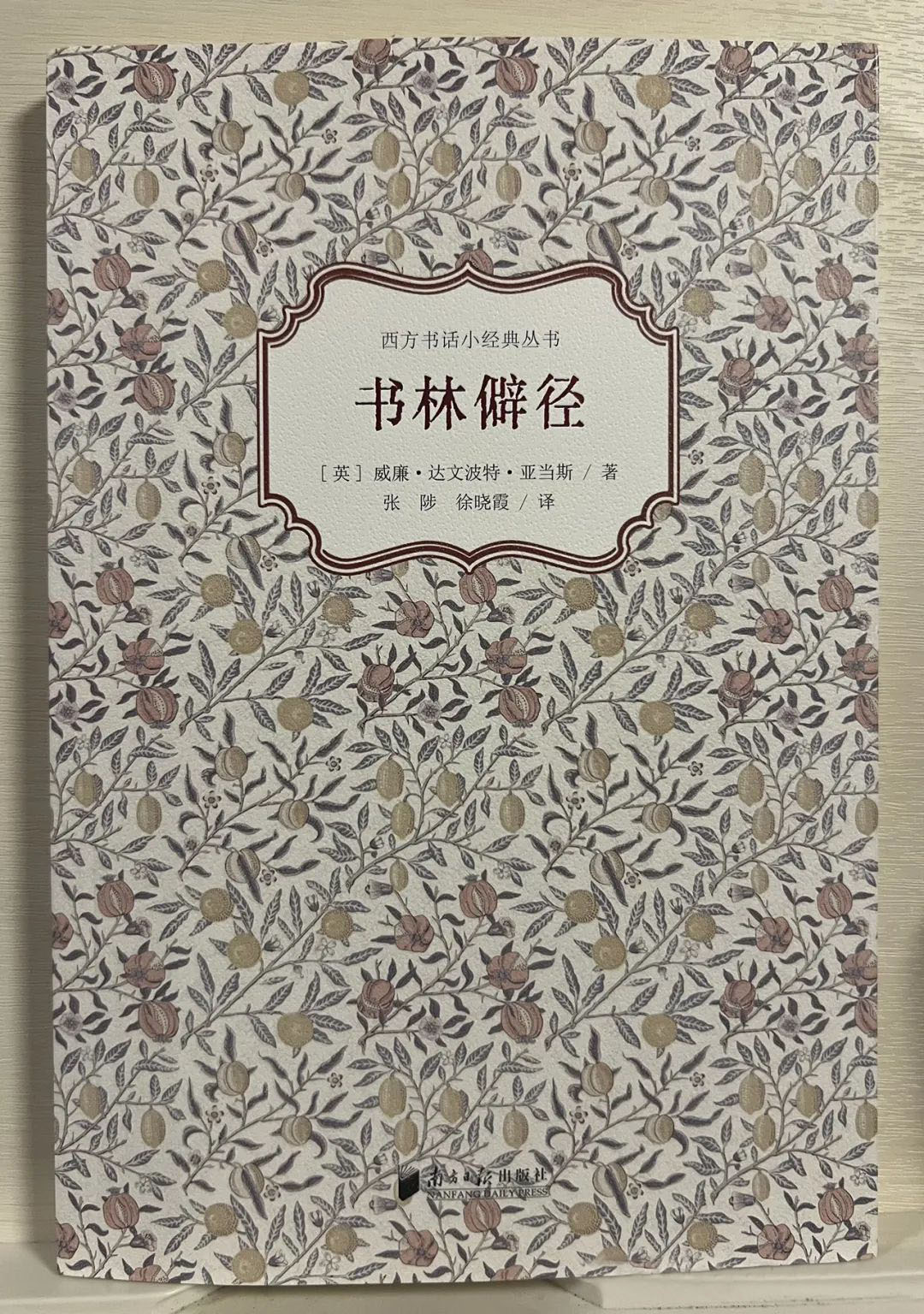
《书林僻径》,【英】威廉·达文波特·亚当斯著,张陟、徐晓霞译,南方日报出版社 2024 年 6 月第 1 版。
亚当斯在《书林僻径》《书林漫步》中多谈诗、谈剧、谈小说,但他不写一本正经的书评与文评,而是在新书旧籍中选一些好玩儿的题目、有趣的角度或刁钻的话题,然后东采西撷,连缀成篇,神采立现,妙趣横生。所谓“僻径”与“漫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信步田野与小径,任性闲游,不事远足,随意采撷,删繁就简。这正是书话文体的精神。
既然是书话,两本集子里当然有不少专门谈论书籍与阅读的篇章,《书林僻静》中有《裁卷怡情》《枕边之书》《书籍外观》等,《书林漫步》中又有《待书之道》《口袋书》《冬日读书》等。一百四十多年后读这些文字,意外的收获是我们可据此知道那个时代英伦三岛书籍文化的具体风貌。亚当斯的两本书先后出版于 1888 与 1889 年。那个年代,正是印刷工业革命大功告成、印刷技术迭代日新月异的年代,是开启“插图黄金时代”的岁月,新的装帧技艺与装帧风格即将大放光彩,礼品书时尚也正在兴起,还是阅读与收藏书籍之风大为兴盛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读亚当斯的书话短章,我们可以获得不少那个时代具体的信息与鲜活的细节。
一
《书林僻径》第一篇题为《裁卷怡情》。虽然以咏叹旧书开篇,但此文实为赞叹新书之作,仅此就可见亚当斯真有不凡见识。“在这个书籍大批从出版商柜台涌出的年代,”亚当斯说,“难道就不值得记下那种源于思考与细读带着印刷机余温的艺文作品的快乐吗?”
我们因此就知道了那个时代的一束新书消息。比如,那时的新书,或布面精装,或犊皮、羊皮装帧,简直是“披着无瑕之衣”,让人顿生“初见无瑕美物”时的深情。但也有人抱怨新书“太光鲜太美好”——太漂亮太华丽,不合“基本之用途”。而亚当斯的观点是:无论从审美层面,还是从文学意味层面看,一本新书就是一次新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注意,他说的新书是“真正的书”。“有的印刷品至多形式上算是书,其内容不过是精确资料的拼凑,有的甚至都不是,实在不足观。”
新书会惹人遐想:“会是什么样的佳作?隐藏着怎样的珍宝?备有怎样的阅读乐趣?”亚当斯引用英国戏剧家平内罗喜剧里的台词说,“我们渴望得到的,正是可怕的不确定。”
这一种对新书的渴望,实则是对新的生活的渴望。一个社会肯为新书而激动,这个社会一定充满活力。这样的活力 1980 年代我们也领教过。
那时的新书,有书页裁切整齐的“光边”,也有书页未裁的“毛边”。我原以为一百多年前的英国读书人对毛边本已经司空见惯,读《裁卷怡情》才知道并非如此。亚当斯说,有人希望书籍发行之时页边都应裁切,此举为购书者省力省时,否则会惹来那些急不可耐的读者的不满,他们“诅咒要将该书的出版商送去冥府”。
鲁迅、周作人兄弟是中国最早的“毛边党”,他们的这一趣味,源于日本留学时的经验。而日本出版界有这样的风尚,又源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书籍文化的传播。近几十年我们听到过很多爱书人谈论读“毛边本”的乐趣,有了《书林僻径》,我们就可以听一位一百四十多年前英国读书人关于读“毛边本”乐趣的描述:
“真正的爱书人,那些渴望从每一部佳作中汲取精华的人,却无不赞同使他们能够愉悦地流连于新得之物的习惯。他看着当下仍是紧闭的书页,想象里面会藏着何等特别的甘美啊!对他而言,一切未知皆视为非凡——这里可能蕴藏着精华中的精华。于是,这位爱书之人便与他的珍爱嬉戏一番,先是窥视书页之内,采撷只言片语。随后,他开始使用裁纸刀——缓缓地,缓缓地——带着陶醉的迟缓,揭开每一页的神秘面纱。”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