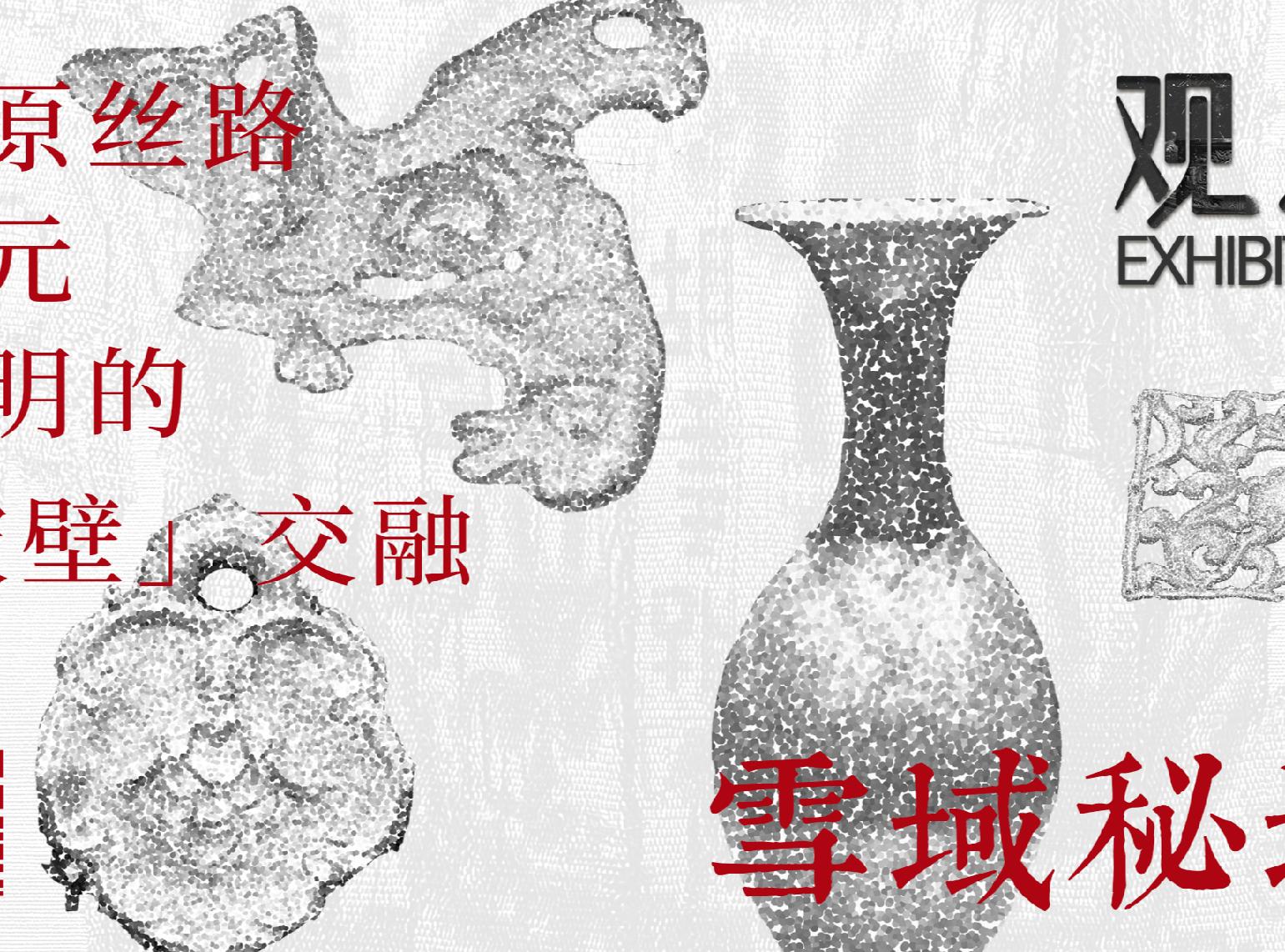▲ 这支来自昆明的乐队身上,有着众多年轻人特有的热爱和激情,所不同的是,十五年,他们一路坚持了下来
2023 年 5 月 25 日,昆明,横跨两年的巡演终于结束。
演出结束后,团队和乐迷都激动不已,他们心里把这场收官演出看作是一个仪式,一场加冕礼。
十五年前,苦果和自己组建的麻园诗人乐队从昆明出发,经受无数个第一次:第一场演出,台下只有七个人;一次表演时,被人轰赶下台;还有一次,被邀请演出,到了一看是在一个村子里。
那时苦果留着一头长发,年轻、粗粝、躁动,就像他们早期的音乐。苦果在昆明出生,昆明长大,在天津念完大学后回到昆明开始玩摇滚。他们在昆明一个叫麻园的城中村排练、演出,取名时仿照鲍家街 43 号,选定了麻园两个字,翻遍字典又想了许久,才加上了“诗人”。
2023 年再回到昆明时,他们已经由当年的“暖场之王”,进化成拥有庞大乐迷群体的摇滚新力量。
那天晚上,演出现场人满为患。鼓手林潇觉得,他这辈子可能没办法再有第二次这样的经历了。唯独苦果,内心平淡,“好像我就是不怎么激动。”演出时,他的耳返坏了,很长时间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觉得当晚自己的表现并不算好。
事实上,他也不过是在这场演出的两个月前才被调音师说服演出时戴耳返。之前这些年,他一直固执地听着现场的演奏直接开唱。他零基础闯入摇滚世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中会认为一些专业的要求更像是束缚。这也是很多乐队早期的特色:现场大于编排,自由超过规则。
在苦果心里,他对昆明的证明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完成了。
那一次,演出还没开始,苦果就决心让昆明看到乐队的成长。那时,他们已经签约了厂牌,成为一支成熟的乐队,发了圈内关注度颇高的首张专辑《母星》。乐队组成更加专业,演出效果更加出色,喜欢他们的乐迷也和登台的机会一样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是一支为了活下去到处走穴接活儿的草莽乐队,不再仅仅是平时少有演出,逮着机会就往天上躁的热血青年了。
到 2023 年 5 月,这场迁徙全国 39 个城市的巡演结束后,他们已经又进化成完全不同的另一支乐队了。“现在回头看,前面十多场的完成度其实很差,很对不起前面的乐迷,甚至说第 25 场都不如第 30 场好。这个巡演,把乐队好好磨炼了一下。”
这是典型的苦果,他不断修正,经常自信,却又时常“心虚”,他担心对不起乐迷 150 块的门票钱,演出越来越好后,他又开始觉得前面的乐迷吃亏了。
苦果的经历是一个很多人都幻想过能在自己身上上演的故事: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位摇滚歌手的作品,当即决定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然后从零开始,拿起吉他,一路跟随内心的驱使,一步步走到聚光灯下。这个故事在当下显得有些不计后果,也有些稀缺。
十几年前,在天津读大二的那年暑假,没有回老家的苦果稀里糊涂地跟着同学去北京看了一场“拼盘”演出,听到了谢天笑,在这之前苦果根本没接触过摇滚。看完演出,回程的路上苦果已经开始盘算买什么乐器、如何成为“第二个谢天笑了”。
没有基础、没有乐器、没有物质的支撑,只有一个自己想要去的方向。苦果开始了 15 年的跋涉。
苦果一口“云普”,唱歌时嗓音更加独特。有乐迷说,苦果长了一副时刻濒临破音但总不会破的嗓子。这让他的音乐欣赏起来有了门槛,跨过门槛又不太好去模仿。他歌唱爱情,歌唱孤独,歌唱卑微,歌唱磨砺,歌唱理想,歌唱坚强,甚至歌唱齐达内。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给人触动,推动人有力量前行,治愈他或者陪伴他”。
这跟很多人印象里的摇滚乐很不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摇滚乐进入中国,新鲜的编排,刺激的旋律,加上直击人心的歌词,一股摇滚风潮风靡一时,变幻的巨浪在一个个年轻迷茫的身体里冲撞,转化成那个年代特有的音符。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习惯他者视角,似乎只有苦逼着唱才有那股劲儿。
到麻园诗人这里,慢慢变了。他们关注个体和内心,喜欢从“我”出发看世界。乐迷也变了,听崔健长大的人已经开始操心养老和医保;听谢天笑的大多人到中年;而听麻园诗人的甚至还没有走出校园,他们有的是时间、激情和体力,一路追随乐队巡演的脚步在城市间辗转,连听好几场,将用不完的多巴胺、荷尔蒙、内啡肽掷于虚空中。
这转变是时代的年轮,有人批评当下国内摇滚乐精神的丧失,骨骼的软弱,丧失了坚硬与锐利,走向了通俗和流行。就像批判诗歌和文学。一切都在变,似乎只有批判才是不变的主题。
但新的就是新的。麻园诗人的所有词曲都出自苦果,最开始的东西很粗糙,也很高产。苦果甚至一度以粗糙为荣,他平时不怎么社交,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创作上,写歌也快,有时出去溜一圈就会有很多新的旋律和想法。
这三年,他和乐队又经历了很多,有疫情,有分合,有反思,有改变。这些经历让苦果越来越会审视自我,让他逐渐变得柔软、包容。这个年轻时“粗糙的直男”开始关注群体和外界的变化,写歌时想避免“我”的出现,去追求“更深一点”的东西。
与乐队成员的相处中,“我”也开始淡化。他变得更有耐心,学会了换位思考。他是主唱、乐队的核心,以前他不容置疑,急了会直接开骂。这次鼓手林潇重新回来后,俩人再遇到分歧,苦果会耐心向他解释,“躁,不代表力量”,所以,“不能一上来就往死里敲”。他们的音乐也有所改变,更工整也更沉着,少了狂躁,多了沉淀,由“重”变“轻”,却更加坚实。
把苦果带回昆明的大巡演开始于 2022 年。乐队签约新公司后,出版了新专辑《闭上眼睛的声音》,制作人是谢天笑音乐总监、国内著名制作人张彧,一个苦果觉得厉害到自己“想都没想过有一天能和他合作”的那种人。专辑发布后,乐队开始了一场雄心勃勃的全国巡演。
这场巡演原计划 2022 年 3 月开始,6 月结束,总计 30 个城市,平均每周两场,强度不亚于一次野外拉练。但由于疫情原因,巡演计划不断更改,中途状况频出。直到去年 5 月,首站长沙才正式开始,最终到昆明收官时,时间已经到 2023 年 5 月底。
作为一支本土乐队,麻园诗人的作品里充满了地域元素:泸沽湖、昆明、此站麻园、西福路、东路桥……把这些地标不断写进歌词的苦果不爱走出家门,若非是一些生存的需求客观存在,他可以一直不出门,除了特别熟的人也不常与人交流,这让他对外界发生的变化更加敏感。昆明的很多地方都成了他表达情绪的载体。
2021 年 5 月,许巍音乐总监、“中国首席吉他手”李延亮上传了一段自己用电吉他弹唱《泸沽湖》的视频。对于以前没听过麻园诗人的歌的人来说,这首《泸沽湖》在李延亮的演绎下,无词胜有词,一下子出圈,此后各种翻唱版本层出不穷,点击量超过 10 亿。
《泸沽湖》创作于 2017 年,一个苦果比较艰难的时期。写这首歌时,他去了趟泸沽湖,然后把自己的故事写了出来。他的表达是含蓄的,他很少有写真式的呈现和直白叙事,那些歌词更像是一个个意象的组合,被情绪串联成逻辑,形成一帧帧连贯的画面。加上苦果擅长的旋律表达,麻园诗人的歌总能让不同经历的人打开更大的解读空间,找到不同的情绪落点。
同一时期的《晚安》也是如此:“在海岸,风冰凉,在路上抬头向上望,在天色渐暗,一起说晚安。”有人听出无奈,有人听出洒脱,有人听出挫败。苦果说,《晚安》在写一种没有得到的爱情,一种和爱人在一起的想象,云南没有大海,但歌里有。
《深海之光》是另一个故事。几年前,麻园诗人被邀请参加南宁的一个音乐节,演出结束后,一支乐队要轰赶他们清场,并发生了冲突。“我也是玩乐队的,就只是想后台学习下演出经验,然后就被他们要求清场。那种心理是很难受的,很受不了。”
第二天,苦果写出了《深海之光》。给卑微者以信心,给怯懦者以勇气。这首歌一改麻园诗人早期作品的急躁与粗粝,变得更加克制,也更有厚度,压住了愤怒,也长出了嘹亮。
在 2022 年的一次线上演出中,苦果要唱给大家一首“最真诚的,代表他们在麻园排练那段时间的作品”,“希望大家即使在最黑暗的深海里也能看到光亮,永远不被生活打败”,即是《深海之光》。
5 月底的全国大巡演刚结束,暑期密集的音乐节现场随之而来。合肥、河源、雁栖湖、温州……马不停蹄,邀约不断。他们离十五年前昆明麻园城中村的那支乐队越来越远,离梦想中的自己越来越近。
2023 年 6 月的一天,平淡无奇,热气腾腾。北京南三环东铁营桥向南不到一公里,一条很不“北京”的巷道无精打采,垃圾桶三三两两杵在路边等待垃圾车的收取,不远处的公厕鲜有人去,偶尔响起的刺耳的鸣笛声和呼啸而过的摩托,构成这一带尚未完成改造的棚户区样貌。
就是在这里,一间排练室深藏不露。钻进吱吱扭扭的铁门,排练室与街道办事处共用一个出口。一截短短的楼梯分割出两个世界:地上肃整、公事公办,地下幽微、天马行空。割裂又杂糅。
这是苦果不怎么喜欢却也并不陌生的北京夏天。混乱、自由、便宜,他们早期的排练和演出场所大都如此,他们在这里出发,调音、抠词、合练、等待着舞台。
进入排练室需要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挂满了那些著名摇滚乐队的著名海报:皇后乐队(Queen)穿白色背心的“牙叔”,那是在 1985 年“拯救生命”的演唱会上,他右手高高举起,话筒拖着半截长杆被他紧紧攥在右手里,活像一柄权杖;涅槃乐队(Nirvana)六张专辑的封面,蓝色海水里一个张开双臂的婴儿爬向鱼钩上的美元,被透视的母体摊开双手长出天使般的翅膀;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三棱镜,黑暗中的一道白光被筛成一个彩条,再次投入黑暗……路过他们似乎就能抵达他们,走廊尽头的霓虹灯无声频闪。
晚上 7 点,苦果背着吉他包,穿过走廊,走进排练室,乐队的其他成员已经就位,各自安静地调试乐器。
旁边的休息室内的一面墙漆略显斑驳,挂满歌手的相框:崔健、朴树、郑钧……还有一些看不出是谁的新生代乐队的现场照片,排练间隙乐队的成员站在这面“闪耀”的墙前聊天、抽烟,也会去一一辨认这些面孔。并不是所有的歌手或者乐队都有上墙的机会,即便这是一面排练室里的普普通通的墙。
十几分钟后,熟悉的音乐响起,苦果闭上眼歌唱:
灯光灿烂,灯火辉煌,
而我想要黑暗;
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
随意把它遗忘;
站在湖水对岸,总有些过往;
站在湖水对岸,总有些过往。

01
我那时候的冒险,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成为第二个老谢
搜神记:介绍下乐队的成员吧,四个人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苦果:我们是国内乐队里换人比较频繁的。鼓手小林(林潇)5 年前离开了,现在又回来了。他加入乐队算是比较早的,当时碰上我们在排练,正好我们也缺鼓手,他就加入了。后来,相处中我们发生了一些摩擦,在音乐上也有一些不满意,然后就离开了。再后来,我们又换了两任鼓手,觉得小林还是不错的,就把他重新邀请回来。
贝斯姬唯,宁夏人,他待的时间比较长了,和乐队是机缘巧合。06 或是 07 年的样子,当时他好像失恋了,跑到西藏和云南散心,就和我们玩了七八个月,跟着我们到处跑演出。我们当时实在找不到贝斯手,他说他有点基础,来试一下,就加入进来了。乐队是 08 年组建的,时间也挺长了,中间有四五年时间停滞了但没解散。贝斯加入之后,我们重新又凝聚了起来。整体上,我们是越来越默契了。
吉他余小强,今年才进来的,云南人。上一任吉他走了,这次我们实在不想再找非云南本地的乐手了,如果不在云南当地,平时排练和演出就会很不方便。我托朋友问了一下云南有没有好一些的人选,就找到了他。
我们这种音乐的风格,决定了无论是鼓手、贝斯还是吉他,每一个都不能太弱。
搜神记:对于乐队成员,除了演奏技能,还有哪些是你觉得比较重要的?
苦果:音乐上的悟性。还有与人相处的感觉。五年前,我不会很在意与人相处的感觉,但现在我自己会去妥协了。你不能要求他有很高的技术,要求他在音乐上有野心,还有很高的悟性,又有创造力,同时还要求他性格特别随和,这些是很矛盾的,世界上好像不存在这种人。现在的要求是,只要别太过分,互相不要太有那种激烈的争执冲突就好了。
搜神记:你们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吗?
苦果:我和小林(鼓手),之前我们还是争吵得蛮厉害的。
搜神记:为什么?
苦果:主要还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是那种特别自我的人,尤其在音乐上,我不太允许别的乐手随意改变我的音乐、我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但在平常为人处事方面,我是特别大大咧咧的那种人,只要为了乐队好,其他都可以。所以有时候,在涉及音乐上的争吵时,我甚至会有一些谩骂,我觉得这是为乐队好,我以为大家会谅解我。实际上,大家觉得我有挺难相处的一面。现在好一些了,现在我慢慢懂了一些事情。
搜神记:是因为这几年你自己变得柔和了、懂得妥协了?
苦果:音乐上没妥协。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原因,就是随着慢慢成长,会越来越审视自我。会体会到乐队其他成员的难处,换位思考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我来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名利,本来就是一心把音乐做好,却还要受这么大的委屈,就会挺难待下去。
搜神记:现在看,乐队早期的风格还是比较粗糙的,无论是作品还是表演。
苦果:粗糙太多了,我们早期甚至以粗糙为荣。乐队风格的变化,其实还是人的审美的变化。早期觉得需要直接一些的东西,现在会需要深一点的东西。
搜神记:早期的麻园太像谢天笑了。
苦果:我为什么玩乐队?是因为偶然看了一场谢天笑的演出。在我看到老谢的演出之前,我都没有接触过摇滚乐。别人可能是因为听了摇滚乐之后喜欢摇滚乐,我是因为老谢的演出喜欢上了老谢。我当时并没有真的喜欢摇滚,也不明白什么是摇滚,我不是那种接触了一系列的摇滚,然后要做其中的一种类型。说得直白一点,我那时候的冒险,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成为第二个老谢。
那时我在天津上大学,大二的一个暑假,我没回家。一个同学看我整天在宿舍待着,觉得好可怜,离家这么远,别人都回去了,就我特别无聊地在宿舍待着,就说,带你去北京看演出吧。我根本不知道要看什么演出,觉得能来北京玩一趟也行,而且又是他请我看,于是就跑来北京看演出了。那场演出是个拼盘,不是专场。演出地点是在北京亮马桥女人街的新豪运酒吧,不知道这个酒吧、这条街现在还在不在。
先是两个特别重的乐队,我不记得名字了,只记得他们的音乐特别重,有点吓人,完全听不下去,特别难受,我就一直拉着同学说,要不咱走吧。然后老谢上场了。风格和旋律完全不一样,我不说他有多好,但就是完全不一样。他唱的第一首歌《是谁把我带到了这里》,很奇妙很奇怪,听到第一个音符,我已经不行了。
搜神记:你跟老谢聊起过这段经历吗?
苦果:我说过。他知道。
搜神记:从开始组乐队时,你就决定了以后要以此为职业吗?
苦果:从我拿起吉他的那一秒钟,就已经决定以此为职业。大二时,那场演出结束后,从女人街新豪运酒吧到北京东站,我是一路走着过去的,满脑子都是在想这个事情,我在幻想以后要怎么弄,幻想接下来的事情。那时这一切已经定了。
后来我辞职时,我爸妈不相信,因为当时乐队也没啥发展。我妈跟我说,你是大人了,自己决定就行。我妈很信任我,她知道我是能够吃苦耐劳,能承担责任的一个人。但我刚辞掉工作的那几个月,她总是偷偷看我银行卡的余额,她担心我、关心我,但又不说,可能是不想让我有太大压力。
当时是发自内心最深处喜欢做音乐的,从来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从来没有第二条选择。如果再让我回头选择一次,我还是会这样选择,我没办法退回去。这个事情,上天注定。
而且我抱起吉他玩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的缺陷,知道我在音乐天赋上有很大不足。比如,我的手很小,手指很短,手速不行,不太适合弹吉他;还有,我普通话不标准。但这缺陷在我心里就不是缺陷,我自己很认定这件事。因为音乐世界太大了,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去追逐你的目标。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当时我就明白这个道理。
搜神记:现在,能让你妥协或者屈服的东西是什么?
苦果:我现在是会有对团队的责任心,我们乐队成员都是全职的,除了乐手,还有调音师、灯光师、舞台助理等。我得让他们过好一点的生活,主导性强一点,可以自由支配一些收益,商业上能够让他们看到价值。我仅仅在这方面会有一点需求,但我一点也不会为了这些去妥协。有一次一个啤酒品牌跟我们合作,要求我写歌时把几个关键词加进去。我写的时候压根就没在乎这些,要不你就别要了,他们最终还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我相信有时候商业和音乐性上是能找到一定的平衡点的。

▲ 拿起吉他的第一天,苦果就认定,音乐世界太大了,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去追逐自己的目标
02
二手玫瑰带给我很大一次伤心
搜神记:“麻园诗人”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苦果: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麻园是昆明的一个城中村,是我们当时经常排练演出的一个地方。当时我 22 岁,乐队在这个地方待了大概一年半,这里有当时云南唯一的livehouse。当时看其他乐队的名字,比如鲍家街 43 号、便利商店什么的,我们就想叫个麻园什么,但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查了一晚上字典也没凑出来。我记得是当时的一个队友说了一句,要不叫麻园诗人吧,我一听觉得,这个好。所以,这个名字真的一点特殊的含义也没有。
我父母知道我玩乐队时,也没有特别强烈地反对。他们不相信我会把乐队当成职业,所以他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关系。而且当时我还有工作,还在上班,他们会觉得好像这只是我的爱好之类的,所以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但那时有一件事让他们很反对,就是我偷偷用了家里 1000 多块钱,买了一块效果器。我看上的效果器是 3000 多块钱,我一个月的工资才 1500,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又想上来就买个好的。我爸妈其实在意的不是这个钱,他们是担心我变坏了。因为当时那个环境,昆明那边有一些吸毒的,加上我玩乐队又经常在酒吧这种场合演出,所以他们担心我变坏了。我当时想的是,先拿他们的钱用一下,等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就又放回去了。
搜神记:当时的工作什么?
苦果:我大学学的是旅游,毕业后在昆明一家广告公司做文化创意工作,具体是文案策划。其实就是套模板,再具体一点说,就是把别人的PPT的模板下载下来,然后换一下上面的字。因为不是自己热爱的事业,所以从来也不去研究,对它没存有很大的责任心。
搜神记:你有感觉特别差、特别糟糕,甚至崩溃要放弃的时刻吗?
苦果:我每次崩溃,都是在音乐节上,自己演得特别差的时候,尤其是看到后面的乐队又演得特别好。这不是崩溃,更多是沮丧。比如,很多年前一次,有一次参加丽江雪山音乐节,山人乐队让我很沮丧;还有一次是江西缤果音乐节,二手玫瑰带给我很大一次伤心;最近的一次是在淮安的一个音乐节上,看到了另外一支乐队。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又特别恨他们,至少演出结束的那些晚上,他们带给我的刺激是很伤心的。为什么人家可以玩这么好?为什么自己就这么傻×?特别痛恨自己。
那些优秀的乐队,表现形式不说,人家的那种舞台状态、专业性、调音师、灯光师等等,整个团队的每一个方面都那么好,突然就会觉得,我们跟人家的差距有点大。我特别害怕这种东西,它会很打击我。不过,打击过后的一段时间就会给我带来很大帮助,因为它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
我没有崩溃过,更多是沮丧,而且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过去。类似这种打击也好,包括某个乐手突然在某一天提出离队也好,我也不会崩溃,我会慢慢找到缺点和不足,然后马上改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好的乐队核心成员,也是这样的,而且一定比我强多了。谢天笑身上的这种东西,更加强大。
前几天晚上,我和谢天笑老师一起吃饭,他说了很多话,还是很震撼,还是需要我学习。我经常和老谢交流,请教东西,我来北京就会找他。我时不时会觉得,我从他身上已经学个差不多了,谢天笑差不多到这儿了。但是下次再和他聊就发现,我靠,还是牛×!他已经在想着怎么把更大的艺术范畴的东西融入到音乐里面,这种野心,这种自信,都特别强。
搜神记:这次你和谢天笑有哪些有意思的交流?
苦果:他跟我说了一个词:破界。
他说,别老想着把音乐做成熟,音乐做不成熟,音乐没有成熟定型的体系。它只有不断地破界,把一个又一个边缘破掉,去拥抱更多的东西。现在麻园的音乐也是这样,不要想把它做大做成熟,艺术不是这样挖掘的,艺术需要被打破,创造新的。像这种观点,我以前就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这种想法。
搜神记:这四五年来,一件又一件这样的事,慢慢让你学会了妥协。
苦果:以前对很多人,包括乐队的成员,都不太care他们的意见,抵触任何人,坚信自己的任何一个音符都是不能动的。现在,我会去认识到谁的优点在哪里,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谁更能创造出东西,而且一旦创造出那些我难以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会马上去抓住它。
搜神记:现在好像很流行焦虑,很流行“躺”。
苦果:我也焦虑,身边的人也焦虑,我不能说大家都不要焦虑。但我不相信只是做音乐的人才会有野心、自信这些品质,做生意的人更需要强大的自信,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很强。以前做房地产的很风光,现在房地产不行了,欠几千万的人也挺多,人家也没有被打倒。很多人都有特别强的品质,只是他们用在了别的方面。
搜神记:2016 年乐队做过一次 21 个城市的巡演,当时乐队成立 8 年、发表了第一张专辑《母星》,转眼六七年过去了,这次跟 2016 年那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苦果:2016 年的巡演跟这次截然不同。《母星》那张专辑的时候,我其实在音乐上是很纯粹的,但是在对待运营或者对待演出这一块,我是很敷衍的一种状态。演出就是来卖票的,或者说来争取让乐队获得收入、获得粉丝、获得名利,而不是去想如何在现场创造和拓展音乐的生命力。那时候的巡演,包括之前的所有演出都是这样一种心态,名利大于享受,是一种义务,是为了演出、为了卖票,但是没办法,那时候真是太穷了,演出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个时候,乐队对名利的渴望非常强,做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
现在回头看,对那个时候的状态倒也不至于讨厌,因为没办法,那时候是以生存为目的。但是现在我之所以能够有底气说,我出来演出我是负责任的,是带着诚意来演,带着追求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来的,是因为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有生活的保障。
搜神记:其实《母星》这张专辑里好几首歌都挺受乐迷喜欢的。
苦果:人生每个阶段,都有要面临的问题。《母星》是非常粗糙的,连混音都是自己混的,能不糙吗?但是那时候的创造力和对音乐的敏感是在的,每个词唱出来,都是用尽全力的,没有任何惧怕,没有任何复杂。要是能把那种创造性的状态放到现在或者放到未来,该有多好。
现在比那时有了更好的条件也更有底气了,但可能那种对周围社会的敏感、那种创造力的爆发,没有那时的状态了。这可能就是很无奈的一点。
我相信我还有创造力。现在一些作品抹杀了一些很自我的东西,在独特性,比如质朴等方面,不如以前了。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现在的作品,也不能说现在我的音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已经在下滑,因为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搜神记:《深海之光》也是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是在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
苦果:这个太有故事了。记不清是 14 年还是 15 年,我们在南宁的一个音乐节,那个时候,我们乐队参加音乐节的机会还不是很多,所以对每一次机会都特别珍惜。我想向那些好的乐队学习,演完之后就在后台一直待着,想看别的乐队是怎么试音、怎么装台、怎么演出。到最后一个乐队,他们要求把后台清场。我就和他们说,我们也是做乐队的,也是来参加音乐节的。他们说,我管你什么乐队的,都要出去。我们就发生了争执,和他们的经纪人或者保镖之类的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
当时就觉得特别屈辱。我也是玩乐队的,就只是想学习下演出经验,然后就被他们要求清场。那种心理是很难受的,很受不了。第二天,就在这种状态下写了《深海之光》。
03
他说他是张彧,想做我的制作人
搜神记:说说 2021 年那次在北京演出吧?在MAO livehouse,跟李延亮、张彧合作的那次,你们表演了一次精彩绝伦的《泸沽湖》,一下子就出圈了。怎么来的这次合作?
苦果:那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演出。我印象很深,但我觉得这次演出其实不算好,有瑕疵,在我们的演出效果里不算最好的。那场演出之前,《泸沽湖》在网上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了,冒出来后,亮哥弹了一版,还发了个短视频。张彧老师是我们乐队的制作人,他就问亮哥是不是喜欢这个,刚好六月份我们在北京MAO livehouse有一场演出,也就促成了这次合作。后来,我们在一些音乐节或者其他演出场合遇到了,有时也会合作玩一玩。
搜神记:乐队跟张彧的缘分是怎么开始的?
苦果:在认识彧哥前,我其实已经关注他很久了。因为我喜欢谢天笑,所以他们乐队的成员我们都比较关注。在那个阶段,彧哥是我觉得自己永远都没机会和他说话的那种人,太厉害了,制作和编曲都太厉害了,我想都没想过有一天能和他一起合作。
2021 年 10 月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下楼丢垃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是张彧,想做我的制作人,让我再交两首demo给公司,听完后会再给我打电话。他就这么直接说的,我当时特别激动特别兴奋,还有点怀疑遇到了骗子。我接完电话发现,垃圾都忘记丢了。
我已经控制不住开始设想彧哥做我们的制作人之后的种种,之前我们的作品都是DIY的,特别粗糙。我很快就发了两张demo给他,过了几天又发了几首给他听。彧哥听完后问我,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都发来,这样可以看看是发一两张单曲,还是可以做一张专辑。我说,如果能做一张专辑当然好。后来就陆续又写了几首歌,包括《无花果》《送给你的礼物或许是我的全部》《你的选择是什么》等,都是后来《闭上眼睛的声音》这张专辑里的。
我记得当我把这些小样一首首交到彧哥手里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他说,“我知道你现在演出也挺多的,即使演出很累,你也得写,越是累的时候,你越能写出好东西。”这句话我记得挺深的,那段时间每次回到家都会想起这句话,我就会跟自己说,不能休息。又过了几个月,就出来了《闭上眼睛的声音》这张专辑,然后来北京定最终的版本,然后录音。
搜神记:他给你和乐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苦果:我和彧哥是互补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的不太适合作制作人,但是他适合和我合作,我适合整体把握一张专辑,他特别适合和我一起来做编曲,做后期的技术环节的东西。这是音乐上的影响。
在音乐态度上的影响就更多了。在遇到彧哥之前,我是特别懒散的一个人,特别随意,没有说为了做一张专辑,我必须要付出多少努力,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品质,我没有这些观念,以前自己做demo时,就是听着背景自己来。在追求完美的音乐品质这方面,彧哥对我的影响和改变都很大。
搜神记:你说自己比较懒散,但其实你挺高产的。
苦果:现在是越来越慢了。我刚组乐队的时候,可能一天能做一首,越到后面越慢了。
搜神记:为什么?
苦果:一方面是现在对呈现的效果、对完成度的要求高了,一旦你要求做到精致,自然就会慢。另一方面,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是,人年纪越大,经历得越多,外界事物带给自己内心的刺激和反应就会越来越迟钝,这是无法避免的。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写,什么都能写,写出来也不在乎任何人的评价,不在乎这个东西的意义和价值有多大。
搜神记:但你的旋律一直都是挺好听的。
苦果:旋律算是我的强项。我比较弱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的宽度或者深度。这两个弱点,也有人或多或少地提过,但现在我自己慢慢觉出来了。
搜神记:乐队一般都有自己比较明确的态度和想要表达的主题,比如反叛、自由,甚至愤怒,当然也有爱和希望等等,麻园想表达的是什么?
苦果:我是分阶段,年轻时有一段时间就写爱情。现在是彻底不想写爱情了。
搜神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苦果:一样东西,如果你得到了,可能就不再向往或者说得到了满足,那就会想寻找新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去关注一些群体的变化,比如疫情这三年发生的一些变化。而不应该只写个体的东西,天天写一些个体的东西,真的太无聊了。我现在写歌的时候会尽量避免写“我”字。
搜神记:这些转变跟疫情有关吗?
苦果:疫情这三年,我从网络上看到太多东西,那种人在大潮流中的微不足道和无奈。很多东西介入太深了,但是你又没办法说它到底是好还是坏,这让自己也很矛盾。尤其前两年和第三年还是不一样,甚至今年一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再回过头去反思,很多想法自己也还是矛盾的,也会推翻自己。第一年就是不停地问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第三年是另一种,是在想个体在大潮流中,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只能去接受,想逃都逃不了。
现在是第四年,会有很多真实的事发生,我会去想我们对社会的价值,作为一个音乐人,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想让它具有力量,具有代表性,具有发声的能力,而不能只是为了流量。
搜神记:你想发挥的价值是什么?
苦果:我说不清我能带来什么价值,但是我能把我放到一个听者的角度,我会去想在我某一段脆弱的时候、打退堂鼓想要放弃一件事的时候,或者已经是负能量缠身的时候,是哪些音乐让我觉得好像是找到了光亮,找到出口。这样的音乐一定是好的音乐。
能够给人触动,推动人有力量前行,治愈他或者陪伴他,这些是我认为的音乐的价值,也是我做音乐的方向。
04
我老怀疑我们的演出能不能让花了 150 块钱来看的乐迷们满意
搜神记:聊聊这次全国巡演吧。跨了两年、39 个城市,中间还有疫情的反复,非常辛苦。
苦果:在这次巡演之前,我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做过巡演了。我们原来策划了 2020 年的巡演,结果因为疫情彻底取消了,然后退票,但是又有好多乐迷挺希望看到演出的。到了 2022 年有了《闭上眼睛的声音》这张专辑,就想好好做一次巡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正式签约了新公司,公司也有一些演出的安排计划。对我个人而言,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做巡演或者自己组织一场演出去卖票。你知道吗,我老怀疑我们的演出能不能让花了 150 块钱来看的乐迷们满意,特别没自信,心里没谱。
搜神记:但一轮 39 个城市的巡演下来,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苦果:我觉得经过这 39 场演出,加上中间的一些音乐节演出之后,无论是从现场的把控能力、表演的专业性,还有唱歌、乐器等专业技能完成度等方面综合来看,现在的乐队和巡演之前的乐队,已经是两个乐队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后悔,我想如果能以现在的能力重来一遍,就太好了。这次巡演时间跨度很长,几乎是两年的时间,现在回头看,前面十多场的完成度其实很差,很对不起前面的乐迷,甚至说第 25 场都不如第 30 场好。这个巡演,把乐队好好磨炼了一下。
搜身记:“磨炼”这个词挺好的,巡演中有没有一些状况是差点把演出搞砸的?
苦果:这真的没有。小毛病小状况发生得太多了,如果算那些小的东西,我身上出现的错误太多了。因为我是主唱,有时候我边唱还要边弹琴,还要去踩效果器,所以出现小状况太多了,但这些不是我特别看重的,它们不影响最终的演出效果。
也有一些我原来没在意,但却能影响演出的环节。比如,前十几场演出我是不戴耳返的。而且我甚至心里抵触这个东西,之前的演出我一律都不用耳返,都是跟着现场演奏出来的声音唱。我们的调音师劝过我好几次,让我戴耳返,一直说带上之后会更准确、更清晰、效果更好,但我不相信,我总觉得摇滚乐不需要这个,差不多就得了。
我们调音师和我合作两三年了,实在受不了,都要被我气崩溃了,他说这音实在没法调。巡演后来的十几场演出,我开始戴耳返了。我一戴上,马上就发现以前不对,我都不是发现,是一戴上就知道了以前不对。我这个人有一些偏执的东西,实在太不好了。
搜神记:这一次巡演,最后一场安排在昆明。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有什么感受?
苦果: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很激动,但是好像我就是不怎么激动。还不如三年前回昆明演出那次受触动,那次回昆明演出,我心里想要让昆明人都看到麻园的成长。但这次内心特别平淡,而且演出效果不好,因为演出时,我的耳返坏掉了,很长时间我都听不到我的声音,这让我对这场演出不开心,还挺遗憾的。
搜神记:现在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乐队越来越红了?比如,音乐节上可以看到乐队的旗帜,演出现场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粉丝,喜欢这种感觉吗?
苦果:它至少让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增加一点信心,但这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到现在这个阶段,在舞台上已经少了很多攀比的心态,因为太清楚自己的音乐有多少生命力了,你真正能拿出来比的只有音乐。其他的一些什么影响力也好,流量也好,太不值得拿出来了。
搜神记:所以,其实你也不太介意音乐节上第几个出场?
苦果:我喜欢晚上演出,不是说排在前面就觉得丢人,因为大白天的太阳很晒。

05
我们没有任何风格,我们什么都想做
搜神记:生活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会像你在乐队一样特别坚持自己?
苦果:我觉得我是比较自负的,有时候特别固执,特别坚持自己,所以我特别矛盾。但骨子里确实又有自卑的一面。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自负还是自卑。
面对批评,我会去反思,我不会抵触,也不会说非要去坚持自己。这可能是我这半年来最大的一点变化。比如以前去街上,或者说做某一件事情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丢脸。现在遇到这种事情,我脑子里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必须走,必须做。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心智的成长吧。以前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东西会逃避,到现在这个年纪,经常要求自己去面对。
搜神记:你的歌里充满了昆明的元素,你家也是昆明的,你经常在昆明到处逛吗?
苦果:我平时很宅、很社恐。正是因为我逛得少,所以我一旦出去逛,就会有很多触动,这些触动让我有欲望去描绘昆明。
搜神记:比如《泸沽湖》,歌词很美,解读的空间也很大。
苦果:每一句词后面都有很大的空间,那时候我是知道的、感受到的东西太多,然后向外表达的又特别少。所以写出来的每一句词都是发自内心的,但我也没有特别多的隐喻,都是特别直接的。那是 2017 年前后,我处在一个比较难的时段。
搜神记:但你很多歌里的意象又是复杂的,而且可能隐藏了一些东西。这是你的习惯吗?你喜欢用旋律表达情绪,因此词就会显得含蓄起来?
苦果:你这个说法还挺对的。我用旋律表达情绪的能力比较强。我写歌时,不愿意细致地去判定这个词到底合不合适。我写歌太快了,很多时候都是即兴写出来的,它可能是一个画面,一种感觉,一个小故事,但又没有什么特定的事,这会导致歌词的连续性或者逻辑性很差,这是我的一个缺点。其实我表达的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心情。
但我不是瞎写的,虽然我比较宅,但写《泸沽湖》时我真去过。我承认写歌时我有些地方不行,但我没有任何欺骗,我不会瞎编,不会把别人的故事套进来,我大部分的歌写的都是自己的事情。
搜神记:你怎么看待摇滚?很多人会觉得,摇滚意味着热血、真诚、直接等等。
苦果:我觉得我和很多乐队不一样的一点是,我自始至终没有把摇滚这个概念当一回事,甚至有时候我不太想提这个词,这是我比较好的一点。我从来不在意这个词,甚至如果有人说麻园一点也不摇滚,我也不生气。归根结底,我们都是玩音乐,只是我们玩的音乐比较激烈、比较直接,比较追求真实和真诚而已。我们希望我的音乐包容性大一点,什么都可以尝试,去探索它的独特性,去挖掘它的创新性,仅此而已。这些事情主流音乐也在做,而且有的做得挺好的。
当然现在可能会出于商业的角度考虑,会给乐队贴上一些标签,这可能也是一种需要,但是从我自己内心来说,一个标签我也不承认。做音乐的人都希望海纳百川,能无限扩大自己的可能性。我很认同声音碎片的观点,我们没有任何风格,我们什么都想做。
搜神记:云南是很了不起的地方,走出了好几支优秀乐队,比如腰、春秋、山人等,你觉得云南给摇滚乐提供了怎样的滋养?
苦果:云南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文化容易让人产生倾诉的欲望,本地的原生态文化也会刺激创作动机。但我觉得云南对乐队附加的影响,没有像西安等地那样大,具体我又说不清楚为什么。我自己分析可能是,云南很质朴,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外面的文化输入比较慢,有一定的封闭性,这让它保留了一定的纯粹性,没那么复杂,做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单一,但也会让它更发自内心,不会人云亦云,这是比较好的。
不过整体来说,云南的演出机会少,内容产出也少,就导致我们当地的乐队必须不停找机会出来,又没有特别强烈的自信。我曾想过去表达和挖掘云南的民族多样、大美山河,但是没有想得那么深。
搜神记:没有演出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什么?
苦果:我是彻彻底底的宅男,不演出不创作的时候我都在宅。以前宅的时候还会打打单机游戏,但是这几年没时间玩游戏了。我是一个很封闭的或者说很自闭的人,老会让自己封闭起来,我打小就这样。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我可以一直待在家里不出门。但这两年,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有做不完的事,音乐制作本来就是很耗时耗力的一个事情,这就已经占据太多时间了。
搜神记:今年还有什么计划?比如说专辑、新歌。
苦果:今年其实有还蛮重要的一些事要做,我希望接下来能少点演出,然后稍微地回归一下创作状态。现在演出太多了,有点不能静下心来去创作。我蛮担忧的。我今年有些作品,小样出来了,但是没有时间去好好打磨,挺难受的。就是没有以前的那种状态了。越往后越难。
搜神记:可以聊聊你的家人吗?
苦果:我外婆是对我影响特别深的人。我小时候是跟着我外婆生活的。我母亲是年轻时候脾气比较火爆一点,我有点惧怕她,我父亲的脾气会更火爆一些。因为这些,到现在我和他们都比较缺失那种温暖的爱的表达。我和父母的关系没有和我外婆的关系那么温暖。但是我外婆已经走了,在她走之前,她是我在这个家庭里面比较温暖的一个存在。但我也很爱我的父母。他们也很爱我,只是不是那种表面的溺爱,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比如希望我好好学习,望子成龙的心态。
我觉得他们对我目前的状态应该是很骄傲的。因为我发现,我的一些演出视频,他们会转发。
搜神记:你有特别担心或者害怕的事吗?
苦果:我会担心哪一天我出什么状况不能再演出了,比如天天戴着耳机哪天耳朵聋了,或者不能再写歌了。别的好像没啥太担心的。如果有一天麻园的歌再也没人听了,那是我自己的原因,不是大环境的问题。
高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