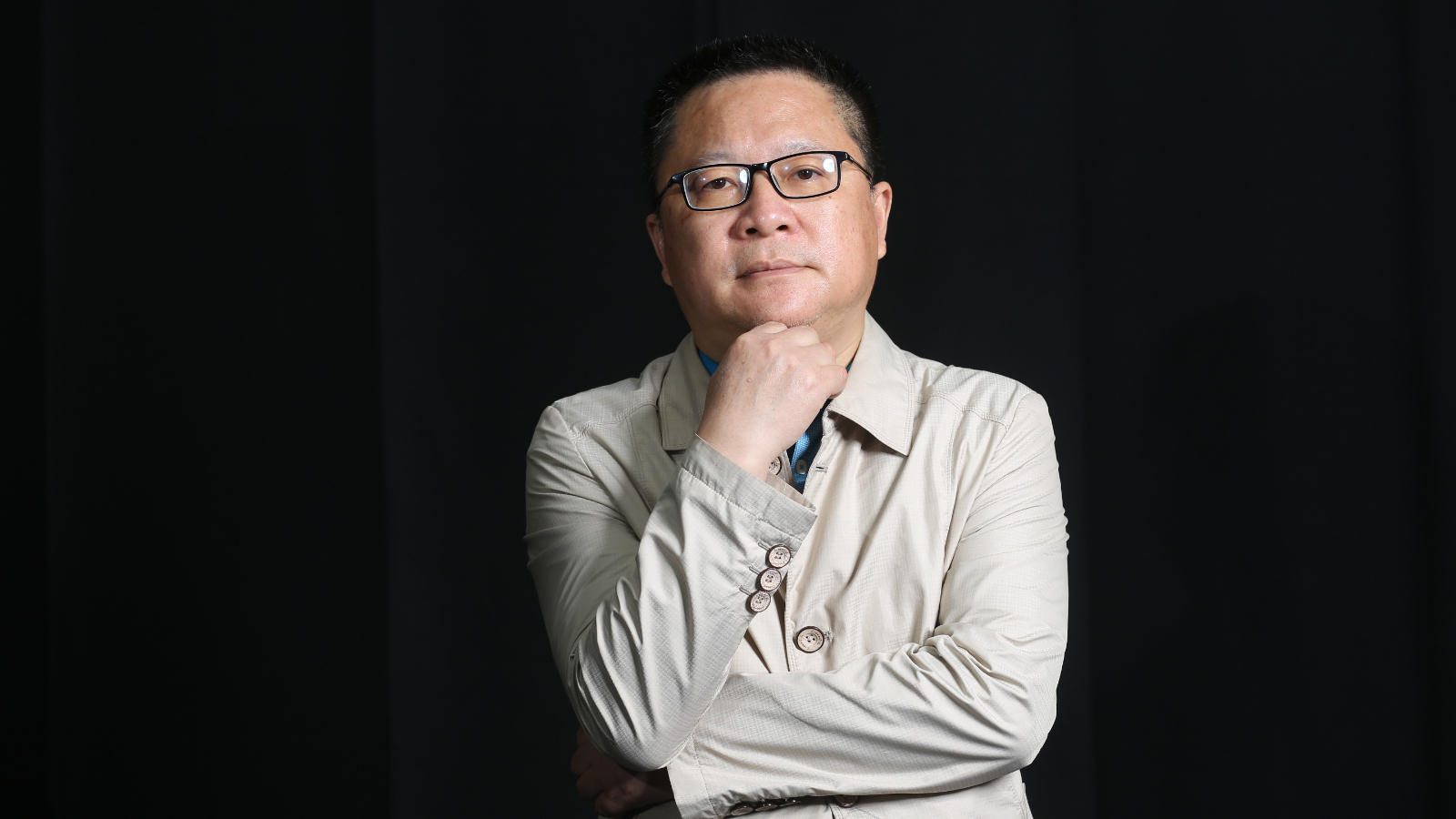李少君/文
有一个讨论,预测人类未来将留下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也许是一种称为精神的东西。”
精神,似乎虚无飘渺,但又真实确凿,我在疫情居家期间,就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每天大部分时间呆在狭窄的书房里,专注精神埋头苦读,安心隔离自得其乐,好像忘却了身边的现实。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充实,每天读圣贤书,感觉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都和我在一起,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我每天和他们对话,从他们的文字里吸取精神营养,浩然之气油然而生。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我读书最专注精神最饱满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出不去,干脆一切放下,另一方面,我觉得一种精神力量自远古而来,灌注到我心灵,让我内心充盈精神振奋生机蓬勃。
那么,真的有精神这样一种东西存在吗?我就结合诗歌谈谈我的体会和理解吧。
在我看来,中国诗歌精神的密码就在这么一句话里:“诗言志”。朱自清先生曾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的纲领”,但我觉得还不限于此,这应该是诗歌的最高标准和黄金律令。
“诗言志”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载,“诗以言志”(《左传》)、“诗以道志”(《庄子》)、“诗言是,其志也”(《荀子》)、“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尚书》)、“诗,言其志也”(《礼记》)。“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可见,在先秦前后,“诗言志”已成为诗歌共识。
那么,如何理解“志”?许慎《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志可以理解为意愿、意向、意义、思想等等意思,总之,属于精神性范畴。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唐孔颖达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为,相对而言,情是个人性的,志就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情是个人发动,志就有指向,有针对性,需要对象,需要协调,需要方向,还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觉得“诗言志”,可以理解为表达情怀、理想和志向,倡导某种价值,弘扬某种精神。
“诗言志”,诗来源于情感,但应该超越于一般情感的。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础上,本身就包含了情感元素。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情绪宣泄,诗应该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诗言志”。这就像郭店楚简里称:“道始于情”,我觉得不言自明的应该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道高于情,或道超越情。“诗言志”长期被看作儒家过于重视教化功能的僵化思维结论,就像“尊道守礼”一度被认为与人情世故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对立一样,其实,“道”和“礼”本身就是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之上的。
因此,我们可以如此论断:诗缘情是诗之基础,诗言志才是诗之超越,或者说诗之要求,诗之标准。“道始于情”、“道生于情”,精神的源头其实是情感。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经过疏导,就可能上升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因此,唯有“诗言志”,诗歌才能成为精神的传道者和弘扬者,成为精神性的来源,并具有繁衍能量和升华能力。
屈原就是践行“诗言志”的典范,是中国诗歌精神的最早代表人物。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屈原为这个世界立法。他追求灵魂的高贵和人格的完美,为了理想拒绝同流合污,宁愿舍生取义,其诗歌所传递的价值观,显现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染力。
屈原的《离骚》最能体现这种高贵而昂扬的诗歌精神,诗人从自己的出身、姓名以及爱好谈起,“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自我发现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并不断自我修行,超越自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表达自己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通过《离骚》等诗歌,最终呈现出一种理想人格的典范,体现了诗歌精神的力量,实现了“诗言志”的真正价值。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