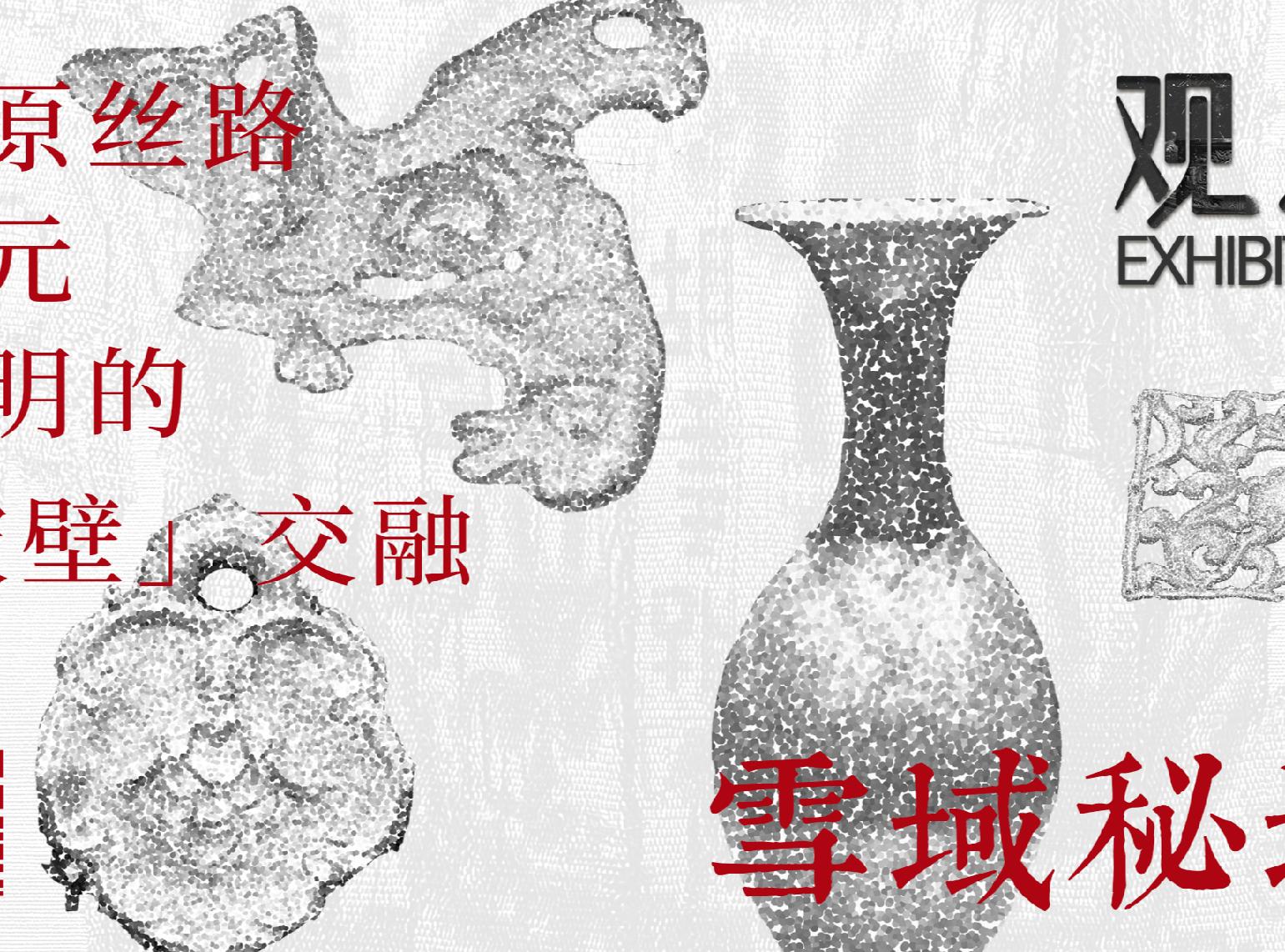钟立风以前叫钟立峰。父母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座顶天立地的山峰。
1995 年,他来到北京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山峰的“峰”改成了风雨的“风”。他无意成为父母期望中那样的山峰。那时他正在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觉得,哪怕这个“风”字有些缥缈不定,似乎抓不住什么,但至少更接近他的一种感觉。
改名字没有那么容易,先要发表一些作品,准备很多文件寄回老家。最后他成功了。
钟立风,中国民谣代表人物之一,1974 年生于浙江省丽水,1995 年开始闯荡北京。事实证明,他改的这个“风”字,是他音乐生涯最贴切的写照。在遥远的古代,《诗经》内容就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那个“风”是不同地区的音乐,实际上就是民谣。
但他不仅仅是一个民谣歌手,我来访问他,还因为他是我喜爱的一位散文作家。
他于 2004 年签约太合麦田,2006 年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在路旁》。2007 年组建Borges乐队并担任主唱。2008 年成立“野草莓”独立音乐厂牌。2011 年,他出版了个人第一本文字作品集《像艳遇一样忧伤》。迄今为止,他一共推出了八张个人专辑,并出版了六本文字作品集。
——也就是说,这些年来,他是几乎每年出一本书的节奏。因此,你也就能知道他有多么勤奋了。他今年最新推出的专辑,是他近十年作品的自选集,名字叫做《有一个你知道的人来了又去了》。他今年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弹拨者手记》。
我一直觉得他的音乐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游离气质,就如他的文字中有一层很神秘的雾。我一直好奇它们来自哪里。
钟立风认为,这还是跟他童年的成长经历有关系。
他的妈妈和姐姐都会唱当地的婺剧、越剧。他小时候,乡下的戏曲爱好者会自发组成剧团进行演出,一些其他地方的剧团——包括傀儡戏团——也会到他们的村庄巡演。他觉得有些气息一定进入自己心里了,虽然那时候他并不明白母亲唱的那些戏的内容。
前两年,他带着爱人回老家,再听母亲唱,就觉得那里面其实也有着他在歌里隐藏的那种情欲纷纷。那种唱腔与表演,用的是一种委婉的、往里收的、“不让你看见的那种看见”来表达。当他的妈妈唱出戏里面的第一句,“完全是心要碎掉了那种感觉”。那真是一种天分。
钟立风认为,自己身体里一定遗传了母亲的天赋。他对天地万物的敏感度,显然比一般人要更强一些。他也是以隐藏的方式来表达。他在自己的歌曲里埋下了各种各样的密码和线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抒情者,更像是一个并不经常显身的引领人。
他一直在歌唱爱欲、赞美爱情,甚至被一些粉丝称为“情色歌手”,但是实际上,他的基础体温一直是冷的。早些年,比如在《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中,他还是歌的主人。到后来,他不想当这个主人了。他希望自己能像一个中世纪的游吟歌者一样,哪怕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也不悲不喜地吟唱。他认为,从那种不悲不喜里面,更能获得一种爱的力量,甚至绝望的力量。
他那些不悲不喜的歌曲中,有太多无法直接说出的奥义。
他喜欢读老庄哲学,喜欢读《周易》。他是那种很受文艺女青年喜爱的音乐人,但他的生活看上去一直很平静。Me too运动火热时,他突然想自己是不是也会被人揪出来,他对我讲述了他的反思,但那只是一个博爱而淳朴的偶遇故事。他的团队里只有两个人,就是他和他的爱人。他一直是一个低调的人,他没有我见过的一些音乐人那么激情澎湃。他更乐于在不好不坏、不悲不喜中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他更多的营养来自欧洲文学,来自欧洲的音乐和电影。这让他的眼界、思绪、想象完全打开,天马行空,心游万仞。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大众语境里的民谣歌手。他的很多歌曲,如《盲人和一位女子去渡海》、《欲爱歌》、《你好,旅人》、《读诗远足》、《镜中》,那些旋律的源头,其实是斯拉夫,是中世纪,与那些他喜欢的法国、俄罗斯歌手有着同一个来源,调性自由,和弦丰富,大小调来回转换,但具有着诗性的流畅。
恭喜钟立风。他在音乐世界里的放任与自由,帮助他成为了格式化写作的成功逃离者。而这样的阅读与写作,又让他的旋律走向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他的和声更加丰满,他音乐中的转调、离调,具有了小说一样的故事性,以及诗歌的隐喻和美感。
为了承接住那些从文学里面溢出的部分,我特地约请了正在北京读文学博士的青年女诗人杨碧薇参与我们的聊天。她说,钟立风歌里有一种回环反复、恋恋不舍的旋律和情绪,这让她联想到了中国古典诗学里的“兴”。据考证,“兴”的原始意义中,包含“四手合托一物之象”的意思,初民共同举起一件物体而旋转,那是何等神采飞逸的气氛。
杨碧薇从钟立风的歌里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的回旋。
而我看到的,明明是一位来自中世纪的游吟诗人。就像他在《牛奶树》唱到的,一列时光列车倒退着驶过,他抱着一把鲁特琴,坐在教堂外面 ,唱着世俗的歌。


仲伟志搜神记:你在你的《书旅人》那本书里面附了一个阅读清单,其中好多书我都没看过。
钟立风:书最后面的部分吧。那个其实是编辑附的,以在书本里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的。其中有的书,可能只是在某篇文章提及了一下,也许我并没有读到过,或只是读了一些章节。但那里边绝大部分都是读了的。我读书的口味其实多少有些偏怪,那个书单有偏“保守”。
仲伟志搜神记:在我了解的范围内,你应该是音乐人中读书最多的一个。
钟立风:你说的这句话,是不是有点“你是写作人里面唱歌最好的,唱歌的人里面最会写文章的”这样的意思呢?哈哈。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并不设想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只是像“消遣”一样进入在书里面。如果你要那么说的话,其实我不仅仅想做音乐人里面读书最多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在大部分人里面都做到那样。
仲伟志搜神记:而且你读的书大部分是文学或人文领域的,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对你而言,文学和音乐是一种什么关系?
钟立风:我觉得音乐和文学对我来说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真正投入到阅读或者写作的时候,又完全是独立的,而不是说我在音乐之余,对文学浸入一点我的情感,或者浸入一些我书写的欲望。我现在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书写、阅读方面。做音乐的状态也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因为我自信每一年都能够有一些音乐作品完成,是水到渠成的一种状态。通过阅读,通过生活的积淀,那个旋律会慢慢、慢慢在自己内心里、头脑里形成,直到有一天灵感突如其来,会调动我所有过往的记忆,然后一首歌的完成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整理书稿上,包括看电影之后写一些属于自己的电影随笔,循环往复,这一切又会牵动我旋律的发展。
仲伟志搜神记:都是艺术电影、独立电影,肯定不看大片吧。
钟立风:不看大片。
仲伟志搜神记:听你的歌,感觉挺神秘的,有一种说不清的游离气质,无法阐释,想象空间很大。这种神秘感是怎么形成的呢?
钟立风: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跟童年的成长、遭遇有关系。前两年我带着爱人回到老家,她也很有感触。我母亲会唱当地的戏剧,婺剧啊、越剧啊。我小时候,乡下的戏剧爱好者他们会自发组成剧团表演,另外,其他地方的一些剧团,包括傀儡戏团也会巡演到我们村庄,我觉得当时有些气息一定进入我心里了。我姐姐也跟着妈妈学唱了一些。这次回去,我说姐姐给我唱一段小时候我听你们唱过的戏吧。然后姐姐就活灵活现地表演,挺好听,声音也很悦耳。但过了一会儿我妈妈从厨房里出来了,看到姐姐在唱戏,就跟我姐姐指出某句唱词该如何,某个动作又该怎样表达,而后她在示范的时候,我们就呆住了,因为我妈妈一下子就入戏了,完全进入到角色里面,是一种,怎么说,她的声音唱腔里,有一种令人身体都会起反应的东西,心碎的,感人的,但又是克制收敛的。那真是一种天赋。我觉得我身体里有母亲那样的东西,一种天赋,一种对这个世界的领悟。我说得比较大,真的,是对一个世界的领悟。我觉得我对一些东西的敏感度比一般人要强一些。比如说一些不是我的作品,当我进入的时候,我也能瞬间发掘到那种人性的涤荡,这时候许多人,包括音乐同行,他们惊叹,××歌手还有这样一首作品啊!?
前两天我翻唱了一首已逝歌手高枫的歌,叫《雨》。高枫被大众熟知的歌曲都是《大中国》、《笨小孩》、《春水流》那种歌对吧。其实老狼演唱的《美人》也是他的词曲,他自己也有一个版本,完全和老狼弗朗门戈的版本不同,也有一种令人心碎的东西在里面——美人嘛,总是令人悲伤心碎的,哈哈。他的这首《雨》就更是有一种低调的但又是情感非常饱满的作品。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感受到这首歌里面不一样的情绪,我就跟爱人说,我怎么没有写出一首情感那么进入的歌曲啊。她说表达方式不同吧。但是我觉得的确没有进入到高枫在那首歌曲里面的那种表达。那个感觉也像是与天地宇宙达成某种默契的状态,虽然我没有写出它,但我至少发现了它,情感一下子与它相融。我想说的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领悟力还是挺强的。我想这是天赋,是妈妈遗传给我的,妈妈进入到那个戏里面第一句,就完全是心要碎掉了的那种感觉。
仲伟志搜神记:我是北方人,对浙江地方戏不是特别了解,听不懂,但也觉得美。
钟立风:小时候我也不明白母亲唱的那些戏曲的内容,慢慢、慢慢地,就觉得里面其实也像我后来在歌里面隐藏的那种充满爱欲、情欲纷纷的状态。但是它并没有用一种特别情色的话表达出来、展露出来,而是委婉的、甚至是往里收的、“不让你看见的那种看见”来表达。
仲伟志搜神记:这本来就是江南戏曲的一个特点啊,妇女参与的也多,风格软糯、婉转、甜媚,不会像北方戏曲那样抒发得那么激烈。
钟立风:是啊,它会悄悄藏起来一些东西,用隐喻的方式来表现。所以我的歌曲里也像埋下密码、埋下情事一样,好多线索埋藏在里面。这是我的表达方式,以隐藏的方式来展现。这是我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似乎有点晦涩,但真正懂我的人其实也不少,而且跟岁数没关系,前两天去南京做活动,一个 16 岁的女孩就像你们问出来的问题一样,说你怎么会把那么多意象放在一起,这种意象的表达不落俗套又很吸引人,这些感觉在其他歌手、音乐人的作品里是听不到的。
仲伟志搜神记:当然这也是你们吴语方言的特点。
钟立风:对,是的。所以我后来形成的这个歌曲风格,与这些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是我在过去不会想到这些,人家说谈谈家乡,我说我对家乡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谈到民谣,想想哪里跟浙江有关系啊,浙江以前出名的歌手,都是白雪啊、刘海波啊,这些通俗类型的。所以,他们很疑惑,浙江怎么还会出现你这样一个“怪人”、会有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我的创作,虽然跟北方的野孩子或者是苏阳他们表达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但毕竟也是同一类型非常个人化的独立表达。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怎么喜欢上音乐的呢?
钟立风:最初就是因为母亲戏曲的影响,后来和很多同道中人一样,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碰到一把吉他啦,或者从五斗柜里翻出一支重音口琴,有一天,翻到口琴,竟然无师自通吹奏出像样的旋律!但我觉得主要还是承继了我母亲那种对天地万物的敏感吧。不用人家教,也没有学过什么乐理,就是看点书什么的。做艺术天分还真的很重要。后来差不多十六七岁的时候,不读书了,我跟爸妈说,我想去杭州拜师学艺,学弹吉他。反正读书肯定是不想读了。
仲伟志搜神记:那时候父母会不会很生气?
钟立风:父母没有生气,相反还蛮支持我的,其实我在家里是一个好孩子,很乖的。小时候会在菜园子里陪奶奶种菜,她教我背诵三字经。后来家里要盖房子,尽管家里请了工人,但我也一起帮忙干。前些天我在外地,一位诗人朋友一直盯着我的小腿观看,而后他问了一句:立风,你以前是不是经常踢足球的?我有点难为情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小腿有些粗?这应该是小时候家里盖房子,我挑砖什么的压坏的,要不然我也许会长高一点。我哥哥就很高。我写过一首歌,《抓住他》,里面有一句歌词:她有白皙的小腿,忧伤的眼睛,她在阳光下奔跑,显得生机勃勃……每次演出唱到这句,我都会看看自己的小腿,哎,粗壮的小腿……
因为还有哥哥、姐姐在家里,父母也同意我离家,拜师学艺,给了我拿了几千块钱,因为要买乐器。后来我到了杭州,找到了浙江歌舞团的老师宋家春先生,他既是提琴手,又是那个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吉他手,他很喜欢我,还是因为天赋的关系吧,几堂课下来之后,他就为我单独授课了。我记得,有一阵子我跟房东的女儿谈恋爱了,你知道十七八岁的时候,那种要命的感觉,我老师知道后非常不高兴,狠狠地批评我,还特意跟房东讲,管住自己的女儿…….叫我赶紧停止恋爱,不然他就不做我老师了。现在我回忆起来,并非老师不开明,而是因为那个女孩,我似乎根本没心思弹琴了。但总体来讲,我一直害羞,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我都脸红,不敢上桌跟他们一块吃饭,躲得远远的,或者逃掉,一整天不回家。家里来了什么漂亮女亲戚,明明很想接近,但也只是默默地、偷偷地看。我觉得我爱好写作、弹琴,跟我内向的性格也有关系。
宋老师既古典又现代的音乐修养丰富了我,加上在那个时候,北京这方面所谓的新音乐的春天就开始了,这种影响其实很大的,我们听广播,买磁带,受到强烈的刺激,竟然也开始词曲创作了,虽然那时我已是一名专业乐团的吉他手,但我觉得不能在南方待下去了,我要闯荡北京!那是 1995 年。
仲伟志搜神记:你在那时就开始写歌了?
钟立风:已经开始写歌了,因为当时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乐手了。当时我的那些同学、同事,每天比的都是比赛谁练琴的时间多,你一天练 8 个小时,他一天练 12 个小时,有的几乎不睡觉,直接 24 个小时!练疯了的这种。大家一律讲究练琴的苦功和技巧。那个时候我就表现出来一种“创造力”。比如那时我们也去夜总会演出,夜总会的歌手们都唱一些港台流行歌曲,那作为乐手你要按照磁带一模一样地扒,那很机械,也很浪费时间,但对于职业人员来说,也是一种专业,必须要做到的。只是我不愿意这样,那个时候我就表现地截然不同,在乐队里,一到我独奏的时候,歌手的眼神望向我,那意思说,怎么不对呀,根本没有按照套路出牌呀。但我还是在那个和声里面,在那个节奏里,并没有说自己完全另起炉灶。也许我音阶弹的没有那么快,但是我一揉弦、一推弦,那个独特的味道就来了。很快,他们就熟悉我的感觉了,他们觉得虽然有些怪,但怪的很有味道。反正一直以来,朋友们都比较喜欢、欣赏我。
然后文学的刺激就来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警察,现在还在当警察,但是他特别喜欢文学和音乐,他当时的样貌气质,就是当年的臧天朔和窦唯的结合体!你可以设想一下啊。有一回他带了几个朋友到了我弹吉他的夜总会,我想,他应该是来执行任务的。恰巧他们到的时候,我正在按照我的方式进行一段疯狂的吉他SOLO。据后来朋友告诉我,他当时就很激动,赞不绝口:弹吉他,就得像他这么弹……很快我们就成为朋友,常去他家玩。
我在他家里看到好多书,有一天翻出一本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天哪,我惊到了!我觉得那本书比《活着》、比《许三观卖血记》都要刺激我,因为书名首先就刺激到我了,一部小说怎么能叫这样的名字?我觉得这多像一曲音乐或者一个梦境的感觉啊,然后就被这种先锋小说所迷恋了。后来我又看到格非,发现了苏童,苏童那个《我的帝王生涯》也让我兴奋,故事也许忘了,但直到现在那种最初的气息还依旧在体内。还有格非的《褐色鸟群》以及陈染这样的女性作家的文笔,都令我迷醉。而这些先锋派跟那么多西方作家都有关联,于是沿着余华、格非、马原他们这种风格,又去读国外的东西。那个时候是自己的成长期,读了大量这样的作品。
仲伟志搜神记:原来你的文学启蒙受益于一个警察。不过那个时候,警察中的确也有大量文学爱好者。
钟立风:那个警察也很逗,刚才说了,他也会写歌。当时在杭州做音乐的人不少,但真正写歌的就两个,一个是警察,一个是我。这个警察朋友会说,今天陪我去执勤一下,我说好吧。然后就坐着警车抓小姐。感觉也挺荒谬,你瞧,我一个文气的、特别害羞的、特别不会说话的人,天天跟着他去抓小姐,这成何体统啊!哈哈。他的家在杭州植物园的一个小院子里面,他不执勤的时候,我会从歌舞团宿舍骑着自行车绕过一条比较偏僻的小路到他的家里,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的家门口是一个大大的池塘,他的小屋里有吉他、贝斯,还有个架子鼓,我们时常搞即兴合作。但我记得他并没有推荐说看看这本书看看那本书。有时候我去他家,他可能还在外面执勤,我有钥匙,我先到了就躺在他的小床上读《河边的错误》。当时也读不太懂,但是已经被深深吸引了。
仲伟志搜神记:刚来到北京是一个什么状态?
钟立风:到了北京来之后,又遇到这样一些怪人。比如我在酒吧里唱歌,那时候在西单,有个乡谣酒吧,北京第一家只演出原创歌曲的,老板原来是在汉唐文化做企划,出来后开的酒吧,就收留了一批像我这样从异地他乡抱着吉他来寻求生路的音乐人。很多朋友都是在那里认识的。老板说,周三你来唱,周四他来唱,周六稍微热闹一点,来个乐队唱。唱一次有四十块钱,我基本上一周的生活费就四十块钱,生活也就这么过来了。
我们当时在那样一个环境下生活,也有各种各样的奇遇。有一次唱歌,下来休息的时候,一个大哥模样的人就过来了,旁边还有几个小弟跟着。大哥说,你唱的歌我挺喜欢的,都你自己写的?他这么一问我好像有点心虚,就说是吧。他问那你住哪里呢?我住在厂桥那边一个平房。他说,自己住啊?我说,是。他说那去看看吧。看什么呀?我心里想。不过又觉得他挺好的,唱歌结束,开车就去了。那天还好他来了,因为北方冬天要自己生炉子,我不会生炉子,他一进门就感觉到有煤气了,稍不注意就会煤气中毒。他说炉子不是这样生的,应该这样,一定要通风……一个大哥模样的人帮我弄炉子弄个灰头土脸的。现在回想,荒谬也温暖。然后大哥就把大哥大拿出来了,拨通之后就说,××姐,你在家吧,我有个小弟,今天晚上过去要住你那。我说今天就去?要不然改天?他很坚决,说不行,你这太冷,你不会生炉子。后来看我犹豫,他说你可以先去一下,如果不行再回来。然后真的开了车就去了,在五棵松,一个很大的房子,好多间房子,我选择一间最小的。里面的确有一个女人,一个忧郁的女人,住在其中一间。有时候在夜里会听到哭泣的声音,好恐怖呀。我胆子很小,也不敢过去看,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说,大哥要不我走算了。后来又回到我的平房去了。
我觉得这些经历好像跟自己以后的创作都有关系。感觉挺离奇的。后来像我歌曲里面那种离调的感觉,那种隐约的感觉,难道是凭空而来的吗?还有,那种哭泣声难道是我幻想出来的吗?真的有那个女人吗?真的有,确实有。后来那个大哥也不见了。当时我还写了《吸烟的女人》这样的歌曲,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女人出现了。后来了解到,她身上全是病,肾病、胃病,还经常看到一个男的来看他,动不动两人不高兴,而后男的转身就走。《吸烟的女人》这首歌,就是写女人那种落寞。当时那首歌要出来的话,也许会成为流行歌曲——午夜的城市街头有一个女人,一个吸烟的女人,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从哪儿来,也许她不要谁来把她关怀……美丽孤独的女郎,就让夜风吹去你的忧伤,如果你心中有什么愿望,就对天空星星讲——旋律、唱腔,有点郑智化的感觉。
当时毕竟也岁数小,自己表达能力或许不够,但确实是真挚的感情。这首歌写出来以后就天天在酒吧唱,经常来泡吧的人就熟悉这首歌了,每次演唱大家都会点,小钟小钟,《吸烟的女人》,我就说好,前奏一出来,所有的女人都会做出那种很酷的很冷漠的吸烟的姿势,哈哈哈。
我觉得我们这批歌手之所以跟以前一些流行歌手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实打实的,就是自己抱一把吉他,用自己没有训练过的歌声唱出来的,真的是生生唱出来的。当然久而久之,也就摸索出来有些歌唱的技巧,这好像跟写作一样,不断地训练,就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了。当时我写了一首歌叫《阿波罗》,挺异域风格的,那时我们从酒吧结束回租住处,常常听到天桥上,有人喊,喂,阿波罗!阿波罗!就这么叫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比我们更上代的歌手,比如好多成名的流行歌手,他们的表达场所是夜总会,唱的也都是港台流行歌曲,所以他们唱歌会有一种“油”的感觉。我们这批人,真的就是真刀真枪地唱出来。我的嗓子一度感觉就是坏掉了,一到假声嗓子就不出声了,假声被假声吃掉了,要恢复好长时间,让自己保持不说话、不唱歌。
仲伟志搜神记:酒吧里边乌烟瘴气的,对嗓子也不好。
钟立风:唱着唱着歌,底下黑社会人士就打起来,那个玻璃渣就直接飞溅到台上来了。那边有个诗人在那喝醉了,开始骂人。另一个美院的学生,泡妞泡得不成功,在那边痛哭流涕。也有某所大学的一个寝室的女生,说钟立风我们全部是来听你的,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出专辑,所以这样的支持很重要,是给自己鼓劲、打气的感觉。所以虽然酒吧乌烟瘴气,但又是一个奇妙的所在,可以遇到各种人,发生很多蹊跷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训练吧,我想。训练很重要,之后就把“训练”融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 钟立风和他的妻子相识初期(大约 1996 年)所摄。一次,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见到这对“最佳拍档”,惊呼:哇,你们还在一起,太有勇气啦!钟立风笑说,早年间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花心”、放荡不羁,没想到到头来,他却成为这些朋友里最钟情、情感最为稳定的那一个

▲ 近照。钟立风夫妇与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在采风途中
仲伟志搜神记:那时候你的音乐还没有跟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吧,是什么时候有了这种自觉呢?
钟立风:是的。尽管我一直都喜欢读书。1995 年到了北京,之后认识了晓利、小河、周云蓬,还有陈羽凡他们,当时基本就在一个酒吧唱歌,各自演唱自己的作品。酒吧里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画家、诗人、艺术家什么的,都在酒吧里出现了,然后跟他们就有一些交往。这些艺术家、诗人、画家也特别喜欢我,骨子里的喜欢。我回想,之前结交的女朋友,画画的居多,但都是偶然相遇的,并非特意寻找。大约三五年之后,我就有些自觉性地想以一种文学的感觉来进入音乐,我乐于在音乐之外找到种种艺术的可能,所以在同行苦苦做歌找门路的同时,我反而不是很“在意”音乐,我整天闲荡、逛书店淘旧书,看话剧、看展览,有些漫无目的的感觉。但是我这么做,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你看,比如小河他们非常懂得如何制作音乐,甚至在出租房的旁边,自己买砖头买水泥建造一个录音室,然后买来一些专业的设备,开始自己录专辑,厉害吧!我一直到现在,都搞不定电脑,对所有技术一点都不通。当时我就想,既然文学、艺术于自己那么投缘,那不如多多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东西吧。久而久之,就真的是因为文学的力量,改变了我旋律的走向了。
仲伟志搜神记:你在写作方面比很多作家都要勤奋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呢?
钟立风:我想想最初我为什么开始写作……当时住在后海,宋庆龄故居旁边不远,一座挺老的筒子楼,住的都是当地的居民,老大爷、老大妈。我通过朋友租了一小间,住在三楼,一打开窗就是后海,游着很多野鸭子。那时候还在非典之前,后海很安静的。我觉得整个环境就是一个小说家能进入到的那种情境。当时写了一首歌就叫《窗前一片海》,“窗前一片海,海上的人自由自在,有人在轻轻的唱,歌声漂向远方,在海的中央,有个黄色的姑娘……”
但那之前并没有开始文字创作,但很快啊,最初到北京的那种寻梦的那种激情就消磨掉了。本来刚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张楚、窦唯那个——怎么说——比较纯粹的年代吧,我想起,还有更早一点的艾敬,她的歌曲《艳粉街的故事》、《外婆这样的女人》,太迷人的表达,真正的民谣!我的整个情绪也是很上扬的。后来,没有几年,无论是自己还是整个歌坛,那股迷人的上扬的音乐势力就没有了。于是,我想到了写作,并且真的就开始写了,那应该是 2000 年。我最初写的是短篇小说,几万字,几千字的,几百字都有。一种做梦或着魔的状态,我甚至并没有觉得是我在写,而是某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我手中的笔,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我感觉十分快活,也十分孤独,跟唱歌完全不同的快感和孤独。
当时也没有电脑,就是一笔一笔这么去写,堆积起来好多的手稿。但也没想过要去投稿,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切,就是自顾自地写,有时实在兴奋,需要排解,就邀请朋友上门,开始朗读。有时候没有朋友来,我就给朋友打电话。朋友那头问,干嘛呢,我说,你要是有空,我读一篇新写的小说给你听一下,朋友说好啊。结果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一个小时还没完……后来我再打电话,对方就害怕,不接了,哈哈哈哈。
仲伟志搜神记:你现在的爱人、当时的女朋友,应该是你的第一读者吧。
钟立风:差不多吧,她也一直鼓励我,她有自己读书的方式。说实话,其实在音乐方面也都是她替我把控,一首歌曲完成了,她会跟制作人、缩混师说,鼓的声音往后一些,弦乐的部分音量再来一点,人声有点硬…….她虽然不从事这一行,但是她有很好的直觉和敏感度。有时候她会觉得我写的有点满了,叫我剔除、剔除。因为她也知道,写作者沉醉其中,情绪难免有些激动而不够客观、冷静的。这时候往往是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我实际上也知道,写作就是一个剔除的过程,剔到最后一个字都不能再剔了,这个就可以交出去了。
仲伟志搜神记:你的音乐也是没有那么用力地去表达,留白很多。这样才有想象的空间,才有神秘性。
钟立风:对,你刚才说到写作,大概就是那样写的,我悲伤地想,如果在音乐上没什么发展,正好还有文学上的一些能量,然后就写,就累积了一些稿子。后来是受到周云蓬的启发——他自己也是积攒了一本诗集,就自己印了出来,然后就跟自己专辑一起,巡演到一个地方卖到一个地方。我爱人说那我们也自己印吧。印了之后,突然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被“理想国”看到了,就是《像艳遇一样忧伤》。编辑找到我说,能不能让它正式出版。通过这件事,我就有一些信心了,就一本一本继续写下来了。
仲伟志搜神记:其实很多作家,比如福楼拜、卡夫卡,他们最初写出的文章都是先读给朋友听。你周围的那些朋友,对你的发展很重要的。
钟立风:对,当时酒吧里认识的一些画家、诗人、作家朋友,他们给我的那种艺术上的刺激、眼界上的开拓很重要。我晚上在酒吧唱歌,白天就跟他们在一起,去看画展,听他们谈论诗歌。我觉得那几年的时光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直到现在,我对他们都特别有感激之情。我觉得来到北京要不是遇到他们,我的世界里如果没有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只是跟唱片公司接触,只是跟自己做音乐的朋友接触,那我写作的方向、谱曲的方向就会不一样,我人生也就不一样。
我一直觉得任何艺术都渴望获得音乐的属性,所以很多文学、雕塑、绘画作品,但凡说到它们好的时候,就会说具有音乐性,是不是?但是作为我本人来说,真的会因为读到一首好的诗歌,读到一篇好的小说,让我的旋律走向发生改变,让我的和声更加的丰满,让我的音乐转调、离调,从而更加具有小说一样的故事性,具有诗歌一样的隐喻性。
因为我是一个写作者,很多人会说钟立风你的歌词写得真好。其实他们忽略了,我真正的好处是在旋律上。你可以说是旋律上的一种创新,就是一直想要发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又在调中。就像诗歌一样,不管给人家多少想象,不管它有多少隐喻,这些东西都包含在它的格律里边,我的作曲好像也是这样。
仲伟志搜神记:你现在出到八张专辑,你最喜欢哪一张?
钟立风:我觉得应该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其实每一张专辑都有着自己的成长,都是通过自己内心的丰富、眼界的变化,那些旋律、和声、节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做艺术一定要朝前走,要创作出新的东西来,老调重弹就没有意思了。但我们现在听到那么多的流行歌,那么多所谓的民谣歌手,那个旋律简直比退步还退步,比老调重弹还老调重弹,就不好玩了。当然我不会去说他们不好,我觉得这太正常了,要是所有人像我这样,想想也是无趣,不是吗?而且这个年代呈现出来的,不管好坏,并不仅仅是这个年代的原因,而是经过漫长时间的流变,到了这个节骨眼了,不得不呈现出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所以,我基本上不像许知远那样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哈哈,但是也必须要有那样的声音,那样的存在,世界不好不坏不停地在运转,各个环节都必不可少。只是我认为,无论哪个年代,世界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特别地充满希望,所以才没有什么抱怨,选择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音乐,发现不同的自己。
仲伟志搜神记:不好不坏,这是你的人生观?
钟立风:对,不好不坏。就像我无论写歌,还是在平常生活中,尽量不要让自己搞得很愤慨、很激情,或非得要充满希望什么的。我在歌曲里唱过,凡事皆有神迹,只需用心体会。还有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愤世、但嫉俗的人。如果愤世,就难免要参与人群了;而嫉俗,只是自己个人的事,选择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一位老师谈及孔子的弟子仲由(字子路),伟志兄,你本家啊!老师以他的名字谈到自由——所谓自由,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我乐于在不好不坏、不悲不喜中获得我想要的东西。
但生活本身是可以找到乐趣的,甚至可以找到一种与之游戏般“对峙”的感觉,我说的对峙,不是真正地对着干,而是一种温柔地碰触。就像在生活里,你按照你的直觉、第六感去“趋吉避凶”,如此来找到一种属于你自己的生活调性。每个时代或许都有它独特的运转轨迹,要知道如何“明象位,立德业”,不要轻易让自己卷入某个不明地带,然后遇到什么样的冲击,我喜欢看张中行先生的书,他是一个低调者,一个趋吉避凶者,他身上有我很欣赏的调性。
仲伟志搜神记:你受“黄老之术”影响很深呀。
钟立风:对,我这两天还想着清朝胡文英说的庄子,“眼极冷,而不管是非;心肠又极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我对世界充满了爱,但是有时候我挺冷的。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发生了灾难,很多人同情、哭泣,我却有些淡漠的感觉,激荡不起我心里很多难过啊、同情啊,哎,我是不是有问题啊。可是这能怎么办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
但是我对周遭一切,还是有爱的,尽管这个爱字也很泛滥啊。前两天Me too运动正火热,我突然想我是不是也会被人揪出来,天啊,这可怎么办?我想起自己有一次,是博爱吗,还是多情的表现呢,那天从地铁里出来下雨了,下得不大也不小,我正好带着雨伞,然后还要等着坐两站的公交车。等公交时,我身边有一位年轻女士,就淋在雨中。我就直接走过去,如此,我们俩同在一把伞下,她看我一眼,有几分感激,但又有点不安,毕竟周围还有很多人,为何我偏偏为她服务呢?然后汽车等啊等啊,怎么也不来,其实就有一种默契产生了,如果有一人开口说话,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故事,但是我也没有,我也不敢。终于车子来了,怎么办?按照一般人,很可能同时挤上去,挤在一块,那没话都有话了。可我等她上去之后,我却迅速跑到公车的另一个门,就故意消失了。Me too运动来的时候,我想了想,这件事可能没事,但另外的故事会不会有事?哈哈哈。其实我在地铁里看到女士都会让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爱。我对身边的、具体的人和事还是充满爱的,从来不会冷漠的。这其实是一种淳朴吧。我觉得人活的有智慧最重要,而智慧的底色应该是淳朴。对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更大的事物,我是冷眼看穿那种感觉,但周遭的一些小事,却又让我不能忘情。
仲伟志搜神记:很多人说你是“情色歌手”,哈哈,赞美爱情,歌唱爱欲,但往深里听,我觉得其实也很冷。
钟立风:对,挺冷的。最初的第一张专辑《在路旁》,《麦田上的乌鸦》、《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有些温情的东西,那时年岁比较小一点,毕竟是初次上手,“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很爱你,长了这么大第一次说给你听。妈妈我告诉你,我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她的模样就像年轻时候的你”,自己完全是歌的主人。到了后来,我不想当这个主人了,我想走出来,我想更加客观一点,更加冷一点。我希望像中世纪的游吟歌者一样,他们拿着一把鲁特琴,哪怕唱的是一个悲惨、绝望、痛苦的故事,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情感投入进去,他只是还原事件的本身。我希望不悲不喜地来吟唱。但是真正懂得这样一种情绪表达的人,他能够从不悲不喜里面获得那种爱的力量、那种绝望的力量。
仲伟志搜神记:就如同罗兰·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
钟立风:就是那种,感情降至冰点,更客观,更冷静。有些时候也表现绝望,但是表现绝望的目的,正如我在书里看到的一句话,绝望也有绝望的力量,就像希望也有希望的无能。我的歌里不太说到希望或梦想,这种大词在我的歌里极少出现。(哦,在那首《澜沧江》里出现过,不过,那是一种“顺流而下的绝望”和“逆流而上的希望”,仍然是一种不悲不喜。)长沙有一个作家叫做何立伟,我不认识他,但我最初到北京的时候,也买来他的书读,有朋友把他的朋友圈截图给我看,他说他喜欢我的歌曲。喜欢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歌里面很少那种大词,完全就是细微的那种表达,我觉得他说得挺准的。

仲伟志搜神记:你的表达都是那种举重若轻的,这也是一种艺术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把重的东西很轻地拎起来的。
钟立风:反正这些力量,这些表达,说实话都要感谢文学,感谢博尔赫斯,感谢福楼拜,感谢E.E卡明斯,感谢马克思·雅各布,感谢加缪!还有那些艺术家、画家,他们画里面每一笔线条的表达,我感觉真的把我的旋律给拉扯出来了。
仲伟志搜神记:你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看你书单里的这些书,主要是来自欧洲吧。
钟立风:但是反过来就是,到达一定高度的时候,中西方就都打通了。我做个比喻吧,就比如说我读到卡夫卡那些东西——你没必要离开自己房间,你待在自己屋子里听音乐就行,甚至不用听,等着就行,甚至不用等,保持沉默就行,世界会主动地朝你走来,由你自己去揭开他的面纱——我觉得这就是老子的哲学,无为而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感觉。他真的不去听不去做吗?不是,而是说没有很多功利心,没有很多刻意性。后来我把卡夫卡读完之后,就发现他对中国真的很迷恋,他读《聊斋志异》。他送给最亲爱的小妹的一个礼物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我还记得他送妹妹的赠语是:“致奥特拉,在一片嘈杂声中跃入轻舟的跳跃者”,也是一种轻盈的意象,非常中国的那种形而上的感觉,一种属于故去年代的自由中国人才有的雅气、人文。
仲伟志搜神记:对,跟卡夫卡一样,你的音乐中也有很多不可解释的东西。
钟立风:还有就是一种冷的幽默感,在我的歌里面也会出现。比如《海边的告别》——在海边,有人被对手剥下了最后一件衣服;在海边有人郁郁寡欢,变幻着节奏——后面就是,“在海边红红的苹果,浪打浪”,有一些无厘头的感觉。普通的一些乐迷他不会注意到这些细微的表达。只有对艺术感兴趣的、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他才会注意到。甚至像罗大佑、李宗盛那些歌迷也都不会感受到,这也是我们内地的创作人跟他们不同的地方。他们达到了一种雅俗共赏,达到了文化融合的一种高度——我觉得算是高度——而我们呢,还是有走“窄门”的感觉。
仲伟志搜神记:所以我说对了啊,你音乐的养分的确来自欧洲文学。
钟立风:我的养分在于欧洲,我读老庄哲学,或者我喜欢读《周易》,感觉自己好像往深了走。但是读欧洲的文学,就会把你的眼界、思绪、想象全部打开,就是扩散了、天马行空了,就是想象力无穷的感觉。还有法国和欧洲的电影,我简直是太迷恋了。我觉得好的电影真的就像是文学书籍,读一遍不够,那些秘密往往藏在特别不起眼的画面的一角,这边主人公在交谈,那边面墙上挂着一幅画,那幅画可能就是电影的点睛之笔。
仲伟志搜神记:是,听你的音乐,有时就像是从法国电影穿越过来。
钟立风:还有法国音乐家,比如塞尔日·甘斯布,他是歌手、作曲家、钢琴家、诗人、画家、作家、演员、导演,被称为是法国歌坛的波德莱尔。他在世的时候也遭人忌恨、诋毁,因为他跟当时几乎所有最有名的女影星都上过床。但是当他去世的时候,大家都流下眼泪,整个法国降半旗为他致哀。他的曲风多元,难以归类,但是作品深入人心。这些欧洲的音乐作品,你听不懂他的歌词,但是他的节奏、旋律、歌唱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能感受到一股股文学的热浪向你袭来,哪怕它是一种特别低微的表达,这就了不得了。有几个歌手,他唱的简直就是如同诉说了,他根本没有说用高八度强制性把你拿下,他完全像是一种夜晚的情人一样的低语和诉说,你可以睡着了,可以爱搭不理,但他的音乐就有一种魔力,一种文学艺术的魔力,把你牵引出来,让你重新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我觉得国内没有这样的歌手,如果有这样的歌手,我觉得那就是我。
仲伟志搜神记:“像是一种夜晚的情人一样的低语和诉说”,这句话,形容你现在的旋律、节奏和嗓音,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你这个趣味,就与大众趣味相去甚远了。你应该也不想讨好大众或者所谓的“主流”了。
钟立风:不可能,我做不到。有人说,钟立风你再写一首《再见了最爱的人》,你就火了。我说不行,我现在已经写不出来了,因为每个阶段的表达都是不可复制的,我再怎么闭门造车也造不出来,我现在一出来就是那种欧洲气息、世界性的,但从某个方面来说又完全是个人那种表达。就像我喜欢的那些欧洲歌手、艺术家,尽管他们的作品已经载入史册,而且拥趸也源源不断,但在整个流行界是根本排不进来的,因为这样的气质品味永远不可能是主流大众,太高贵了,没办法,尽管越高贵越朴素。人是会有创作洁癖的,创作越多会越有洁癖。那种没有难度的东西,或者讨好大众的东西,你最后是不愿意去写的。当然这也是一个人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
仲伟志搜神记:没有想过上选秀节目?
钟立风:完全没有。
仲伟志搜神记:你团队里都有什么人?
钟立风:我和我的爱人,就我们俩啊,哈哈。
仲伟志搜神记:你这么说,你的乐队会不高兴吧?
钟立风:乐队他们知道我。乐队快十多年了,也没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跟机会。他们除了跟我合作,在别的乐队也有合作,贝斯手宋扬,还给国内外很多乐器品牌做代言;吉他手王闯在孟京辉的蜂巢剧场工作,是蜂巢的音乐制作人,经常会在国内外参加戏剧节什么的。如果只在我这边,机会就少很多啦。反正他们也懂我,就像我的制作人柳森,他平常给一些火爆的选秀出来的歌手弹键盘,但他特别希望跟着我和乐队一起巡演,我说,你的费用太高了,我请不起啊。他说,跟你演出,不谈钱,多少都可以。我很感谢这样的音乐朋友,因为他完全理解我的创作,他完全能够进入到我的创作里,他们觉得在我的音乐里,是艺术的享受。但是也得生活啊……
其实你们没有看到我现场表演,虽然看我一本书一本书地出,但我一旦上台表达,就是完全投入,也很有看点。我知道在哪个地方埋下什么伏笔,就像写作似的,有个句子,突然出现了。在录音里是没有这样的表达的,但是在每一个现场,我都会出其不意出现一个东西,就好像一次离调,或者文学里面那个溢出的部分。
仲伟志搜神记:你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巡演?音乐节?——与其他乐手不同的是,你有很多文学同道,你可以参加一些诗歌节的演出。
钟立风:这些年来,也许自己还算比较勤快吧,录音、出专辑,写作、出书基本没有停止下来,所以收入似乎还比较稳定,有演出费也有一些版税。不过这些年年轻歌手层出不穷,各大音乐节好像也都是他们在演出。还有我并没有很多物质欲望,我需要花费的地方,只是买书、买碟,兴之所至出门旅游一圈,拜访拜访有趣的朋友,花费不多。
说到诗歌、文学活动,对的,近些年每年总有不少相关活动,诗人、作家朋友们总会邀请我参加,我也乐于加入,与诗人、作家朋友们在一起,很快乐,他们一个比一个有趣。
仲伟志搜神记:你们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钟立风:精神上是。然后他们就说只有你们歌手有钱,我们诗人都没钱拿的。我真是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真的很佩服诗人,真正的诗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开启天地宇宙的一把钥匙,通过那几行诗,你内心憧憬的那个世界一下子就打开了。能做诗人太幸运了。但这也是他们的天赋和长期训练的结果,难能可贵的。
仲伟志搜神记:我们觉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民谣是在向诗歌学习,而中国诗歌现在越来越失去它的音乐性,正慢慢变成一个纯粹语言的艺术。我们倒是觉得它应该向民谣学习很多东西,当然是更多是从经验上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学习。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诗歌与民谣的自由转换。你可以说是歌手中的诗人、诗人中的歌手了吧?
钟立风:的确是国内外好诗也读了不少,但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做出一些评论。我觉得能欣赏到好诗已是莫大的幸福,更幸福的是,身边还有那么多优秀的诗人朋友,他们的作品我觉得都是世界级的,与他们一接触,就能吸收到无穷的养分。像诗人宋琳、蓝蓝、耿占春、唐晓渡他们,总说我就是诗人,是游吟诗人,我说不敢不敢,我觉得真正的诗人是时代的先知,是天地间的沟通者。我真的不好意思,我觉得自己真的没达到那种能量。
仲伟志搜神记:我感觉,生活在音乐中相对幸福吧。
钟立风:从音乐中走出来也会有幸福感。走出来,走出来,不要总是待在某个地方!我总是这样的。
仲伟志搜神记:诗人、作家,可能远远不如音乐人这样具有内在的幸福感。比如做一个真正的诗人,代价是很大的,第一他需要另外的工作养活自己,第二他需要不停地拷问自己的灵魂。相对来说,音乐还是可以帮助你内心更平静一些。
钟立风:伟志兄,你忘了吗,采访之前我们谈及的几位歌手,他们的内心也不是很平静啊。我的心情,也时常起伏不定、不太安宁。所以,我觉得内在的幸福感,无论是哪一行的人群,都各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体验吧。或者说,即使一个普通人,也会拷问自己的灵魂,而作家、诗人,也有可能他们会让自己过得轻松,仅仅去体验词语、节奏的快感,因为他们看得更透啊。
仲伟志搜神记:现在怎么定义你呢?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民谣歌手吗?对你而言,这个标签是不是显得门槛太低了?
钟立风:民谣这个词怎么说啊,如今也真是用烂了……我们说点真的民谣,比如像野孩子、苏阳这种,是从民歌发展起来的,他们或许更加进入普通听众的内心。苏阳的音色一出来,是那种生命在炙热的黄土地上爆发的感觉。而我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接近欧洲的传统,不过你发现没有,一些蒙古的调子或者新疆的旋律,甚至和希腊的、俄罗斯的音乐很接近,也跟西班牙、葡萄牙的音乐有某种关联,这里面的内涵,是时间的魅力,也有人文的养分的滋养,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我突然发现我的很多歌曲,如《盲人和一位女子去渡海》、《欲爱歌》、《你好,旅人》、《读诗远足》、《镜中》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它的源头是斯拉夫,是中世纪,和那些我喜欢的法国、俄罗斯歌手有着同一个来源,调性自由,和弦丰富,大小调来回转换,但具有诗性的流畅。
比如朱丽叶特·格雷柯,一位女性,九十岁了,还在歌唱,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萨特就毫不吝惜地赞美道:她的嗓音里包含了一百万首诗。萨冈、加缪全是听她的歌,她也唱他们写出来的诗歌。还有一位叫芭芭拉的创作歌手,她的节奏调性,完全也是人性的流露,就连歌唱间隙的一声微弱的叹息,就能把人带到一个迷人的境地。她的旋律,仿佛已是血液般的流淌在法国人心里,据说只要她的歌声从某个咖啡馆一响起,就连一两岁的小孩,都会突然——像寻找母亲乳房那样——找寻歌声的出处!
包括写《枯叶》的雅克·普雷维尔,他的诗歌也被很多具有文学性的歌手唱出来。我觉得他们这些也能称之为民谣。他们唱的是人性的通透、爱欲的婉转,是人内心深处最幽暗的、但也是最美好的东西。那首《枯叶》是在二战期间写的,歌词其实很简单,但朴素高贵,当它被唱出来,那种深邃的力量是无以言表的,而不是说像一首普通的民谣反映一个社会现象、表达一种情感那么简单,那个旋律一出来,你就会不由得将生命融入进整个历史长河中,觉得一切不堪都无所谓,让你觉得不孤独,因为还有那么多跟你接近的、相同的心灵和灵魂,在拥抱着你。
仲伟志搜神记:是一种安慰。
钟立风:对,我心里的民谣是那样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以称为一个民谣歌手。就是说,我这个民谣歌手跟当下中国所说的民谣是不太一样的,我对应的是欧洲,是世界,所以我在中国并不被特别多人喜欢。
仲伟志搜神记:不对啊,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你很受文学女青年的喜爱啊。
钟立风:哈哈,那当然也不是说特别多吧,文学女青年能有多少。不过最近我看到一些音乐网站的后台数据,之前我并没有注意到,我发现自己这些作品,光是一个网站每天就有将近十万的试听量,我想啊,要是聆听者多多少少给点费用,对于创作者会是个良性的循环呀!这说明我们这样的歌手,虽然称之为小众,但也无妨,有一批坚定的欣赏者也就够了,要那么多干嘛呢?任何东西,一旦多了,难免就俗气了,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我记得有年轻的歌迷给我留言说,你给于坚谱写的那首《读诗远足》,听第一遍时被吓到了……..我知道她说的这个“吓”,没有一点儿夸张,因为在她的聆听经验里,我这样的表达实在是非常意外的,大众嘛,总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她能够静下心来,第二遍、第三遍地进入,这样一来,她就被深深地迷住了,发现了其中的韵味,和诱人的密码。但如果第一次听完之后被吓走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觉得,但凡好的艺术,总是有些挑战性的吧。就像一本好书,重读是多么有必要有意思啊。
仲伟志搜神记:你觉得现在是你最满意的生活吗?游荡、写诗、唱歌,还有奇遇……
钟立风:满意或者不满意,日子都得继续过啊,对吗?我想,只要在日常生活中,能捕获一点点好玩的东西,就会令我满意。或者游荡、写诗、唱歌等等这些事本身,都是奇遇吧,就像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话,也是奇遇。
仲伟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