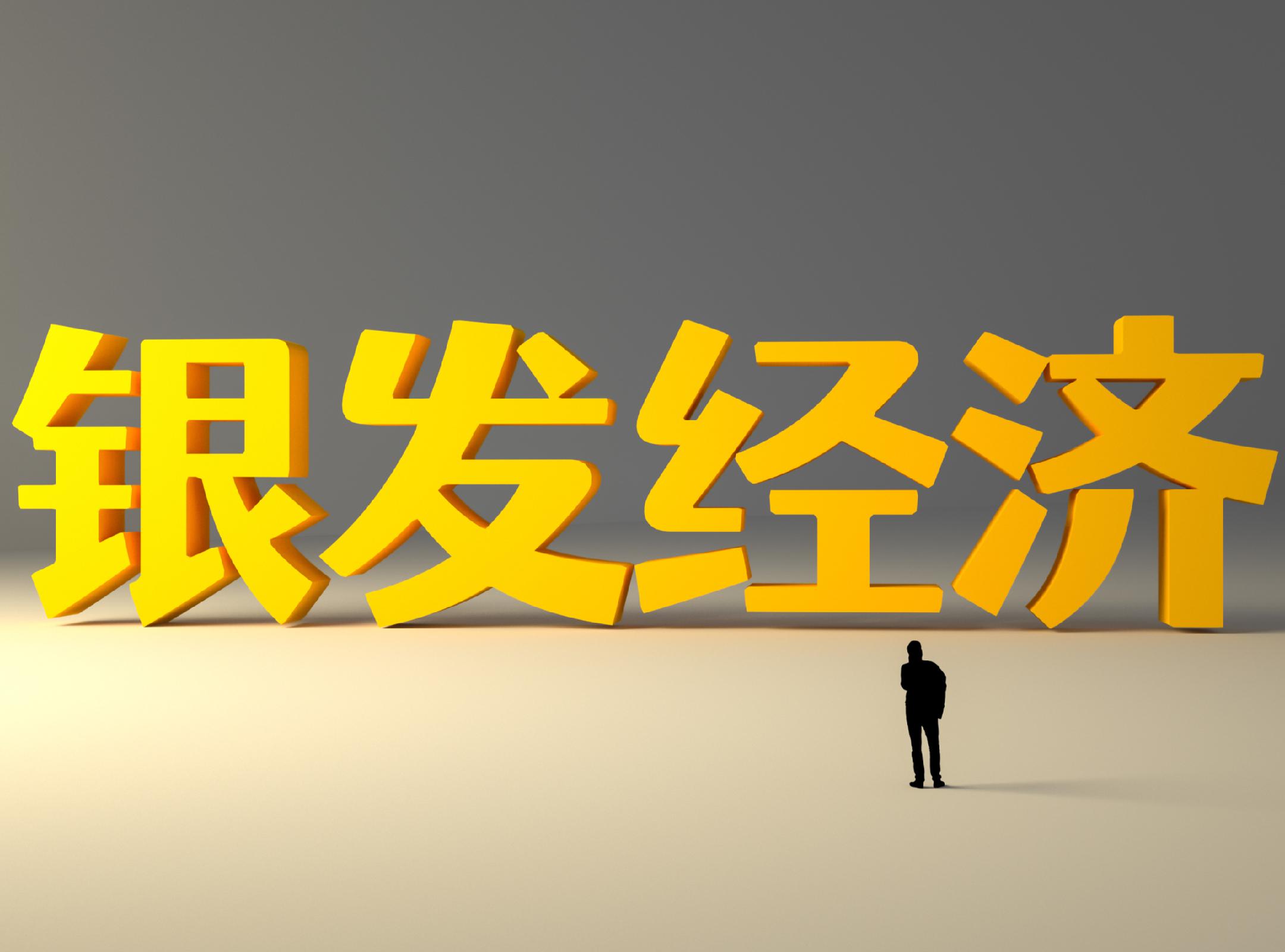王小广/文
就业是经济发展与老百姓生活之本,也是宏观治理之要。稳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解决就业问题过程中,应对结构性失业矛盾最应重视。因为解决不好,会导致较长期的严重宏观经济失衡;而解决得好,就能全面提高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的效率,形成巨大的新动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或高质量发展。两种结果,正是风险与机遇之别。
一、警惕结构性失业风险
失业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周期性的(指短期的基钦周期)失业,另一类是结构性的失业。
周期性失业也称总量性的,是经济运行短期周期波动过程中因经济景气波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而导致的失业问题,通常包括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等。如企业在经济上升期,为了增加产量而扩张,增加劳动力需求,而在经济收缩期则减量或转产,从而降低劳动力需求,导致失业率上升或下降。
那么,什么是结构性失业?关于结构性失业,美国经济学家萨尔.D.霍夫曼在《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绝大多数由于劳动力市场调整过程引致的失业均属于摩擦性失业,然而一旦衰落部门的失业者与扩展部门的工作彼此不相吻合时,结构性失业便产生了。最令人关注的例子是技能失调,现有职位上需求的技能正是失业工人所缺乏的……结构性失业也可能因现有工作与失业工人地理位置上的失衡而存在。”即结构性失业不是短期问题,而且相对长期的问题,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或就业空间结构的失衡所带来的长期性失业问题。
结构性失业一般分成两类,一类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结构矛盾引起的,如美国上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婴儿潮”,它是人口与劳动力供给异常变动的典型。
近几年,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生扩招的累积效应;另一类则是经济结构剧烈调整而带来的就业在时空上的结构失衡。像美国“铁锈地区”的人口流失、失业率上升,我国国有企业布局调整、老工业基地转型以及我国处于结构大转型期所产生的较长时间的就业供需不匹配问题,而引起的特别区域、特定行业失业率明显上升等,均属于这一类。
二、“两个超千万”的就业压力
当前我国结构性失业风险,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就业面临“两个超千万”压力。青年失业率高企问题已经受到关注。
近5年来,我国大学生失业问题,既与疫情反复爆发所产生的短期冲击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扩招及产业高级化发展而引起的结构性问题。
数据显示,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从前几年10%左右猛升至2020-2021年的14-16%。今年由于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加和疫情反复冲击产生的累积效应,4月份以来青年失业率攀升至18%以上,6月份经济出现全面恢复,但6月份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达到达19.3%。
我国结构性失业矛盾,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高学历人力资本的不充分利用,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总体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所以,当前稳就业、保就业要高度重视“两个超千万”的压力:
第一个“超千万”的压力,就是今年我国应届大学毕业生总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1076万人,比上年新增167万人。因大幅扩招导致应届大学毕业生显著增加的起始年是2003年,当年大学毕业生总数为199万人,到2006年则突破400万人,2018年又突破800万人,短短15年间翻了两番。2019年至今又增加了31.2%。过去两年多时间前所未有的疫情持续冲击,使大学生就业压力“雪上加霜”。
第二个“超千万”的压力,则是预估自2003年以来我国高学历人才累计失业总数已突破1000万人。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为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增量,而且还要考虑多年累计的存量。
三、如何将结构性失业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青年强,国家强,青年有信心,国家繁荣就会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1)美国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经验教训。
美国“婴儿潮”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青年失业率严重偏高的根源,是导致当时美国长期“滞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它既是导致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繁荣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70年代经济“滞胀”的重要内生原因。针对当时的外部强冲击(石油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出现了两个严重错误:
一是在稳就业和稳通胀的目标上不断摇摆,宏观经济政策过度重视短期,而严重忽视长期,对价格和企业活动实行越来越多的管制,把大量的财政、货币资源用于短期的稳定增长与防通胀上。
二是把“婴儿潮”引起的青年高失业率问题和黑人群体的高失业率当成周期性失业处理,利用传统的凯恩斯政策试图解决结构性失业难题,结果背道而驰。里根经济学或供应学派政策则通过放松管制、铁腕治理通胀、增加长期高科技投资、鼓励发展风险资本市场等,通过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创造了大量的高质量且适应青年人的就业机会,一举解决的十多年难解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最终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高科技驱动的新的繁荣周期。
(2)应对结构性失业须从全面深入有效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入手。
“滞胀”是由特殊因素综合引起的,严重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必然带来“滞胀”。现在市场上流行大量“滞胀论”是不了解这一背景,可以认为是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我国经济形势的一种“误解”。
当前,除我国以外的全球高通胀,主要是纯外部冲击型,很难持久,因为没有有效需求作支撑,更大的风险是经济衰退和长期的通货紧缩压力(此结论将在之后的系列谈中另题讨论)。而就我国来讲,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虽不会发生“滞胀”,但是由于长期的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最终可能会步入“低迷增长期”。
实际上,结构性失业问题与创新不足是高度关联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供给高质量问题,解决结构性失业必须从全面深入、有效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入手。
结构性失业问题一旦有效解决,既可显著增加有效、高质量供给(人力资本充分利用),又能有效地解决需求问题(高端就业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导致中等收入家庭比例提高和收入较快增长)。
(3)解决我国结构性失业矛盾的对策思考。
解决我国持续较长的经济下行压力,必须从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入手。既要发挥货币财政政策在短期稳增长、稳就业的重要作用,更要发挥综合结构性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对培育供给新动能和需求新动能的重要作用,大量的新增人力资本谋求的更大用武之地主要存在于这些供需双方的新动能上。简单的货币财政扩张政策和增加一般的投资举措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难题。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从根本上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最根本的举措是将经济政策的重点实质性由“短期”转向“长期”,重塑供给结构与需求增长机制,使我国人力资本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得到充分体现。
一是按照“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要求,全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通过产业升级、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加强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等,全面增加高端就业岗位。大学生失业率大幅降低及充分就业之时,就是我国高质量发展全面实现之时。鉴于此,可考虑在今后的官员政绩考核中增加创造高端就业岗位这一指标。
二是坚定控制房地产泡沫、促进房地产软着陆,从根本上使许多地方经济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以盘活住房存量为主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减轻青年人生活压力,提高青年人对国家经济趋势和人生发展的乐观预期。
三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要把鼓励“零工经济”等就业新业态发展作为缓解大学生失业问题的主要举措。对当前广泛使用的“灵活就业”概念,必须进行严格分类和有效统计,以避免把“灵活就业”看成是一个低效率就业,从而使人们错以为灵活就业规模越大,就业形势便越严峻,且质量越低。至少要分出趋势性灵活就业和非趋势性灵活就业,非趋势性灵活就业是指该类就业带有明显临时性,或叫应急型就业。而趋势性灵活就业,则是就业的新形式,不仅显示就业时间、空间的灵活性,也体现经济发展新趋势和高效率,这里最典型的就是零工经济方式,它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在就业上的一种新创造。建议将零工经济这种代表灵活就业的新趋势纳入就业统计大类,并建议国家和各地区要把零工经济就业新模式作为扩展大学生就业渠道的主攻方向,及早出台促进与规范政策,有力保护零工经济就业者的各项权益,并成立专业机构,提供优质周到的配套服务。
四是将国家重要就业统计数据和第三方权威大数据的分析评估结果与大学专业招生增减、教学内容调整结合,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供需结构的适配性。如针对多年来程序员需求旺盛,在完善程序员等重要新就业统计的基础上,将结果作为需求导向,调整大学招生专业结构和课程设计,既要增加新就业对口专业的招生数,又要在文理科高校普遍地开设计算机程序设计、大数据应用等公共课程。
当前及今年一段时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要努力稳住就业大盘的同时,更加注重缓解高学历人才的“两个超千万问题”,化巨大的结构性失业压力为强大的高质量发展动能。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