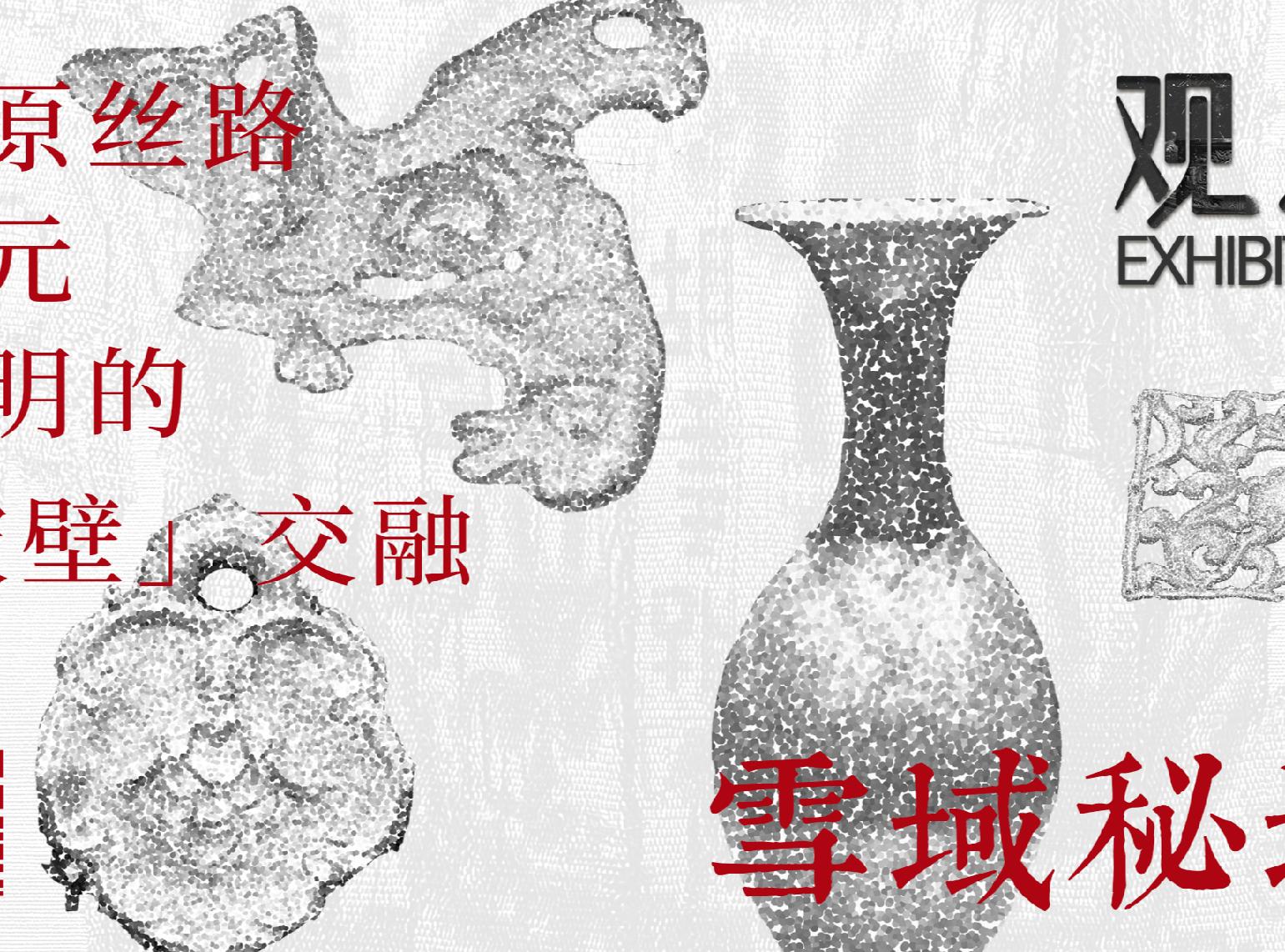(作家毕飞宇)
惜墨如金的人很多,但真正像毕飞宇这样“吝啬”文字的不多。比如已经成为短篇小说经典的《是谁在深夜说话》,仅仅四千多字,恍如南京的云锦,巧夺天工的织物。
用云锦比喻毕飞宇的小说还有点不恰当。小说领域的这十年,一个名字被人反复说起。这个人就是毕飞宇。也许毕飞宇来自水乡泽国,所以这十几年,毕飞宇的小说就像神奇的息壤一样,在如洪水一样的文字中,不但没有被湮没,反而在有意无意的湮没中越来越坚定,也越来越辉煌。
毕飞宇已成好小说的符号,也成为读者的焦点。
有人说读他的小说就像是在夏天里吃冰激凌。
这是阅读的感觉。但小说是份手艺活计,可以说是白上之黑。这白纸黑字的东西对每个人都是一种考验。谁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保证那白上之黑的生长?
这些年,只要和文友们在一起,作为毕飞宇小说的爱好者,我们总是要谈起毕飞宇:他和他的小说。因为他的独特,因为他的优秀,让人羡慕,也让我们说不清楚地佩服。总而言之,我们心甘情愿地被毕飞宇的小说“俘虏”了。一位北方作家对我说,他当年读《玉米》,仅仅读了一半,就把书一扔,感叹地说:“有了它,我们还写小说干什么?”
毕飞宇已成了年轻小说家的榜样。
榜样是用来学习的,也是用来赶超的。研究毕飞宇的小说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但结果是:在外国文学的岛屿中,找不到毕飞宇的落脚点。
这好像有点窥视欲的味道。其实,在当今文坛,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能不说,中国当代有许多好小说家,他们为我们贡献了许多好小说,但在这些好小说中,似乎都能在外国优秀小说家的岛屿上找到一些树,一些草,甚至有蛛丝马迹。也就是说,会找到可能的师承——这不足为奇,这就是影响,可以作为影响的焦虑,也可以作为影响的因果。每个人的走路都需要支点,能够找到支点并能够健步如飞的就成了优秀作家。
——就看你能不能把文学的胎衣埋得很深很深。
用另一句话来说,看你的消化能力,对汉语小说的传统,对可能的文学遗产,对当代的消化能力:每一个手艺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汉语之光。因为小说的湮灭是可怕的。作家惟一可做的就是完成自己。
毕飞宇的生长轨迹似乎和中国其他优秀作家一样。先是先锋,然后再蜕变,再找到自己的那个地方。
但毕飞宇在先锋里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短得几乎没有痕迹。就像一个在操场上写字的人,写着写着,他就写过了围墙,写到田野里去了。
有人说,中篇小说《叙事》是毕飞宇的先锋。我觉得,那是先锋的另一种可能,也是毕飞宇小说中最值得重新研究的小说。这《叙事》中,可以找到后来的《是谁在深夜说话》《青衣》,也可以找到后来的《玉米》,更可以找到后来的《地球上的王家庄》,找到后来的《平原》《推拿》。
但毕飞宇不是自我重复的人,他与生俱来的“息壤”品质,就决定了他是“自己长自己”的小说家。
现在看来,《叙事》其实也不属于先锋,也不是集大成,它是一个转折点。在《叙事》里,毕飞宇展示了烹饪文字的另一种技艺。年轻的《叙事》是毕飞宇自己也无法逾越的一种可能。也许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毕飞宇就开创了另一种可能,也就是另一种现实。
“息壤”的成长是需要力量的。毕飞宇有他的哲学准备,这哲学准备是许多作家无法准备的。毕飞宇有强大的消化能力。他的那种想象中国的方法属于最沧桑也最忧郁的汉语。毕飞宇回到中国的大地上,他的撤退令许多朋友不快。有人说他从先锋中撤退得太早了,也就是说他老了。
他承认自己老了。
毕飞宇的回答没有掩饰。一旦没有掩饰,那毕飞宇的内心就无比强大。他有他的自信,使得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小说等待他的位置。
强大的还有他的文字。每一个优秀的画家都解剖过人体,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解剖过优秀小说。他像一个技艺精湛的画家。小说的一切他都爱惜,并且成了习惯。他把所有的能量全部集中到小说中了。比如他每天的举重锻炼(献给小说以最好的体力),比如他的专注(献给小说以最好的技艺),比如他的简单生活(献给小说以最好的精力),息壤的生长永不停息。直到他长成了毕飞宇的一切。
从《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写字》《怀念妹妹小青》《白夜》《蛐蛐蛐蛐》,中篇小说《青衣》再到《玉米》《玉秀》《玉秧》。就拿《玉米》来说,文字的松弛有度,简直成为众人叙说的风景。
简直就是小说给我们的大惊喜。
找不到外国文学的师承,后来有人就说那毕飞宇的小说里面有《红楼梦》,有张爱玲,有白先勇,有王安忆,但都不是,毕飞宇只是毕飞宇,恰如北斗不是启明。
每个文学家的因果都是有特定的。一步一步地走向枝头,那延续的果实不是你选择了它,而是万有引力把果实打到了你的头上。
毕飞宇修成了中国汉语小说的正果。
有人说他是幸运的,其实不是。从先锋中撤退下来的毕飞宇就站在一棵很“中国”的树下,也许是土生土长的“七十年代”的树,也许是在九十年代锈迹斑斑的“八十年代”的树,或者这棵树,就长在王家庄,苦楝,抑或榆树,他在“树”下站了很长很长时间。
那是在夜晚,在白天之外的黑夜。毕飞宇总是在深夜里写作。总是在深夜里“走神”。在夜晚再看白天的喧嚣。在夜晚再看白天的灰烬。他在闲庭信步,其实胸中有千军万马。小说的节奏、走向、长短。叙述的干涩、厚薄和冷暖。还有小说的肌理,毕飞宇处理得那么的细致和饱满。这样的工笔的辛苦是怎样才能达到呢?
所以,每一个黑夜里的毕飞宇走在白纸上,那实际上是在保持和现实的距离。也是和作家的距离。也是对南京以及当下的走神。这种距离使得他有了一种超越。那是对现实机警的超越。
所以毕飞宇的小说最不像谁的小说。
但是汉语文学的正果。汉语小说的长廊上,那么多的神奇,还有那么多的人物。那是怎么样的梦啊?又是怎么样的现实。
写《玉米》的那几个月,毕飞宇简直丢掉了一切。他写得那么累,又是那么的快乐。《玉米》的每一个人物都在纸上走动。王家庄啊。有福的王家庄。王家庄是什么?王是中国最大的姓,整个中国都是王家庄。
说到底,还是毕飞宇摆脱了自己的焦虑,他愿意被一个人物苦苦地纠缠。那么多的人物就在纠缠中活了过来。他从最中国化的叙说中让汉语小说达到了宽广、丰满和健康。
比如《青衣》中的筱燕秋,那哪里只是青衣,根本就是经历过黄金八十年代的我们。她是八十年代纯情诗人在物质主义时代中必然的遭遇。不甘的人,不甘的心。读完之后,从未有过那巨大的艺术力量撞击我们。青衣就是我们自己。溃不成军的理想啊,还有疯狂,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你想不想再找回来呢?
臣服,已经好久没有了。
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但我们总是想把自己的生活在创作中给漏掉,或者过滤掉。但毕飞宇不。画家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画的含义。”放到毕飞宇的小说里,同样适用。他对人生的百态充满了兴趣、关注和信心。他对“人”充满了关注。
其实毕飞宇就是以小说为宗教的人。
好小说就是珍惜的回报。
好的小说都是有体温的,体温下面是有血的,这血都是优秀作家在你身上血的再版。鲁迅贡献了《阿Q正传》,阿Q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那《青衣》中的筱燕秋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另一个名字,或者是月亮下的影子,你否定不了的,骨子里的那份固执,也是我们的命根子。
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雄心,毕飞宇肯定也是有雄心的。比如《平原》,那里面的爱与恨,扭曲与灼热,有人不愿意正视,平原其实就在当下,也在王家庄的风中水中土中。端方就是我们的同事,领导和儿女。
还有玉米呢?
玉米是王熙凤吗?玉米是尹雪艳吗?是曹七巧吗?是延安时期独自结扎的江青吗?可能都是,又可能都不是。
玉米就是我们的食指。指到哪里,哪里都是疼痛的食指。还有施桂芳,我们疲惫的大拇指。王连方,我们不堪的中指。玉秀,我们的小拇指。还有玉秧,自生自灭的无名指。一家子,伸开来,是一个命运线交叉的巴掌,缩起来,是一个骨头与骨头较量的拳头。
——它砸在我们沉睡已久的额头上。
还有语言,毕飞宇的语言与莫言的语言、苏童的语言、王朔的语言,都成了汉语小说的贡献。
当然还有细节。比如《玉秀》中一个极平常的细节,当玉米跪到为郭主任开船的郭师傅面前要求郭师傅也为他保密时,郭师傅也跟着跪下了,并对玉米说了一句:“郭师娘,我以党性做保证。”此时的郭师傅就必须要姓郭,而且必须要入党。还有《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的地图。还有《玉米》中的嗑瓜子。《白夜》中那只苏格拉底的猫。《是谁在深夜里说话》中的明城砖。随便说出哪一部小说,里面的细节都是信服的精心,随意的真诚……经典的,也是最恰当的。在《相爱的日子》里,我们爱得那么热闹,却是那么的荒凉。那里面的宇宙感超过了《地球上的王家庄》。荒芜的不是那对爱的人,而是象征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越是热闹,越是荒凉。那是一片荒原。和艾略特诗歌中一样的荒原。预言一样的来到了。我们就在荒凉的拥抱中取暖。
还有我特别喜爱的《家事》,这是一篇 2007 年度非常出色的小说,通过我们生活的子宫生下的儿女们,我们就在他们的身边,但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找不到我们,反而满世界盲目地寻找。表面上,只是写了中国人的伦常的消解。但不仅仅如此,它的价值其实不亚于当年的《班主任》。
因为那里面真的洋溢了汪政先生所说的“短篇精神”。
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个根深叶茂的老毕:毕加索,两个老毕是何其的相似,都是会生长的人,都是根深叶茂的。
所以,有了毕飞宇,那白上之黑就有了深不可测的无限和未来。
( 庞余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泰州市作协主席,靖江市政协副主席 )

左一为毕飞宇,左二为庞余亮

左起:叶兆言、余华、庞余亮、毕飞宇
小说选读
是谁在深夜说话
作者:毕飞宇
关于时间的研究最近有了眉目,我发现,时间在大部分情况下只呈现两种局面:一,白昼;二,黑夜。时间大致上没有超出这两种范畴。但是,人类的生存习惯破坏了时间的恒常价值,白昼的主动意义越来越显著了,黑夜只是作为陪衬与补充而存在。其实我们错了。我想把上帝的话再重复一遍:你们错了,黑夜才是世界的真性状态。
基于上述错误,我们在白天工作,夜间休息。但是,优秀的人不,也可以这么说:接近上帝的人不采取这种活法。例子信手拈来,我们的哲学家,我们的妓女,他们就只在夜间劳作。白天里他们马马虎虎,整天眯着一双瞌睡眼。他们处置白昼就像我们对待低面值破纸币,花出去多少就觉得赚回来多少。
我也是夜里不睡的那种人。我的生命大部分行进在夜间。熬夜消耗了我的许多大好时光,反过来说也一样,熬夜构成了我的许多大好时光。但我必须把话挑明了说,我熬夜并不能说明我也是优秀的那种人,不是的。我只是有病,失眠。你千万別以为我能和哲学家、妓女平起平坐了,这点自知我还有。在夜间我偶尔跟在哲学家或妓女身后,狐假虎威,或虎假狐威,都一样。
我住在南京城的旧城墙下面,失眠之夜我就在墙根下游荡。这里是哲学家与妓女常出没的地方。城墙下有许多树,树与树不一样,但每棵树有每棵树自己的哲学家,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决定了那么多的树在根子上是相通的。
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南京的城墙始于明代。我在一本书上发现,那时候城墙下徘徊的可不是哲学家与妓女,而是月光与狐狸。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鬼气森然。但鬼气森然不是大明帝国的风格。大明帝国的南京纸醉灯迷,遍地金粉,秦淮河边云集了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最杰出的妓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对明代的妓女如数家珍,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扳一扳指头就是秦淮八艳。南京城今天的泱泱帝气得力于明代,得力于秦淮河边彩袖弄雨的惊艳一绝。
那一天夜里有很好的月亮,由于月亮的暗示,我把自己想像成狐狸。我点了根烟,以动物的心态贴墙而行。我发现夜很好,真的好极了。月亮照在城墙上,城墙很破,坍塌了许多块,但破得不失大气,有脸有面,月光一照,像一张高清晰度的黑白相片。我行走在夜里,我知道黑夜是没有朝代的,所以我可以在明代散步。只走了两步我就想哭泣,我怀念明代,明代的南京城感人至深。当然,南京现在比那时强多了,人人会说普通话(即官话),家里的卫生间贴上了瓷砖,去年的十月一日还放了礼花。但作为一个夜间失眠的人,一个梦游者,我的梦始发于明代。至少,在每天的黄昏过后,月亮总是从四百年前升起,笼罩了一圈极大的古典光晕。
我和邻居的关系不好。我是说不好,也不一定就是说坏。我们处在一种“物我两忘”的情境中。当然,对小云我不能够。小云是我们楼上最著名的美人,从长相上说,她的眼角和走路的样子都接近于狐狸。她的笑容相当迷人,往往只笑到一半,就收住了,另一半存放在目光的角度里头。许多夜里我看见她行走在墙根边沿,她走到哪里哪里的月亮就流光溢彩,哪里的天空就会有一朵雨做的云。事实上,她的行踪和狐狸十分相似,走得好好的,然后在某一棵大树下面滞留片刻,裙子的下摆一闪,她就没了。我欣赏她身上的诡异风格。我曾经非常认真地准备向她求婚,我已经打听到她是秦淮烟雨小学的音乐老师,甚至连她擅长吹箫我也打听得清清楚楚。那几天我整天想像小云抚管弄箫的模样,越想越陷入痴迷。她吹箫时的脖子应该倾得很长,下唇摁在箫管的顶部,十只指头参差婀娜,像白蜡烛,浸淫在半透明的光中。我必须坦白,我的想像夹杂了相当的色情内容,但这怨不得我,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至今都没有挨过女人。你们都是饱汉,哪知饿汉饥;再说,我整天读那些旧书,哪一本不闹人?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刘大妈。这名字一听就是居委会的主任。刘大妈听完我的话推了我一把,笑着说:“书呆子,人家嫁给你?人家可是鸡窝里的金凤凰!”好多人听到了刘大妈的这句话,他们笑得很厉害。他们一边笑一边侧过头去往小云家的门口看,小云正在那里洗头,旁边晒着她的紫裙子。她的动作又懒又散和她的眼神一样有一股仿古气息,像秦淮河里四百年前的倒影。我伤心地望着小云,伤心地眯起了双眼。我一眯眼小云和她的紫色裙子离我竟远了,成了我和刘大妈讨论婚姻大事的旧背景。我失神了,无端端地想起了一本书上的话:不是历史滋养了现在,而是现在照亮了历史。这话说得多好,小云活生生地在那里洗头,她的长发足以概括整个明代,足以说明任何问题。
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建筑队终于驻扎在城墙边了。有七支建筑队参加了南京市旧城墙的修理招标,兴化市第二建筑队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为了不影响市内交通,他们的修理工程选择在每天夜晚,正像牌子上标明的那样:晚上八时至凌晨四时。这是一个好的决定。修理城墙这样的事应当“历史地”放在深夜。这再一次证实了我的研究成果。细心的读者还记得我在小说的开头所讲的话。历史大部分是在白天完成的,而修补历史是另一码事,只能在深夜。
一盏两千瓦的太阳灯悬挂在城墙垛口。城墙因此而惊心动魄,城墙上的野草、伤痕、子弹坑因此而纤毫毕现。我就此改变了夜间散步的习惯,拿了一张小凳,通宵坐在搅拌机的旁边。建筑队的队长后来发现了我,他特地从城墙的断裂处爬下来,向我汇报了工程的总体构思。我接过他的烟,不说话,直到最后我才点了点头,对他说:“可以。”他的话说得很多,槪括起来说,他决定把城墙修复到比明代“还完整”。他把这话重复了一遍,我看了他一眼,告诉他“可以”。我顺便问了一句,明代的城墙到底什么样?他把手头的过滤嘴扔到搅拌机的水泥桨里去,大声说:“修出来看,修起来是什么样明代就是什么样。”我拍了拍他的肩,这家伙不错,是个哲学家的料。我早就说过,我们的哲学家只在深夜工作。
但小云到底出事了,她给“抓住了”。这三个字时常跟随在美人身后,世俗生活因此险象环生又饶有情致。具体的细节我不清楚。事情也不复杂:一位电工沿着墙根检査电路,他看到了小云的丑态种种。照道理说小云应当能够听到动静的,可她在那种时候就是忘乎所以。手电筒一下子把她抓住了,一只狐狸在喇叭型光柱里头立马原形毕露。她的眼睛到了这个份上居然还闭着。男人这一点比女的强。男人做任何事都能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所以男人历来都能选择最佳时机撒腿狂奔。我在第二天一早专程到现场勘探过,那里有几棵大树,树冠比城墙的垛口还高,树与树之间堆放的全是旧城砖。我就不明白,这地方有什么好,能做什么?不过,后来我肯定了一点,这种地方绝对不只是月光和狐狸出没的地方,有一块砖头上还有出事当天的晚报。那块砖头被(屁股?)磨得都发亮了,字迹都没有了。旧城砖上可是有字的,这个我很清楚。由谁出资,哪个窑匠生产,提调官是什么人,全烧在砖头背脊上。这些字就是磨平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功绩就是这样给抹杀的。我听到出事的动静冲进了工棚,音乐老师惊魂未定,没有一点凤凰的样子,没有一点仿古气息。我的心情走了样,好在心智尚未大乱。我走到小云面前,扶她,她不动。我说:“跟我回家,孩子等你热牛奶呢。”我至今不能相信我能这样大智大勇,大智大勇对我来说仅仅是一次脱口而出。我挽起小云,从建筑工人们的身边款款而出。两千瓦太阳灯的炽白光芒照耀在深夜,它使一轮满月黯然失色。建筑队长揪过那位电工大声骂道:“说过多少次了,只管修墙,别管别的,我说过一百次了!”
英雄救美必然导致风流韵事,大部分书上都这样。英雄在一页纸的正面救出了美人,到了这页纸的背面总免不去一些苟且之事。小云来到我的房间,她不做任何铺垫,爽直地脱,赤条条地往床上爬。她望着天花板,说:“你救了我,来吧。”我回头望望一墙壁的书,想起了柳下惠。才过了几秒钟我就乱掉了。到了这种时候我才明白“乱”这个字的厉害。我上了床,因为是自己的床,所以轻车熟路,那种感觉是从城墙上往下跳的感觉,是旧城砖全部风化,以沙的姿态在风中流淌的那种感觉。我坚信我和小云做得很认真,很投入,称得上行云流水。她的嘴唇不停扯动,声音就像纸张慢慢撕裂。她就那样一页一页地撕。后来我对她说:“嫁给我吧,小云,你知道的,嫁给我吧。”后来小云一把推开了我,坐起来穿衣。“还干什么吧,你?”小云无精打釆地说,“你救了我你就了不起啦?”
拆迁通知来得很突然。我从拆迁的通告里知道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楼房底部的基础部分是用旧城砖砌成的。这是一个易于让人忽视的事实。拆迁通知说,旧城墙需要旧城砖,旧城砖属于国家,属于历史,理当回归国家,还给历史。
拆除楼房当然也是在夜间进行的。那一天没有月亮,建筑工程队在楼房的四个角落支起了四只两千瓦太阳灯,整个工地一片通明。明亮的程度甚至超越了白昼。明亮使灰尘越发抖乱。我站在城墙的顶部,亲眼俯视了脚下的纷乱场景,尘埃被照耀得漫天纷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华丽的颓败景象。我想起了古人关于现存生活的高度概括:尘世。我站在旧城墙的顶部,明白了尘世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俏皮一点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兴化市第二建筑工程队按期完成了城墙修复。看过新城墙的人都说,修得好,垛口齐齐整整,蜿蜿蜒蜒,凸凸凹凹,原先不就是这样的么?有几位赞助商在电视上对记者说;比过去的还要好,新修的部分千干净净,比下面的旧墙漂亮多了,颜色在那儿呢,真是泾渭分明。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我住进了新楼,是一个两居室的小套间。样样都好。我真正像一个大都市的现代人了。不好的只有一点,失眠之夜我的梦游不简捷了。我只好骑上自行车,花二十分钟到原先的地方游走。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的散步另有所图。我徘徊在小云被“抓住了”的地方,怀念单骑闯营、虎口救美的英雄一幕。那些砖头还在,撂在老地方,我成了旧城砖所做的梦,萦绕在它们四周。我夹着烟,坐在小云曾经坐过的砖头上。我突然想起来了,为了修城,我们的房子都拆了,现在城墙复好如初,砖头们排列得合榫合缝、逻辑严密,甚至比明代还要完整,砖头怎么反而多出来了?这个发现吓了我一大跳。从理论上说,历史恢复了原样怎么也不该有盈余的。历史的遗留盈余固然让历史的完整变得巍峨阔大,气象森严,但细一想总免不了可疑与可怕,仿佛手臂砍断过后又伸出了一只手,眼睛瞎了之后另外睁开来一双眼睛。我望着这些历史遗留的砖头,它们在月光下像一群狐狸,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