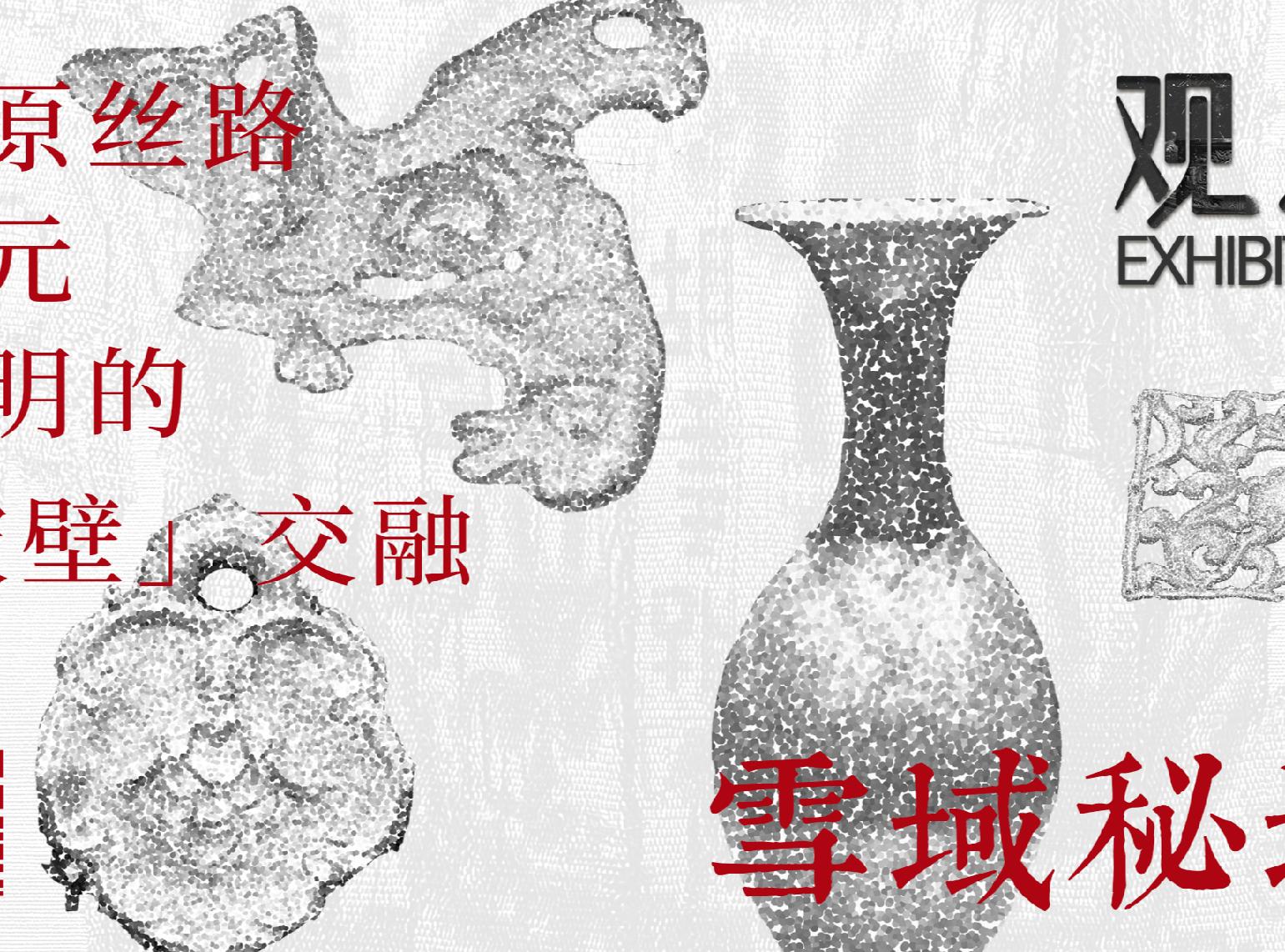每旅行到一地,满城找旧书店,这样的一种热情这些年也渐渐淡了,一来拒不凋零的旧书店越来越少,二来看得上眼又买得起的旧书也越来越少。如此也好,省心省力。
多年前每次来杭州,孤云、毛丫没少陪我们逛书店。今晚小河直街饭毕,他们带路,小街闲逛,走着走着又拐进了一家旧书店。看来看去,看上两本128开微型词典。不因其有用,只觉得好玩儿。夜书房里好玩儿的微型书也有不少了。前些天一位过路用户读了我的一篇公号文章,愤而留言说,“玩物丧志”。是是是,确是如此。种种所谓“志”,我只嫌“丧”得还不够快,不够彻底,我继续努力。好玩儿的小书并不好找,所以我宁可冒“丧志”的危险,也不能错过“痛失小书”的机缘。


其实我也喜欢超大开本的书。昨晚在杭州茑屋书店看见几种对开本画册,忍不住摸了摸封面,如结识新朋友,忍不住拍拍他们的肩。当然,最终也是擦肩而过。巨型书存放太费空间,翻阅太耗体力,抱一套回家的事,自搬回肖全对开本《我们这一代》之后,好多年不干了。
当然,正常开本的书我也不是不喜欢,只是这类书太多太常见,好书无数,不用特意搜罗你也避无可避,所以买起来虽容易满足,但不容易激动。更何况,普通开本的常见书,印装得好玩儿有趣乃至值得珍藏者,尤为难得一见。
买书买到不仅为求知、更为求乐趣的地步,就会明白实体书店不能消失的理由之一,即是你可以来这里“碰”乐趣。对,不仅是“求”,不是仅“寻”,还有“碰”。你根本没打算、没预算要在书店遇到某本书,然而无端邂逅了,不期而遇了,此之谓“碰”到乐趣。
碰到的乐趣都是意外的收获,此一种惊喜有人买了一辈子书也未必能碰上几回,何故?心中无“趣”也。只把书当读物,当工具,当升学晋职的阶梯、临时救急的佛脚,心里哪里还容得下功利之外的书情、实用之外的书趣?心中既无“趣”,走进书店,入眼皆有用无趣之书,“碰”到乐趣的机会难免就微乎其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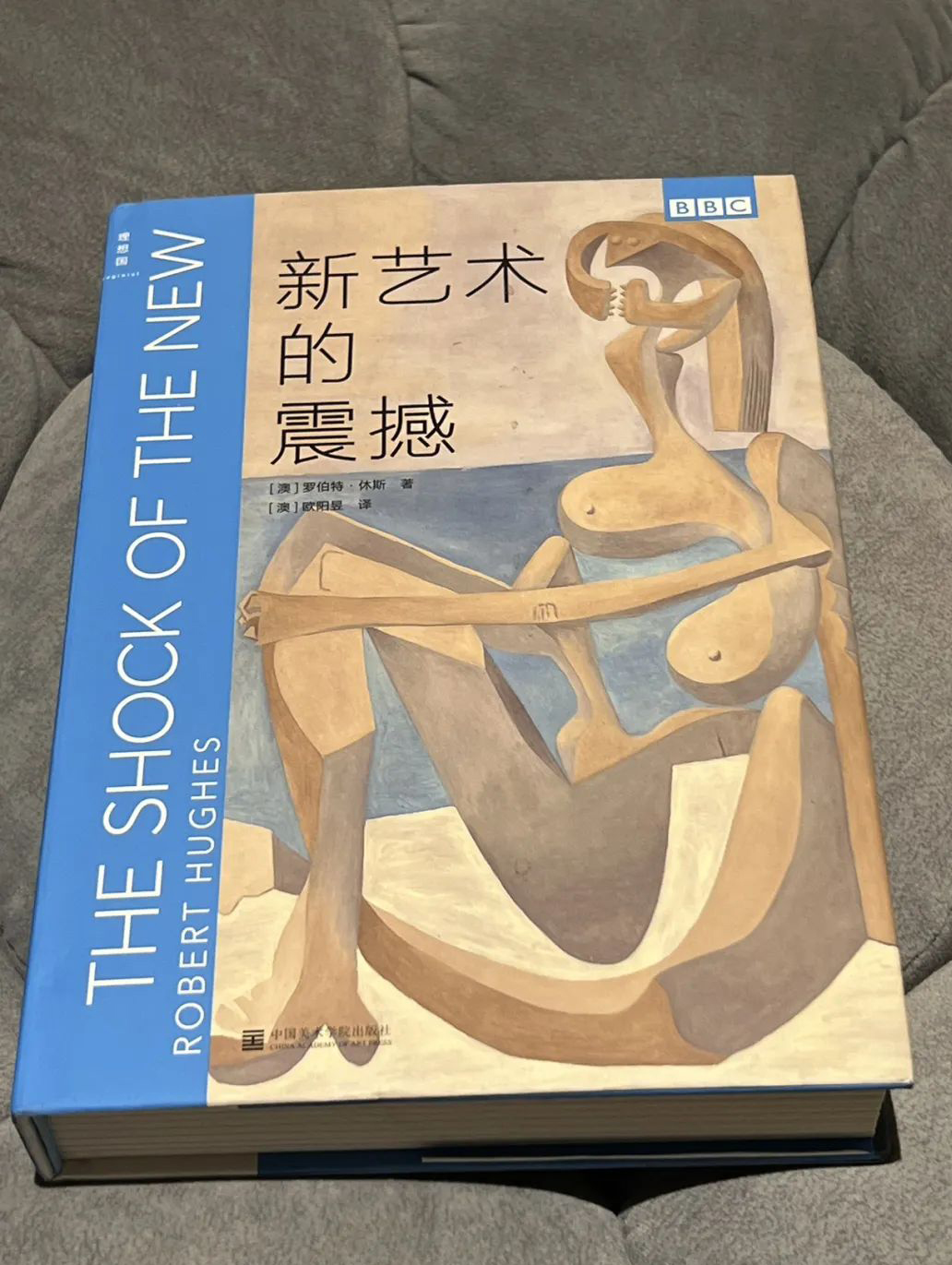
“碰”上的乐趣没有什么“公共性”,纯属“私家乐趣”,既不足为外人道,更难被外人理解,连偷窥都不可能。昨晚我在茑屋书店买罗伯特·休斯著《新艺术的震撼》,我对朋友说我不能白逛茑屋,需买一本留作念想,实则我心中另有乐趣:由这本新版,我想起了一种此书的旧译,书名是同一个,译者却另有其人,出版时间是1989年1月。我买此书读此书,是1990年我到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了。那时学的是新闻,我却在学校乱读了一阵艺术史,起因是衡水一位画家送了我一本贡布里希的《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后书名改为《艺术的故事》)。那位画家朋友或许到现在也不知道,他送我的这本书对我之后几十年的阅读影响有多深远:我竟然从此对贡布里希大感兴趣,然后由贡氏而波普尔,而范景中,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一些书。当年那本上海人美版《新艺术的震撼》也正是由此阅读兴趣衍生出来的小小乐趣,书页间夹藏着那个年代的风云与尘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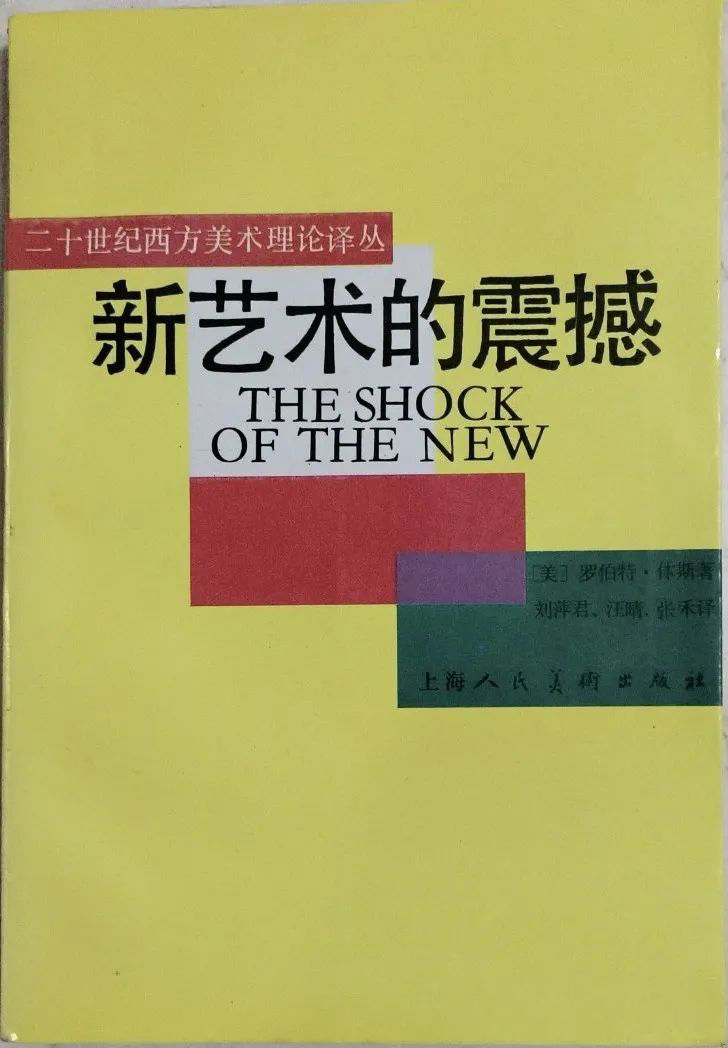
谁知这次书店偶遇新版《新艺术的震撼》,竟然是在杭州,书就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2019年1月的出版物了,我昨天才碰上。中间这五年去哪儿啦?如此想来想去,其中的乐趣像雪球一直滚个不停,别人又怎么能够知晓。“私家乐趣”,此之谓也。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