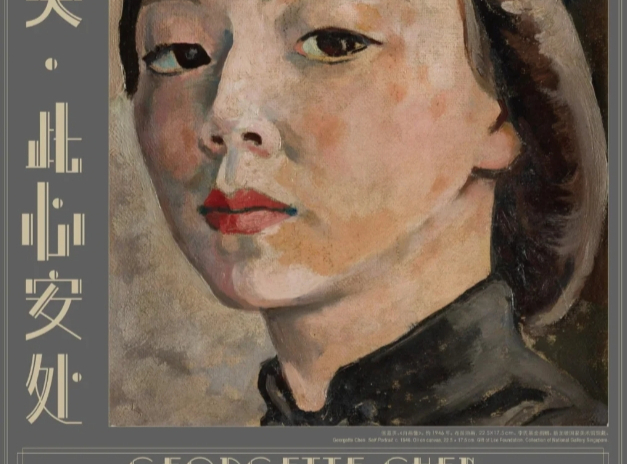张根庆/文
今年重阳节,年届鲐背、终身务农的老父亲收到了一件特别厚重的礼物:人生中梦寐以求的第五代砖混结构的二层楼房终于大厦落成。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家中排行老幺,与爷爷、奶奶、姑姑、大伯、二伯六人共同居住在一间祖传的、面积不到三十个平方的“乌银屋”(农村里厅堂与游廊交接处的那几间旮旯屋)中,别说晚上,白天进家门,连自已家里人也得站上好一会才能适应环境、明辨方位。
雄鸡一唱天下白。解放后,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住房紧张的奶奶与小儿子——父亲。娘俩终于“土改”到了一间二层木板结构的瓦房。父母结婚后,前几年尚可,六十年代,我们兄妹四人相继来到人间,记忆中的楼下前半间,西侧是一张八仙桌和两把靠椅、东侧是奶奶与我老大合睡的一张床铺、中间是上楼和后半间的通道;后半间的西侧是楼梯、楼梯下是烧饭的“锅灶下”和堆放猪草料的“花草池”、中间是灶台、东侧是猪栏和厕所;楼上前半间是父母和我们仨兄妹的二张床;后半间则用来堆柴草,居住窘境不言而喻。
七十年代,迫不得已的父亲向大队写了申请报告,开始动手建房,那时别说拖拉机、农村里连手推的独轮车也很少见,落脚用的石头是从横山水库下的溪滩中捡来的、垒墙的泥土是从挖通济桥八0线渠道的工地上挑来的;虽然材料不用花钱,但都是靠起早贪黑、肩挑手扛,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最令人担忧的是下雨,好不容易请泥水匠和亲朋好友的帮忙,辛辛苦苦垒起的泥墙、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水,又得推倒重来,特别是白天晴天、晚上下雨更让人防不胜防——叫苦连天。垒好了泥墙、购买房梁椽子又成为一个大难题,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木材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私自到山区卖买,被森工站发现:不仅要没收,还得罚款。
历经六年艰辛,二间二层泥瓦房终于完工,年过八旬的奶奶与我们一起住进了父母亲手建造的新房子。

八十年代,改革春风吹进丰安大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手头宽裕的家父看着子女们长大,又开始动手建造他的第四代房子——二间二层的沙灰墙平顶洋瓦房。落脚石、拉沙子、运石灰,只要舍得花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树大开桠、儿大分家。父母将二间一层在建的沙灰墙平顶洋瓦房分给了老大、二间二层的泥瓦房分给了老二和老三、把当年的“土改房”留给了自己,因为老二与老三先后在县城自购了房子,木板结构的“土改房”也因年久失修、缘于出入起居方便,父母依然生活在二间二层的泥瓦房中。
岁月流逝、时光轮回。五年前,木板结构的“土改房”被县里评定为“危房”,经村干部丈量、核对后,村里开来了推土机,父亲和左邻右舍的几位老人,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居住了近半辈子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心疼不已。并成为了他们的一块“心病”。
大孙女在杭州装璜了、二孙女在上海购房了、大孙子在宁波选房了!
近年来,随着“孙字辈”们学业有成,先后在杭州、上海等地安居乐业,每每听到这些喜讯,老父亲虽然脸上高兴,可心里总有种说不出口的滋味。
前年冬季,得知“原危房可原拆原建”的消息后,耄耋之年的父亲高兴得像个小孩,在第一时间告知我们仨兄弟的同时,逢人便夸:“我们这些新社会的‘无房户’终于可以圆梦了!”
说干就干!去年元宵刚过,左邻右舍六户人家就联合租来了推土机挖脚、混凝土浇基、排污桶预埋、红砖头彻墙、新瓦片盖顶、横梁、不锈钢门窗统一采购,房子建成后,按统计的总金额,再根据每家每户的实际面积进行公开分摊。
老大在家多出力、老二、老三来出钱。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紧张施工,占地面积近三十个平方、供电、排污设施齐全的二层红砖洋瓦房在原来“土改房”的位置重新建成。
站在秋日的晚风中、夕阳下,望着自己人生中梦寐以求的第五代砖混结构的二层新房前,鲐背之年的老父亲满面皱纹的脸上再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