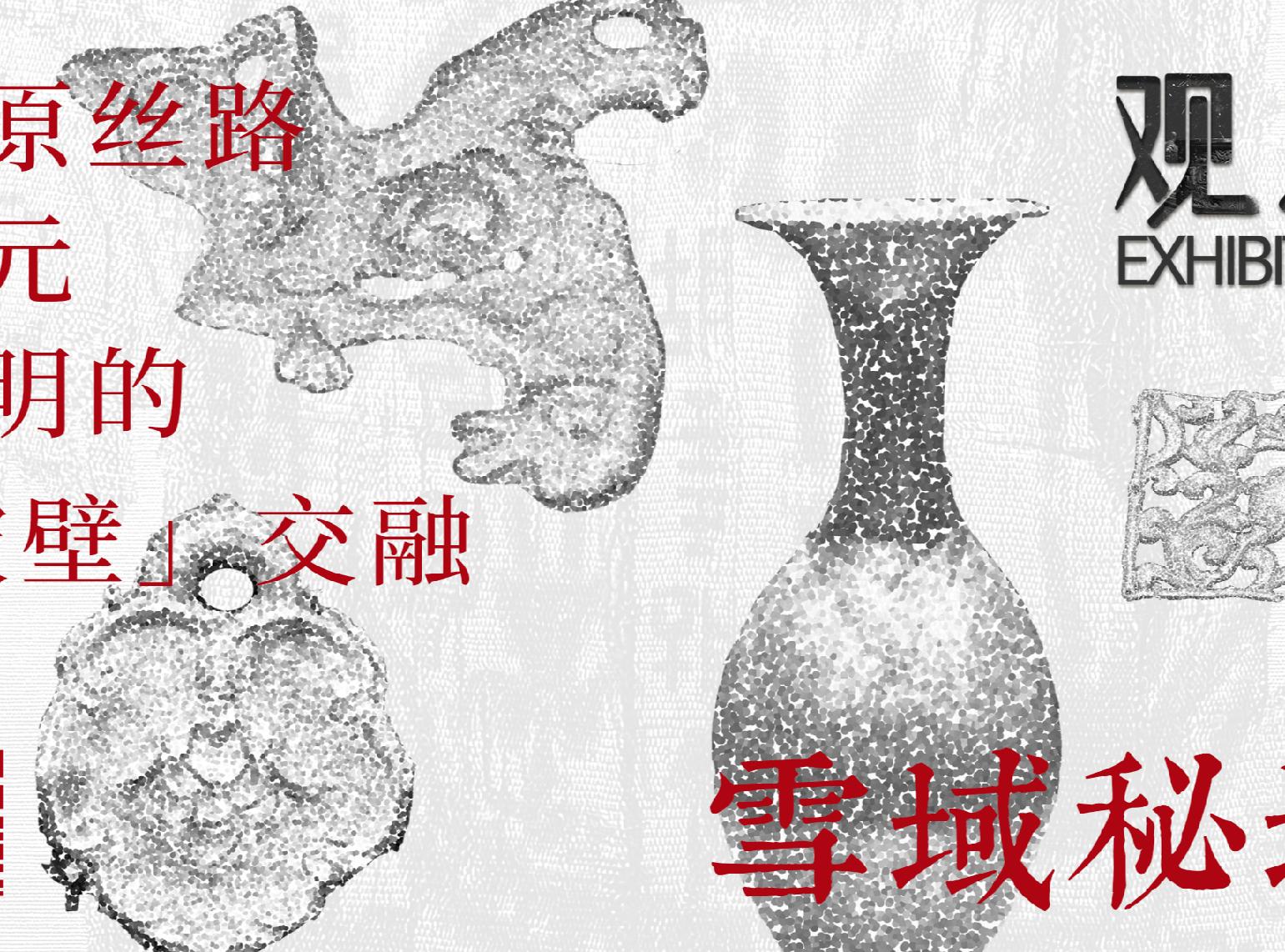陈巧茹有些惊奇地看着我:一个北方人,怎么会对川剧感兴趣?
陈巧茹,当代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工花旦、青衣、武旦,两次摘取 “中国戏剧梅花奖”,另外还获得过第 14 届上海白玉兰奖,第 12 届、14 届文华表演奖,代表剧目有《四川好人》《白蛇传》《欲海狂潮》《好女人、坏女人》《红梅记》《目连之母》《青春涅槃》《激流之家》《马前泼水》《打神》《打饼》《贵妃醉酒》等等。她主演的剧目多次到海外演出,为川剧赢得盛誉。
而我,一个北方人,则是突然间被川剧俘获的。
一次走在成都的街道上——也可能是在乐山——听到茶楼里的川剧,一人领唱,众人合唱。那合唱的部分,像巴山上粗犷的山歌,像川江上高亢的号子,与锣鼓的套打彼此呼应,时而激烈,时而悲苦,时而又投射出一种欢快。我没听清楚任何一句唱词,却如触电一般,一下子就被震慑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川剧高腔中的“帮腔”。高腔则是川剧五种声腔形式中的一种。
如此“帮腔”,与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功能有些类似,可以激发演员情绪,控制舞台节奏。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表现形式,台上人物想说而不好说的内心话,都可用帮腔表达出来。它甚至可以代表作者表达立场,代表观众表达心声。当然它还有更多奇妙的作用,那就只有川剧爱好者才能领会了。
对川剧感兴趣,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胶东半岛度过的,而我的母亲也曾是当地一位专业剧团的戏曲演员,受她的影响,我小时候就看过很多山东地方戏,什么柳琴戏、五音戏、茂腔、柳腔。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一唱众和”的表现形式。京剧当中也没有。
地方戏曲是依托在地方方言与地方民歌的基础上形成的。大西南山高水急、万物生长,造就了川剧唱腔的高亢激越而又婉转抒情。它历史悠久、剧目繁多,是中国戏曲的主要剧种之一,历经荣衰起伏,至今薪火相传。它妆容精美、表演细腻,折射生动的世态人情,素为观众喜闻乐见。而且,与多数中国传统戏曲一样,它不仅仅具有娱乐功能,同时也包含着很多教化世人的故事和道理。对于过去的中国百姓而言,忠孝节义、伦理纲常,大多就是从戏曲中学来的。
对我而言,最关键的,还是好听,入耳入心。
我有一颗“四川心”。我开始留意与川剧有关的信息,也看过几次川剧演出。对,就是川剧。并不是只有川人才能听川剧。它流行于四川省、重庆市及云南、贵州、湖北省的部分地区,是中国西南部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但我一个北方人完全可以看懂。它可不仅仅是你在宽窄巷子里看到的那些“变脸”、“吐火”——那不过是川剧众多技艺中两项小小的杂耍。某种意义上,它是巴蜀文化的集大成,在历史、文学、艺术、民俗等方各个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欣赏水平高低,只要问他喜欢川剧还是喜欢越剧。”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在他看来,川剧文学性更高,像“月明如水浸楼台”这样的唱词,在别的剧种里是找不出来的。而川剧的表现手法,也是更为奇特,更为新鲜。
有一年夏天,我去成都拜访诗人翟永明,谈到了川剧。我知道她与当地川剧界颇有渊源,就说,我很想采访一位当代川剧的代表性艺术家,你觉得应该是谁?翟永明说,那我介绍你认识一下陈巧茹吧。

▲ 陈巧茹 摄影/肖全
陈巧茹在 1979 年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考进四川省叙永县川剧团。从叙永县川剧团娃娃班的一名学员,到今天整个川剧界的领军人物,陈巧茹有着自己波澜曲折的戏剧人生。她见识了八十年代川剧黄金岁月的炽热火焰,也经历了九十年代中国戏剧市场的冰河时期。在川剧处于最低谷的日子里,她卖过化妆品,做过服装生意,还去唱了歌,差一点儿留在香港拍电影。但是她“入戏”实在太深,最终没有选择改行,十年跌宕之后,终于等来了川剧市场的一步步复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戏曲,就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一直以为中国戏曲的大幕早已落下,起衰振敝谈何容易。但近年戏曲市场的回暖还是让我感到意外。这固然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因素,但更多还是因为中国戏曲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随着当代人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的巨大变化,那种一场戏几千人上万人的大场面一去不返,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戏曲在局部生机盎然。中国古老文化的体量实在太大了,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也必须为其腾让一席之地。
或许,中国戏曲并不是在衰落,而是在转型。就如同唐诗没了,还有宋词;元杂剧没了,还有明传奇。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一起,号称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但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没有延续下来,而中国戏曲和它所依附的文明母体,则是屡背屡起。它所积淀的美学价值和人文内涵,其实就是那个古朴中国的精神基因双螺旋。
有时我们看不到它,不等于它不存在。
2018 年 7 月 2 日,成都暴雨,在陈巧茹的工作室里,我不停地追问她的过去,而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代表性传承人,一次次把话题引向未来。人生如戏,长亭短亭,有人谢幕,有人重生。她一直在努力捕捉变化,试图为我们带来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全新川剧。


▲ 舞台之外的陈巧茹

第一个十年:最宝贵的十年,最值得回味的十年
仲伟志搜神记:你的童年时代是怎样的?
陈巧茹:我生在梨园之家,父母都是叙永县川剧团的演员,家就住在剧场舞台的后场。从出生开始,生活、玩耍、学习,都是在剧院里、舞台边。我是在川剧的锣鼓声中泡大的,到五六岁的时候,早上六点钟就起床跟着父母长辈们练功,练完功吃点东西,到八点了再去上学。所以应该说我是从娘胎里就跟戏曲结缘了。

▲ 5 岁巧茹扮演的玉兔,嫦娥的扮演者是她的启蒙老师许云生
仲伟志搜神记: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艺的?
陈巧茹:真正从事川剧艺术应该是 1979 年 5 月份,就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那个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众所周知的文革样板戏的时期刚刚过去,赶上传统戏剧解禁,全省每一个县市都在招收学生,叫做“团带班”,是剧团带的班,不是川剧专业学校什么的。那时基本上都是团带班,比如金堂娃娃班等等,因为当时全省很多市县都有剧团。我就在这一年考上了家乡叙永县川剧团的娃娃班。
当年我们进剧团学戏,和现在的艺术类院校的教学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戏曲学校是按教学大纲循序渐进慢慢地学,基本功就要学上一两年。而我们那时进了剧团以后,也就半年集训时间,主要教我们简单的戏曲的功底,一般就是腰、腿、台步基本功练习,还有唱、发声,半年以后就开始排戏。我的第一出折子戏是《贵妃醉酒》,大戏就是《白蛇传》。然后,从 1980 年到 1983 年,我随团几乎跑遍全省地演出,内江啊、自贡啊、荣昌啊,还有很多更小的地方,1980年我们还是第一次来到成都,演出《白蛇传》、《贵妃醉酒》,还有《双驸马》、《百花公主》、《郑小娇》等。那会儿市场比较好,演出的时候观众也比较多,就在这四年里,过年过节从来都不休息,一年四季都是在演,四川每一个旮旮旯旯都演到了,基本上从早上起来就化着妆,有早场、午场、晚场。

▲ 1979 年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巧茹考进叙永县川剧团。前排右六为陈巧茹

▲ 1980 年到成都演出,与成都川剧名家们在一起,二排左六是张光茹,张光茹身边是陈巧茹

▲ 陈巧茹的启蒙戏《贵妃醉酒》
仲伟志:还有早场?那可真是川剧的黄金时代。
陈巧茹:有,一般早场十点开始,演到十二点休息。午场两点演到四点又休息,然后晚场七点开始。如果没有早场,那就下午接着演两场,一点半的演完了三点半,三点半演完晚上接着又演。因为那会儿没有电视,大家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业余生活就是看大戏。演出场次很多,所以我们这一代演员是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比较多,有时候还没怎么学好的,就已经“赶鸭子上架”地走上了舞台。但恰巧我们传统戏曲就是要多演,每演一场都是在学习,每演一场都有不同的心得,然后再调整。我的唱腔,我的动作,我的节奏点,或者是我的身段,或者是我的情感表达,每一场下来都有新的感悟,下一场可能就有新的改观。每天演出,每天感觉都不一样,唱做念打,都有了实践机会,所以进步提升会很快。现在的学习方式,在学校学一个戏,要三个月甚至半年,有机会的演上一两场,又不演了,等再演的时候,又忘光了,所以这是现代教学模式相对于传统艺术教育存在的弊端。社会在飞速地发展,什么都快,现在我们很多人都静不下来,就是要快快快!但是戏曲表演真不是你快就能做出来的,艺术是有特定规律的,特别是传统戏曲,“十年磨一剑”,它一定是点点滴滴逐步养成的。我经常感叹,为什么我们现在戏曲团体的学生(我们团现在就教了一批学生)——四年了,排一个戏两个戏,嗨呀!唱不了!可能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少了......所以我说,孩子们就要多演多唱啊!
仲伟志搜神记:这跟运动员“以赛代练”一个道理。
陈巧茹:对对对,就是以戏代功。演员在排戏、演出的时候,就是在练你的“唱做念打”,特别是武功演员,必须要给他边演边练。例如《白蛇传》,为什么我们强调《白蛇传》要长期演呢?因为这是一出几乎全行当“犯功戏”,演员在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是在练功,如果不在舞台上演练,功力肯定下降啊。人都是有惰性的,再加上现在的孩子,既不好管理,又比较娇气,一会儿肩又伤了,一会儿腿又疼了,根本没办法严格要求,一旦严厉了些,他们会觉得反感而抵触。根本不像以前的我们,师父有要求,那就必须练,每天要该做些什么,都得按师父的规矩来。现在不行,孩子们意识松散,不重规矩,有各种借口偷闲偷懒。所以跟我们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仲伟志:你说你 1980 年第一次到成都演出,给我们讲讲那个时候的成都吧,包括你们在成都的故事。
陈巧茹:我们是 1980 年 9 月份来的成都,当时觉得成都好漂亮啊,虽然春熙路还没有现在宽,有霓虹灯的成都夜景,还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记得看的第一场戏就是在红旗剧场(现在红旗剧场都没了),看的是阳友鹤老师从艺 60 周年纪念演出。没票了,我就仗着小身板儿混进去了,坐在二楼观众席的过道里看。好多人啊,现场气氛很热烈,观众很热情。当时心里就暗暗地说:以后一定要到成都来。这就像唱京剧一定要去北京、天津、上海,唱川剧一定要到成都来。如果不能来唱戏,也要来成都学习,只是机会难得啊。
因为当时家乡是座川南小县城,相对闭塞,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有电话、网络,家里也没这方面的社会关系,招生讯息什么的也都没有了解的渠道。但是也好,从 1980 年到 1983 年,这四年我跟着剧团在全省各地到处演,在剧团老师们的指导下,唱了好多好多戏,演了《百花公主》、《双驸马》、《白蛇传》,还有《贵妃醉酒》......扮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贵妃、公主、白蛇、青蛇,包括小乌龟......所以,我比其他人唱的戏都多,舞台经验也比其他人多。虽然表演还青涩稚嫩,但是舞台上的驾控能力、节奏等等方面的基础打得非常扎实。
那段给我很多回忆的岁月里,有这么个趣事:
1983 年,恰逢宜宾地区地级汇演,剧团老师给我排了一折《打神》参加汇演。那会儿我就十五六岁,年龄还小,还不能理解人物,只知道要怎么美,总觉得《打神》里那个凄苦的焦桂英造型不好看,我觉得还是《贵妃醉酒》、《白蛇传》里“娘娘”和“小姐”的装扮漂亮。于是,我坚决不演《打神》,说女主太丑了,披头散发,像个疯子。我要像其他小伙伴那样演美丽的“小姐”......
当时和我父亲同辈、一直很疼爱我的团长苦口婆心劝导我:“幺儿,就演这个戏嘛,这是个好戏啊!不是每个戏都要戴花戴凤的哦。”那时的我可听不进这些,我就要漂亮!最后还是团长伯伯妥协了,改了传统的造型,让我梳上“小姐”头,漂漂亮亮演了《打神》。到现在,我的《打神》也是个改良版“漂亮”的焦桂英,哈哈.....很有意思吧。
我是经历了这样的感受过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到小学校园去推广川剧,一定要抓住孩子的心理,不讲究剧目的高深,一定要载歌载舞,美轮美奂。漂亮的,好看的,好听的,才能吸引他们,才能让孩子们喜欢。孩子们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没有那么高的艺术鉴赏力、理解力,就是要好看、好玩、好听。兴趣是欣赏的基础,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强加给他们,只会适得其反。
仲伟志搜神记:梳着小姐头演《打神》,结果怎么样?
陈巧茹:我拿了一等奖。当时我自身条件和底子还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唱腔、表演、动作还是功夫,都很好。这个戏要求演员具有全面能力,而戏曲必须要有技巧的东西,技艺要惊人,表演还要感人。有位宜宾的女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巧缘(我的本名叫巧缘),你那么好的表演,可梳了个小姐头,就没办法展现戏中角色内心的悲愤和哀求。比如乞求神灵的时候要磕头,但你不能老这样磕头,要有戏曲的招,要用戏曲传统的这种技巧来展示人物的内心,就需要甩水发,你弄一个小姐头,怎么甩水发呢?”我想真的是,我情绪到那里了,不能老磕头的,要用更多的肢体语言来展示更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以啊,少年时的我认识还是浅了。
当然,人是逐步成长起来的,不是突然就全明白了。我们现在给孩子们排戏,也只能一步一步,急不得、快不了。那次虽然拿了一等奖,但是遗憾的是水发没有用上,技巧表现并不完整。之后我带这个戏参加成都市调演和全省的比赛演出,也是拿的一等奖。1983 年来了成都跟着老师(张光茹)以后,就开始转变了。老师对这个戏的剧本进行改编,以前是 50 多分钟,后来尽量精简,没有原版那么冗长;服装造型方面也做了调整,功夫比如说倒硬桩、还有高下(桌)、水发全部装进去,装扮既比传统造型干净漂亮,又保留了表演所必要的功能。后来我拿一度梅(注:第一次获得梅花奖)也有这一台折子戏,也是有这个《打神》。从这个《打神》里面,我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感悟,也就有不同的呈现。
仲伟志搜神记:你是怎么来到成都的呢?
陈巧茹:1983 年地级汇演拿了一等奖以后,宜宾地区一个老师感叹,“这个女孩子条件太好了,可惜生在了县剧团,如果是在成都、重庆可能发展空间更大。”当时我也十五六岁了,也有一些思想了,加上 13 岁来到成都,迷上了这个美丽的城市,就觉得我一定要找机会到成都。1983 年 9 月份、10 月份的时候,爸爸就带着我来成都拜师学艺,然后就有了和张光茹老师的这段师徒缘分,所以我后来的艺名就叫陈巧茹。
那时县剧团不是国营的,是自负盈亏的大集体,我是剧团年轻一代的主要演员之一,如果我走了,就少了一个主演,票房就要受到很大影响。于是,单位不同意调离,老师也担心我不能离开叙永。我的想法是:哪怕我进不了成都川剧院,也应该留在成都系统化深造两年。然后我去咨询四川省川剧学校,但因为川校刚招了一批新生,要等三四年以后才有招生计划。那怎么行啊?三四年以后我都二十多岁了,我等不了。我打定主意跟着张老师先学两三年,如果到了二十岁左右成都这边工作单位还没有着落,我再回去,哪怕回到泸州或者宜宾的市级以上剧团也好,也是为自己的前途想嘛。
张光茹老师还是考虑了很久,我们县剧团的刘团长是张光茹老师的师兄,如果我离开叙永来到成都,她会感觉有点对不起大师兄。后来我给老师表态,如果她不收我,我还要继续找其他老师学习,我的主意不会改,我就要来成都。老师终于收下了我,给我制定了严格的、密集的训练计划。就这样,我离开了叙永来到了成都,是 1983 年。
当时,进剧团都是要有人事指标的,即便来了,也不可能做临时工,就跟着老师做学徒。那时成都市川剧院有三个团,老师在一团,三团是青年团,一团、二团主要是是中老年演员。后来我就跟着老师到绵阳、什邡、绵竹巡演,从 1983 年 10 月份演到第二年春节,演了四个月。巡演期间我没演戏,但是我在这三四个月看了很多很多的戏,比如说我老师的、周学茹老师的旦角戏,包括我老师的大戏《庆云宫》、《程夫人闹朝》;还有就是小丑戏,当时刘金龙刘爷爷很火嘛,他们的《拜新年》啊、《劝夫》啊、《金台将》啊、《柜中缘》啊,我看了好多。还比如王世泽老师的小生戏。这些都是成都市川剧院老一辈艺术家的戏,和我在县剧团、地区级剧团看到的就不一样了,成都市的省市剧团,这就是川剧演员心目中的最高学府。这些戏大部分现在都不演了,有了这段经历,估计很多人都没有我看的戏多。
1984 年春节回到成都,二团的团长来一团请我老师参加一场演出,就在太空艺术中心演。太空艺术中心你不知道吧?那是在春熙路边的一个老剧场,现在拆掉了。那个团长看到老师身边的我,就问这个女孩子是谁?我老师说,这是我学生,你让她也演一个《打神》吧,人家刚拿了奖。团长说,行行行!这样我就去演《打神》。
那个时候,二团团长想引进一些年轻的演员,我去演《打神》的时候,他就请了当时文化局的一些处长来观看评估,我事先并不知情。这次演出后,大家都评价这个孩子还可以,就准备用特殊指标调我来成都,先做临时工嘛。这样一来我就有工资了!当时我来成都,我父亲每个月给我寄二十五块钱,吃住在老师家里,给老师交生活费二十块钱,自己五块钱零花。能拿工资,我很高兴啊。后来一团团长张开国老师说,你在我这里“搭伙食”都学了半年多了,你去二团干嘛?就在这儿!于是一团也坚持要我,好吧,就到一团做临时工,每个月能领到四十八块钱。当时四十八块钱很多了,就不要家里给我寄钱了!
进来一团做临时工以后,机会也比较好,先排了一个《薛宝钗》。《薛宝钗》里面我就演尤二姐,有技巧、有动的,大家都说这个孩子还不错。接下来就演《武则天》,因为正好武则天进宫不是才 13 岁嘛,还有响马,还要打,各种各样的功夫,那时候我十六七岁,正好这个年龄段,所以我就演《武则天》的一本和二本,就是从进宫到出家甘露寺这段戏,我老师演的三本和四本。领导们一看,说这个女孩子条件很好,当时就给了一个特殊指标要招进来。这是 1984 年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人事调动手续啦。虽然我们县剧团是自负盈亏,但还是要走人事调动程序的。当时的特殊指标基本上都只有 12 月中旬的时候才会下来,办手续的时间只有十多天,团长为了留下我,规定要先交五千块钱才放人,成都这边团长做承诺暂时给欠条都不行。由于成都这边没有及时交上这笔钱,这个指标就浪费了。那会儿有一个指标是很难的。成都这个团长挺好的,挺爱惜人才的,后来就让我没办理户口迁移的情况下,先给了五千块钱,第二年再申请这个指标。但是第二年又没有这个指标了,第三年又申请,一直到 1987 年才把我的人事关系办过来。所以说成都市川剧院还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平台,我后来当常务副院长也这样,只要你是全省的尖子,我都会给你拔上来,我不管你是哪里学的,不管是不是科班出身的,只要你能演好戏,我们都给你搭这个平台。

▲ 在《白蛇传》中扮演小乌龟的巧茹(左二)和张光茹老师在一起

▲ 张光茹老师讲戏

▲ 在《白蛇传》中饰演白蛇
仲伟志搜神记:这跟你的成长经历有关系。
陈巧茹:对。2004 年的时候,很多人说,陈巧茹弄了些不入流的“草根演员”进剧院。你知道,现在这个体制内的人员存在很多很多问题,自己不能唱,台下挺能说,上台就傻,还讲究什么学校毕业。有人对我引进人才有意见,说这些人和我有关系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我就在剧院大会上发言:我能走到今天,是成都市川剧院的前辈们、老领导们,还有成都市的领导们对人才重视和关心的结果。所以我说不管你是黄埔军校的还是总统府的——我们这里将川校叫做黄埔军校,将成都市艺术职业学院叫做总统府——你都要在川剧这舞台上来展示你自己,不管来自哪里,不能唱戏就不行!谁说草根出身就不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团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优秀的演员都是从县级市上来的,这就是大成都的胸怀,我们应该把这种优良的传统延续下去。
现在过去了十多年了,团里很多代表新生力量的好演员都是从各个县招进来的,现在全部都顶在舞台前沿,那些黄埔军校的就不一定行,就因为他自我感觉不一样,心态也各种不一样。舞台是唯一检验能力的标杆。
仲伟志搜神记:像你出道这么早的,还是很少见。首先是有实力,然后就是运气好。
陈巧茹:当时我演《武则天》的时候,按戏曲团体的论资排辈的常规,上有老师他们一辈 50 岁的,中间还有一拨 30 多岁的。我才十几岁,刚进剧团,还是个临时工,想当主演,戳脊梁的非议肯定多。可恰恰这个角色的各种特征都适合我,有领导和老师们的提携,顶着压力也上了。那会儿锦江剧场挂的牌,常常都是张光茹、周学茹、陈巧茹这些名字,所以很多人都以为陈巧茹也是 50 多岁的。因为出名早、还经常演,大家就觉得我应该是个老演员了。到现在我跟别人说我是陈巧茹,是张光茹老师的学生,还有人不相信,感觉陈巧茹应该好老了。还记得那时蓝光临老师点名要我跟他演戏,配《石怀玉惊梦》,我还有点胆怯,那是大艺术家啦!他安慰我:“巧茹不怕,你可以,我教你!”我真的很感恩这些老师,晓艇老师,蓝光临老师......就是他们这些大艺术家带着来自基层草根的我,一步一步地进步,最后脱颖而出。

▲ 1980 年,与阳友鹤老师合影
仲伟志搜神记:你的老师张光茹,也是一代传奇。
陈巧茹:是啊。《武则天》以后,老师给我排了很多传统的折子戏,那是非常宝贵的学习和经验积累。我一直希望在空闲时,乘精力还好,把我学过的剧目恢复一些出来,能把这些传统经典保留下去。而老师就一直在演大戏,一直在排戏,从 1983 年一直到 1987 年年底,五年,我就住在老师家里,吃饭在同一口锅里,睡觉在同一张床上,学戏基本上就是口传心授。
张光茹老师不光是教我艺术,还教我做人。她曾经是著名话剧演员、影视演员,是一代影帝冯喆的爱人。她的人生经历非常坎坷,早年在宜宾学川剧,因为人长得非常非常漂亮,常被宜宾的各种军阀骚扰,于是躲去了重庆,参加应云卫组建的中华剧艺社。应云卫觉得老师条件好,就把她介绍到上海拍电影、演话剧。她在上海认识了冯喆,在香港结婚,解放后,又回到上海。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老师看了成都川剧院在上海的演出,又勾起了对川剧的感情,然后回到了成都,重新拾起川剧表演。
冯喆老师较早过世,1993 年,老师在 60 岁的时候,患了肺癌,刚刚 63 岁就去世了。所以说我老师真的是非常坎坷的。
仲伟志搜神记:《四川好人》应该是你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川剧的代表剧目。那是你离开张光茹老师之后排的?
陈巧茹:是 1987 年以后。八十年代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传统文化在那个时候还比较兴旺,还比较受重视。在 1988 年的时候,我们就合团了,就是一团、二团年龄比较大的合在一起,然后一团、二团年轻、比较拔尖一点的就调到三团去,叫三团青年团。老师对我去三团还有点生我的气,有一段误会。我跟老师解释,不管哪个团三团,都是唱川剧,我都是在成都市川剧院的啊,走到哪里都是你的学生啊。后来老师也理解了,我们的关系也一直都很好。
我调到青年三团以后,就排了一个《四川好人》。《四川好人》在全国戏剧院团里面是走在最前列的,根据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同名剧改编,而且是李六乙导演的。就算到现在来看,我都觉得,我们四川,我们成都,我们的意识是非常超前的,至少在传统戏曲里面,川剧是走得很前列的。我的机会,都是成都川剧院领导的超前意识带给我的。像徐棻老师、魏明伦老师,这些剧作家在全国都是走在很前列的。
李六乙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刚毕业,《四川好人》正好是他的毕业作品,这个戏不是传统的戏曲,有话剧成分,但是又不是话剧,有戏曲传统的路数,这就要求一个演员要很恰当地把握这个度。团里排戏的时候,我就天天在台下看。参加排练的一个老师感觉有点吃力,李六乙导演就安排每天守在台下的我上去试试,我大胆上去排了跟晓艇老师演对手戏的那场。排完一段,李六乙说:就这种感觉,就你排,你排!我那会儿也就十八岁,而且刚调到三团,有顾虑。李六乙最终决定,由三个人参加排练,一人排一场,田老师排一场,毕小华老师排二场,我排三场。
我就这样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了,然后这些人都彩排、都演。可北京只能一个人演啊,领导反复斟酌,决定去北京由我出演。据说他们经过了一番激烈争吵,我也不知道,那时年纪还小,你叫我演我就演,不让我演就不演。所以我第一次进京就是《四川好人》,是 1987 年 11 月。演出场地是在北京王府井的吉祥剧院,现在也拆掉了......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和他的家人还一起来看了这个戏。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演出结束后,我们在北京还待了一个月,十三大期间,又到中南海去演了一场,演的是传统戏。我进中南海演出过两次,1987 年这是第一次。这次进京演出以后,在北京戏剧界奠定了一些基础,大家说这个孩子值得培养啊,所以 1991 年再去北京演传统戏《白蛇传》,1992 年拿了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仲伟志搜神记:出道早,成名也早。
陈巧茹:成名比较早,但是功力还不够。这就是我成长经历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里,我学到了最扎实的基本功,有了那么多舞台锻炼机会,看了那么多传统的剧目、那么多老艺术家的表演,现在看都看不到啊。我觉得这十年是我最宝贵的十年,最值得回味的十年。

▲ 《卓文君》外景之“当垆卖酒”

▲ 《卓文君》外景之“听琴”

▲ 《卓文君》外景之“夜奔”
第二个十年:彷徨与坚守
仲伟志搜神记:拿了梅花奖之后,接下来的日子,应该是你最高光的时刻吧。
陈巧茹:恰恰不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十年是我最艰难的十年,是精神上的艰难,就是说,在面上很风光的这十年,恰恰是我很彷徨的十年。
1992 年拿到梅花奖以后,我觉得以后应该更好了,应该做更美好的展望了,但是变了。整个剧团平常都没什么演出,三个团合了一个联合团,就只参加国家的调演。年轻人就更少演戏了,男的要么开出租车,要么在春熙路做倒爷,赚钱啊,白猫黑猫哪个挣着钱就是个好猫,大环境就是这样。这十年我做了什么呢?我去卖了化妆品,我去唱了歌,还去拍过电视。当然我没改行。这十年中,每年至少一次会到欧洲演出,有时是两次。
仲伟志搜神记:遇到了整个戏曲市场大环境的改变。
陈巧茹:那段时间剧团只有我在练功,都没人练了。锦江剧场没有人演戏,演也没人看。但我又很喜欢,我说管她呢,我自己弄吧。1991 年我们到香港去演出《白蛇传》,香港有机构要我留下来,就在香港拍电影、拍电视,那个时候很年轻,我唱歌听着也很好,他们说给我灌唱片,旁边人都说,很多人都到香港去了,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啊,他们还跟我签合同,要拍戏。但我们当时那个局长说不行,我们要先看剧本才能拍。香港哪有先看剧本的,我们要审,他们也没有审这一说。局长坚决不同意。我好不容易来到成都,更舍不得辞职,所以就放弃了香港。如果我去了,或许就是另外一条路了,人生就是选择。
我们在香港演出影响很大,姜文、刘晓庆也都来看。法国的一个文化交流项目的中间商看过后,找到我们。有个项目好像是法国的文化部给了他一笔经费,每年从国外带一两个剧团去法国演出,是半商半演。举例说吧,我们去那么多人,吃住行要两百万,只给你一百万的补助,另一百万要靠自己巡演票房赚回来。细节我也不太清楚,当时我只是个演员。那个时候还是喇叭裤流行的时代,我们《白蛇传》的服装都用尼龙纱这些流行的面料,衣服上还钉着闪闪的亮片。法国演出商找到徐棻老师,跟我们提出,他们什么“时髦”元素都不要,不要布景,不要舞美,只要你们纯传统的服装,全部要丝绸,然后手绣,他们就是要传统的那种,纯手工的,金线图案的就要老金线来盘,不要亮片这些东西。我还觉得他说这个老土啊,我们觉得我们那样是先进,那才是时髦,但是人家不要,就要你原汁原味的。
然后我们就全部用丝绸面料、手工制作,裤子上绣的蛇鳞,就用了传统的银线来盘的。准备好以后,我们就到法国去演出,成都市一位副书记带队,徐棻老师是艺术总监。那是 1992 年底,演了五十多天,在巴黎的圆点剧场演过,去我们的友好城市蒙彼利埃演过,走了 30 多个城市,回来都是 1993 年了。我演白蛇,一个人演了 38 场。刚开始是六成座,后来八成座,到了后来全部加座。我们演唱全是原生态的,按他们的要求不用麦,所以特别特别的累。我们已经习惯用麦、大喇叭的那种演唱,所以都不太适应。但是慢慢地,我才知道,人家其实是在欣赏我们最原汁原味的、我们最优秀的、传统的东西。
在法国演的时候,西班牙一个演出商也看中我们的剧目,跟我们签订了合同,然后从 1992 年底到 2002 年,每一年都是一到两次去欧洲,法国、瑞士、德国,还有加拿大,开始是《白蛇传》,后来是《目连之母》。长期合作以后,对方对我的表演就很信任。我也不能总是演《白蛇传》啊,1996年刚做了一台《目连》,但那个是文戏,没有《白蛇传》这么热闹,我担心他们看不懂,他说没事儿,只要你的戏就行。然后又请我们过去演。
所以,那十年里,在国内演出不多,很多人都以为我不唱戏了,其实是我们经常在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演出。在国内我只是参加了个别戏的排演,当时的大环境下做不了什么戏。于是,我的心理落差特别大。我们在国外演出,得到很高的荣誉和尊重,但是回到国内来,参加聚会时,大家一听你是唱川剧的,纷纷瞧不起。那种失落感真的是太强烈了。当时我的师兄师姐们,还有我身边比我条件更差的人,人家都在做生意赚钱。有人劝我,你不比她们差,为什么还搞这个川剧,川剧都死了你搞啥子嘛。有一段时间,我也不想唱戏了,做生意吧。我卖服装,经营化妆品、饰品,做得还很好,都赚了钱。当然,我做的生意跟我的专业还是有关系的,演员的本能嘛,我爱美呀!我没有去卖煤炭哦,跟艺术还是比较挂钩的哈。
仲伟志搜神记:但对你这种人而言,赚钱带不来更大的幸福。
陈巧茹:实际上,这十年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挣了钱,买了房子,有美美的衣服和高品质的生活。可魂丢了,方向没了,非常困惑。我常扪心自问,是我变了还是这个社会变了?是得了梅花奖,心态变了吗?但我觉得梅花奖对我也没有什么,那只代表过去啊。就是觉得迷茫,找不到方向。所以当时我就跟徐棻老师经常沟通,她说这是时代变迁,经济越是腾飞的时候,传统文化往往越是没落。
但是我要特别感谢那些年的国际文化交流演出,这坚定了我对我们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对川剧价值的认识。我是反过来看,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土的、我们瞧不起的,别人觉得那么好?包括我们戏曲的这种表现形式,这种虚拟空间的运用,这种空间的转换,别人都没有的,为什么我们会自暴自弃呢?
仲伟志搜神记:能有这种认知,说明这十年你有更高层面的收获啊。
陈巧茹:是,这十年让我获得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这十年是对内心的一种煎熬,当然同时也是一种坚守,是一个坚定信念的过程。
到 1996 年、1997 年,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这样患得患失不好。唱川剧不挣钱,还要倒贴,但是又舍不得放弃川剧,怎么办?徐棻老师对我很好,她会开导我、引领我,经常跟我聊天。后来徐老师说,你自己定吧,你自己喜欢,就让自己开心吧。从 2002 年开始,我就从剧团安排我做什么、从别人安排我演什么,逐渐转变到我自己选择应该演什么、我想表现什么、我要展示什么。
仲伟志:你要展示什么?
陈巧茹:我们的传统戏,首先是传承、继承,但是我们还要创新,包括调整剧本、唱腔、音乐;我们的新创剧目,在保留传统精华的同时,还要有思想的提升,还要变得更有意思,因为观众在变化。他们不像以前的老观众,闭着眼睛听你唱,睁开眼睛看杂耍,现在观众有新思想了,他在乎看了以后他能感受到什么,感悟到什么,这两个小时给他的生活有一些什么启迪,跟他的心灵有一些什么碰撞。这样一来,就对一个演员、一个剧目,对所有表现形式,他们都更挑剔了。川剧不可能再像八十年代初期那种广场文化一样,只要热闹、好玩就会来看。我们有大众欣赏的,比如变脸啊,喷火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创新发展。很多传统的剧目不能像以前那样演,而是应该修改,调整长短,服装、化妆一定要美,要精致。我们要有我们的精髓,要将我们传统中那些优秀的东西,通过新的包装呈现出来。因为我们现在能吸引的这一部分人,毕竟是小众的,但是这个小众不是一般的观众。
仲伟志:他们是川剧的种子。
陈巧茹:对。他们会把川剧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以前我们的老艺术家,没有那么好的灯光、舞美,煤油炉子照着,黑乎乎的就演了,也能满足当时观众的需要。现在能满足吗?不能。现在虽然我们的剧目是传统的,但是我们的灯光要明亮,舞台要干净,服装要漂亮。比如同样是《贵妃醉酒》,我们现在的舞台效果就是美轮美奂的,明亮光鲜。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传承下来了,该怎么样包装,怎么样创新,这是很重要的命题。在这方面我们要向日本、德国这些国家学习,学习他们对艺术的态度,对传统的态度。这十年我去日本参加了几次亚洲戏剧节,看到他们如何对待他们的能剧,是如何追求完美,而我们在这方面缺失太多了,所以应该向他们学习,比如在服装方面的考究,在舞美、音乐这方方面面都要考究,千万不能以量化取胜,我们应该有质的追求,才能够保证我们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仲伟志:钱从哪儿来呢?
陈巧茹:从九几年开始,一直到 2000 年,我就在调整自己,也挣钱了,即便只是够生活花销。还是喜欢川剧,就随着自己的心愿做,一直到 2006 年,才知道川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才知道这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瑰宝了。概括地说,从 2000 年到 2010 年这十年,我努力去做,自己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少,然后尽量去推广,包括到大学。没有费用,我就去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向人家游说,包一场嘛,五千块钱嘛。你想啊,我们租车、吃饭都要费用,还有消耗品,纸啊、油啊,这些化妆的东西都要费用的。一开始,朋友们碍于情面支持,演完一场,感觉不错,然后我就趁热打铁,下次再多争取点钱嘛。后来慢慢政府又支持,演一场给一万块钱,两万块钱演两场。我就拿着两万块经费演四场,还是五千块钱一场。就这样慢慢、慢慢地推广,现在情况就好多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曾经参加一场演出,虽然那天没有多少人,我还推掉了一个生意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认真地演了下来。演出结束时,一个老教授跟我说:“巧茹,真不容易啊,为了你们的坚守,我给你们深深地鞠一躬。”我感动地差不多哭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有人理解,有人懂你。那个时候大概是 2003 年的,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说现在都地球村了,吃的、用的、看的都是人家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什么,你们还在这里坚持做川剧,真的是要感谢你们。
哎呀,我觉得终于有懂的人了,继续再做吧,就坚持下去吧。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的理想,就是觉得川剧真的是很有意思的,真的是很有魅力的,如果还有人懂你,为什么不做呢?
我是从 2004 年做常务副院长以后,考虑的问题比较多了一些,剧院的建设,人才的培养,等等等等。一个剧院、一个剧团、一个单位,不管你是什么性质的,没有人才,你什么事都做不了,怎么样来留住人才,怎么样来吸引人才,这是最重要的。戏剧团体的演员的思想状态很简单的——你看着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只要给他们足够的尊重,给他们一个愉悦的工作环境,就可以,他们不像生意人过多的计较金钱的得失。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能快乐地做艺术,而我的责任就是给他们搭建好平台。如果说一个剧团没有戏演,大家比较闲,那绝对矛盾很多,有事做、有戏排,忙起来就什么矛盾都没有了。
不过呢,现在还是出现一些让人不乐观的现象,和以前又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多演,得不到演出机会,就不开心。现在很多人的态度是无所谓,可以找各种借口不参加演出,我还得用提高收入来抚慰他们。大家的意识和思维都变了,趋利啊。当然在这十年,我觉得无论从我们国家层面,还是到我们地方政府,再到我们剧院,给予戏曲演员的平台和待遇都比九十年代好多了,当然你想回到八十年代那不可能,所以也要调整心态,调整自己。
仲伟志:就是要把自己真正当成文化遗产?
陈巧茹:我经常在跟我自己对话,调整心态、坚定信心。为什么要调整心态呢?戏曲不可能再有一场戏几千人上万人的大场面了,不可能的,我们尽量把我们的戏做细做精,哪怕是 50 人、100 人来欣赏,也要认真对待。这 50 人、100 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众,他们可能是大学、企业里的年轻人,然后我们就可以与这些爱好传统艺术的年轻人一起来共同推广川剧。
仲伟志: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川剧进校园就很好啊。我跟学生们聊过,他们还是愿意看,但是让他们花几十块钱买票去看就不现实了。就是应该让这些孩子们先接触川剧、了解川剧,他不了解川剧,就不可能去热爱。
陈巧茹:对,这就是我强调的,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人,你都要从认识到了解,从了解到喜欢,从喜欢再到热爱。年轻人谈恋爱也是嘛,要先认识,中间交往的过程不可能省略的。对戏曲来说,剧场没有了,这个过程的“媒人”也就没有了,让他们怎么认识你、喜欢你啊?当然,现在扶持政策非常多了,问题是,要有针对性地选好剧目,对小学生、中学生的剧目一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做不好,就是反向宣传。这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不能一刀切,但是现在我们太粗放了,尽管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但是效果并不好。

▲ 《贵妃醉酒》外景




▲ 在三和老爷车博物馆艺术空间演出的《贵妃醉酒》剧照
未来的十年:努力把一些经典的剧目保留下来
仲伟志:除了手头这一摊子行政事务,你还要自己演戏,还要推广川剧,压力很大吧?
陈巧茹:一直压力都大,现在好一些。我不是单位的一把手,压力不是最大。在艺术方面,在剧院发展、剧目建设、人才培养这些方面,这是我的职责,我把它做好,然后全方位的工作是我们院长负责。
仲伟志:你是按照每个十年来概括自己的人生的,那么未来十年有什么计划?
陈巧茹:面对未来十年,我还是要调整好心态。我是这么思考的:个人精力所限,现在我想搞创新也比较难了,应该努力把一些经典的剧目保留下来。去年“四个一批”给了一部分经费,正在计划实施。
还有,我这里还有个小剧场合作项目,是跟三和汽车集团的好朋友一起喝茶聊天聊出来的。他们本来搞了一个小电影厅,二三十个人,我说你扩大一点点嘛,就可以看戏了,全世界到处都有汽车,中国的汽车还不是世界最好的,你全世界弄些车子到四川来,来看什么?四川的代表文化是川剧嘛。我把他给“编”进去了,哈哈,就弄了一个小剧场,他给我一些基本的演出费用,我用演出给他的企业、剧场带来人气。我说你可不要想用演出赚钱,你在你汽车上赚钱就行了。
这是一个精致的、纯传统的、需要细细品味的川剧舞台。我认为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如果有国外的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要来成都看你们川剧,要看你原汁原味的川剧,在哪里能看?我们可以把小剧场做成这样的平台,那就成功了。
仲伟志:你拉赞助的能力很强啊。
陈巧茹:我们尝试着把这个项目做好,这也是人家企业家的情怀。不过从长期来看,企业是讲经济效益的,能做多久就多久吧。可惜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我自己要有那么多钱,那就修一个剧场,开心、愉快、美美的来做一些艺术,但是没这个能力,没办法。总的来说,这未来十年,我只要做,一定要开心地做,不会像我 2004 年我刚任常务副院长的时候,看到剧院现状心里急,想马上做好啊,所以付出的太多太多,包括我对儿子都觉得很抱歉,基本上没时间关照他。
仲伟志:以后还会经常去国外演出?
陈巧茹:会,将来还想做更多这种中外文化交流。计划今年 11 月份到日本几所大学去演,演出之后做讲座,他们就要传统折子戏,比如说《秋江》、《打神》、《思凡》,但是经费呢,日本方面可以负责落地,其他经费要我自己去找,我今年带团队去美国就是这样,要自筹资金。其实我这么做为什么?理解的就理解,不理解的也有很多,但是我不想多解释。国外的文化界人士,就是看到了我做的这些,愿意来找我。日本这个事情,我最近太忙了,现在还没有精力去做。不过今年让我再找经费的话,可能就有点麻烦。但我觉得这个项目是非常好的,尽量争取实现。
仲伟志:你怎么看王佩瑜所走的这条路线?
陈巧茹:我觉得非常好,我认为,我们不要去计较,说这样不是京剧,那样不是川剧。王佩瑜不是京剧,那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川剧的变脸一样,我们也不能阻挡,你阻挡不了的。变脸它就代表不了川剧,但它是从川剧延伸出来的,没有变脸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川剧。王佩瑜让那么多年轻人喜欢京剧,这就是她作为京剧人的最大贡献,而且王佩瑜京剧唱得非常好,我觉得很棒很棒。

仲伟志/文